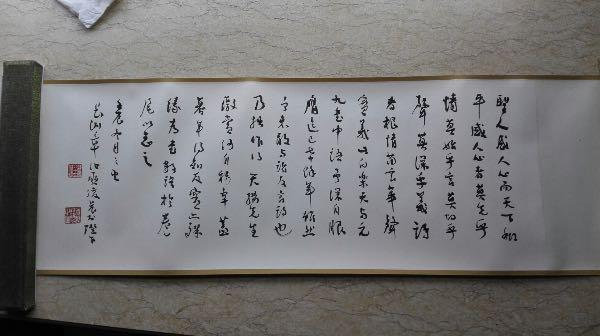我有一个远房的堂兄,叫王三溜。为人特别不着调,那是好吃懒做,胡吹乱確,胡做非为,逮谁確谁。他不干正事,他爹俺二大爷恼得受不了,打骂饿饭,捆绑送官,啥招都使了,就是拾掇不了他。劝人不醒,顺手一㧐,随他吧,不管了,爱咋地咋地吧。他爹都不管了,谁还管他呀?谁又能管得了啊?于是,我这位仁兄更是任性胡来 ,无法无天。打瞎子捂瘸子气哑子骂聋子,戳个猫逗个狗,偷看大闺女解小手,扒绝户坟踹寡妇门,当街摔五保户的和面盆,啥坏事都少不了他。把俺二大爷恼得,咬牙切齿地咒他:“小三溜,老天爷咋不打雷呀?咋不嗑嚓一声活劈了你呀?”王三溜嘀嘀嘀笑笑,说:“俺爹,老天爷活劈了

我?他哪舍得呀?你知道老天爷是谁不?那是俺老丈人!”二大爷气得哼一声,一下子躺倒床上,半天没缓过气来。
我们那一带,一到秋末,地里庄稼割砍完了的时候,打野兔子的人就多了起来。这帮子走了那帮子来,这里“嘣”,那里“哐”,四处冒烟,到处开火,枪声响过,猎手紧跑几步,搭手就逮起一直只肥嘟嘟沉甸甸黄褐色野兔子。然后,打兔子的笑嘻嘻地把兔子往后边背篓里一撂,就走了。馋得小孩子崽子乱叫唤,“给我只兔子尾巴”,“给我只兔子尾巴”。俺三溜哥瞅着蚂蚁上树了。大秋天,又是收秋,又是种麦,忙死人。他仁兄鸟活不干,跟着人家打兔子的转悠了好几天,非要求人家收他作徒弟不可。好话说了一草篓,眼泪流了两箩筐,最后膝盖一软,竟给人家跪下了。可是打兔子的一般都是窝班,父子相传,不收外人。不管王三溜用啥手段,人家就是不收他。恼得王三溜一蹦腰高跳了起来,破口大骂:“我日恁姐,离了恁这茄棵就吊不死人了?瞪大恁的狗眼看着吧,看看我王三溜怎样打兔子的吧!”说罢拿腿蹿了。
王三溜一蹿出去,村里人有小半年没见过他的鬼影子。等人们再发现他的时候,这活宝正在西北地里转悠着打兔子呢。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一整套的装备,长筒枪,扁背篓,宽腰带,火药壶。浑身上下收拾得利利落落,有模有样。可是当然是中看不中用了,转悠了好几天,裤子鞋袜弄得脏呼呼的,结果连个兔子毛也没打着。村里人都知道他打不住兔子,故意出他洋相,说,“老三哪,打了几只啊?”“溜溜啊,用不用我替你掂几只啊?”“三掌柜的,喊恁爹拉辆车子接你吧,甭压死你?”恼得王三溜乱怼乱骂:“驴吃葛针——用你多嘴?等着吧,老子吃兔子肉时馋死恁个王八操的。”
老油条王二壳篓说:“俺三儿啊,你这可不中啊。隔行如隔山。人家打兔子的长着兔子眼呢,甭看咱过一趟啥都看不见,可人家打老远里就看清了,那叫看色望气儿加闻味儿。兔子卧草窝,浑身紫花色,恰如屁股蛋,灰白加黄褐儿。上边还冒白气儿,外带尿骚味。打兔子更有技巧,兔子不动就打卧,兔子要动就打跑。就是说,兔子没发现你,你就趁它卧着时开枪;它要发现你,它一准要跑,你就在它前边开枪,它一跑,你枪一响,正好打上,一打一个准。这就叫打跑。”王三溜疑疑惑惑地说:“俺二叔,你不是在確我吧?”二壳篓说:“看俺三儿,咱俩谁跟谁呀?我跟恁爹俺二哥还伙着一个老爷爷咧。”三溜说:“那,就谢谢了。”
人家打兔子的常常是趁着秋罢青纱帐放倒的时候,才做活。图得是行走无碍,观察无挡,做活得力。而王三溜子不管这些,不分季节,见天在庄稼地里胡出溜。兔子胆賊小又贼警觉,你在庄稼棵子里胡踏乱趟,弄得哗啦啦山响,兔子听到了随便一躲,你打兔子呢,打个茄子吧。所以,王三溜出溜了一月多,还是连一根兔子毛都没瞅见。这活宝着实有点烦了。
这天 ,三溜子灵感大发,突来异想,老子何不顺着豬笼河大堤转转呢?这里宽敞明亮,野花开放,野鸟成群,河水荡漾,又看美景,又打兔子,一枪攮俩眼,那叫得发他娘哭半夜——得发死了。于是,三溜子扛枪就登上了豬笼河大堤。
大堤上,都是生产队里种蓖麻。夏天了,蓖麻棵子分杈已经很多了,盘铺子伸展得很大,棵棵像伞盖,茂密葱茏。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绿色的长龙,蔚为壮观。真乃是乡村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三溜子一登上大堤,就高兴坏了。一高兴,把神圣使命都忘了,竟然唱起路戏来了,“我是走过了嗷嗷,一洼啊啊又啊又一洼啊啊,洼洼地里好嗷好庄稼啊嗬嗬嗬……”
吔嗬,前边蓖麻棵子下面是个啥玩意啊?紫花地儿,屁股色儿,灰白浅黄的。还冒着白气儿,透着骚味儿,这不是只兔子还能是龟孙啥呀?不错,没跑,就是只大肥兔子。这回你狗日可跑不掉了,我可发利市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呀,岂能错过?这次我要是再叫它跑了,我王三溜就是个百分之一百的的废物蛋,那我怎么对不起这一个多月的鞋底子费呢?必须悄悄的,可不能再叫它跑了。三溜子一边想,一边靠近。行了,行了,位置恰到好处,举枪,瞄准,扣扳机,三溜子开始了神操作。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嘣”一声爆响,蓖麻棵里“啊”一声,“呼”,蹦出来一个大活人。那人往前一扑,扑通栽倒在河堤二坡沿上,嗷嗷惨叫起来。剪发头,青布褂,黑裤子嘟噜到脚脖那,白白的大屁股全裸着,一边的屁股蛋上肉翻血流,惨不忍睹。这个人,还是个娘们,还是个年轻娘们。不用说,她中枪了。就是说,王三溜打兔子呢,打住了个年轻娘们。这问题可严重了哈。
当然,王三溜子也吓坏了。随着娘们那“嗷唠”一声和那玩命地一扑。吓得王三溜子“哎呀”一声,一屁股蹲着了地上,头蒙一家伙啥都不知道了。等王三溜子恢复了神志,他看到了眼前的情景,听到了娘们的惨叫,他啥都明白了。我的老爷,稀屎粑粑拉裤兜里,这叫我咋擦呀?这娘们能活不能活呀?她要死了,他家里的人还不打我个半死,然后再叫我抵命啊!就是死不了,光医药费我也拿不起啊!要是再弄个不死不活的,残废了,我还不得养她一辈子呀!不管咋着都够我喝一壶的了!我还是趁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候快闪吧,叫人弄住,马上就会被揍个苦茬子呀!走吧。走了走了,一走就了,不了也了,不了了之啊!
想到这里,王三溜根本没有靠前仔细看看,或者认真问问啥的,而是把破枪背篓扑通往河一撂,拿腿蹿了,比兔子都快。
中枪的娘们,鬼哭狼嚎地惨叫了半天,见也没人向前探问。力气就小了许多。模模糊糊听着好像有人要开路,娘们就不顾喊疼叫苦了,改央求了:“大哥呀,恁不能撂下我不管哪。恁行行好,喊人救救我吧。只要恁喊了人,救了我,我就不赖你了。真的,我不赖你。你不信,我给你赌咒盟誓...…”回答她的是哗哗的河水和呼呼的南风。
娘们央求了半天,见没有任何动静,不央求了,又改了,改骂了:“你个血王八孙哈,没爹的孩子,你把恁娘的腚打得血里呼啦的,破筛子底样,你扔下不管了。等俺娘家的人知道了,看不活撕了你!”如此这般地骂了半天,只有几只麻雀子围着她喳喳叫唤了几声,又飞了,再无其他声音了。娘们害怕了,不骂了,用尽浑身力气嚎叫起来,“救命啊,救命!救命啊,快救救我吧!”
哭叫声惊动了下地薅草的老头王二腥气。二腥气走上前去,赶紧把眼捂了,说:“你这闺女快把裤子拉上啊!”娘们说:“疼,疼啊!疼死了!”二腥气说:“那甭了,还这样吧。你这是咋回事啊,恁给我说说。”娘们哇啦大哭,边哭边说,吭哧瘪肚地把情况给二腥气说了一遍。
原来,这娘们是西村罐头寨的,要到东村李家楼看他娘家爹。走到豬笼河大桥上,觉着有点尿憋,一看四外无人,就跑到大堤上蓖麻棵子下面方便,刚尿了一半,嘣一家伙,她脑袋轰一下就啥事都不知道了。等醒来了,光觉着一边屁股疼,用手一摸弄了一手血,她才模模糊糊知道咋回事了。可她也傻了,光知道害怕了,光知道喊屁股疼了,啥也不顾了。可她还是觉着好像有一个打兔子的在她眼前晃荡了几下,就跑没影了。
二腥气啥都明白了。不用说,这一准是村里那个不着调的半熟子货做下的这种没屁股眼子的事。可这事该咋办哪?你总不能领着苦主儿往王三溜家送吧?到时候人家三溜家不认账,不把你搁艮瓜地里么?那你可就屙屎屙到南瓜叶上没法擦了。可人命关天哪,不管可不行啊。二腥气就问娘们,你是李家楼谁家的人啊?娘们说:“李二肥家的四妮儿。”二腥气大叫一声:“咦嘻,二肥哥家的孩子啊。别哭了,别哭了。我跟恁爹老好了,赶柳河镇集从恁门口过,恁娘老给俺端水拿馍的。闺女,忍忍,把裤子拉上,我这就去叫人。”
二腥气撅哒撅哒,一口气跑到大队部,找到了支书王三托盘。三托盘一听,勃然大怒:“龟孙王三溜,能得豆豆的,白兰洼盛不下他了哈,要上天入地咧。你看看,你看看,屙这一滩子。我看他驴日的咋摆治?猴七儿,四头鸡儿,小假妮儿,还有二母猪儿,瞪着两眼咋了,还不找车子去!”几个年轻人一声呐喊,“走走走”。拉过一辆胶皮拉车,把二腥气撂到车上,拉起就跑。
速度那叫一个快哟,一眨眼就来到豬笼河大堤上。娘们还在那趴着打粘窝咧。几个年轻孩子一看,娘们那白白红红的两爿子不一样的屁股,再联想到三溜子瞄准开枪那滑稽样子,大家都吞儿一声笑了。二腥气呵斥道:“啥时候了?还还还笑。”年轻人忍住笑,七手八脚地把娘们捂拢到拉车上,然后,拉着车子还是个跑啊。
跑到李家楼,猴七儿几个把娘们交给李二肥,拉着车子又跑了回来。路上大家越想越觉着可笑,哈哈哈,哈哈哈,笑得都走不成路了。
李二肥可忙坏了,一边组织人马送闺女去柳河镇医院就诊,一边请大队干部来白兰洼交涉。李家楼的干部往白兰洼大队部一坐,三托盘敬烟人家不接,递水人家不喝。几个干部扮白脸的扮白脸,扮红脸的扮红脸。扮白脸的气急败坏,恶语倾盆,说:“马上交出凶手。不然,明天血洗恁白兰洼,杀个孩娃不剩!”扮红脸的一团和气,笑逐颜开,“哎哎,托盘啊,咱俩个村,村头搭村头,庄尾接庄尾,老辈都没有错过。杀人不过头点地么,事大事小都有法么。恁交出凶手,再包工养伤,把医疗费也拿了,俺李家楼再不说半个不字了。这多好啊,和和气气,啥问题都解决了。”三托盘原先打算死不承认呢。一想,人命关天,再瞒瞒藏藏是不合适了。那好,孩子哭了抱给他娘。三托盘一声吼叫,三溜他爹俺二大爷就被薅到了大队部。
二大爷屁股还没挨住板凳呢,就被三托盘骂了个狗血喷头:“二掌柜的,你瞅瞅你瞅瞅,你养的是儿啊还是狼羔子呀?能得还是他不是他了?打鸡巴兔子咧,打住人家个大白屁股。兔子啥样啊?屁股蛋子啥样啊?眼瞎呀?还是眼搁腚沟子里长着了?这都哪跟哪呀?这下好了,腚给人家打透气个球的了,我看你咋屙呀?咹?二掌柜的!”二大爷点头如確蒜,弯腰如弯弓,叉腿似罗圈,结结巴巴地说:“哎哎,三弟,托盘,恁二哥我是磨道的驴——专听你喝,你说哪我应从哪,中不中?”三托盘恶狠狠地说:“看看,看你那熊样。我我我恼上来,光想踹你几脚!”二大爷更加卑微,说:“踹吧踹吧,只要不怕闪了恁的尊脚,你就踹……踹踹吧。”踹倒是没有踹,只是包工养伤住院费全掏是跑不掉了。二大爷咬着牙应承下来这些。李家楼的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那时的人都古道热肠,朴实厚道,饿养儿女往上长咧,谁也不愿意落下个讹人的恶名。哪像现在呀,动不动就讹你一家伙。弄不好就叫你倾家荡产。
也是三溜子时运好,娘们那屁股看起来血里呼啦,皮开肉翻厉害得不得了。但是,打兔子枪威力有限,打在屁股蛋子上,只是在肉里留下了几粒铁砂子。屁股蛋子上肉厚筋少,铁砂子并没有伤着筋骨。医生把铁砂子剥出来,再弄些消炎药上上,慢慢也就好了。当然那洋罪是没少受,那两天这娘们老像蝎子蜇住腿裆似的直嗓子拉气地鬼嗥,吓得住院的病号乱捂耳朵。
等娘们出院了,俺二大爷二大娘又兜了些鸡蛋挂面油果啥的,不厌其烦地登门看了人家好几趟。杀人不过头点地,做功如此,李家楼的人气儿慢慢也消了。事情也就算了了。当然,二大爷为此也拆着卖了两间屋子。可没闹出人命,还不够幸运的了吗?
事虽然了了,但三溜子却没影了。也不知道他蹿那去了。二大爷恼恨他是不错,可毕竟是儿呀,二大爷为此常常摇头叹气,嘟嘟囔囔:“唉,这死孩子哪去了呀?”三溜子人没影了,可恶名却留下了。村人不再叫他三溜子了,改叫他“神枪手”了。神枪手?不错吧,一枪打住个肥兔子,一打一个准,够神的吧?


濮水野老.2020.6.3。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