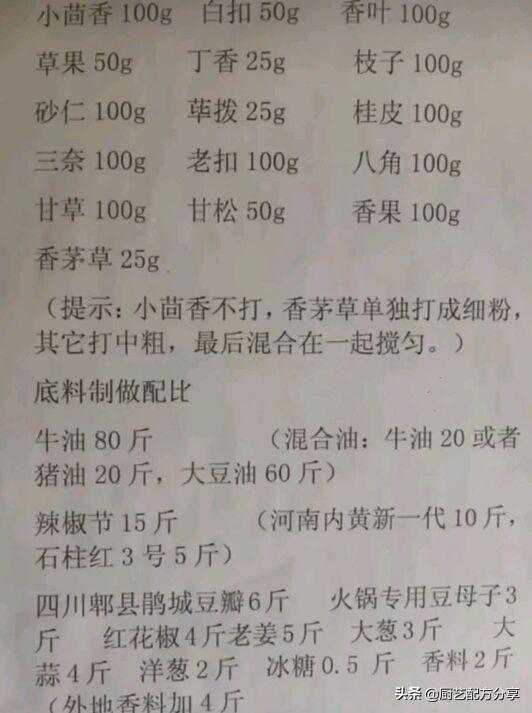嘉宾档案
王振堂,1938年生,北京市人。播音指导、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代名赵明。曾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党支部书记,中共贵州省广播电视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贵州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译制部主任、国际部主任等职务。
1962年起,从事广播电视播音工作达30余年。曾主播大量新闻、社论、通讯、专题片解说;先后播讲电影、话剧及古典、现代文学作品数十部(篇),主持参与200余部集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译制片等演播、译制配音及导演工作;撰写论文《播音员主持人形象改善与自律意识修养》《播音情感刍议》等数篇,其中分别获全国播音主持论文评选一、 二、三等奖;主编我国首部播音论著《中国播音学文集》(第一集);为重庆邮电大学主编我国首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试用教材《广播电视节目语体学》;合编电视剧《乌蒙情》,合编反映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电视连续剧《巨龙之光》(10集)。受聘于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香港国际影视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其业绩辑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9年)《中国当代播音员主持人大典》等。
>>>>>>>>>>

“王振堂实在是一个幸运的人。”
他做播音主持,差错率仅有万分之零点几;他做电视台主编,编排译制的节目走进千家万户;他在退休后去各大高校任教,受到许多学生敬爱,交情延续至今……于是,他朝夕相伴的夫人打趣他“幸运”。但王振堂的“幸运”并不是凭空发生,在他60多年的从业时光里,单纯、欢乐、热情等特质组成了他个性的细节,他尽心挥洒这些温暖的生命介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为那份“幸运”积攒了力量。
回看过往岁月,王振堂将来到贵州、扎根贵州的际遇也归于一种“幸运”。1962年初秋,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王振堂怀揣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信念,来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以“赵明”为代名,开启了自己“声”动传播的职业生涯。尽管过去条件艰苦,但王振堂依然坚定梦想,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思考,以“在其职,谋其位,尽其力,担其责”的态度兢兢业业,攻克一个又一个从业难关。
2022年是王振堂来到贵州的第60个年头,对于那个“离开家乡北京,奔赴大西南”的决定,王振堂觉得“一切都值得”。在贵州,他收获了友谊,实现了人生价值,见证贵州实现一个又一个跨越。“就像欣赏一朵花一样看着它盛开,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是那浇水的人。”王振堂说。
1998年,王振堂正式告别广播电视播音工作,但退休之后他也没有闲下来,而是继续发光发热。他先后受聘为国内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教学播音主持和广电编导专业,为培育人才贡献余热。他亲和谦逊的教学方式得到了学生的一致喜爱,如今虽已告别讲台多年,但天南地北的学生还是会常来看望他,不断延续难得的师生情。
在那本名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优秀格言选集(五)》的书籍里,王振堂写下了自己的人生格言:做人的真谛在于“诚”,艺术的真谛在于“情”,言语的真谛在于“敬”,成功的真谛在于“行”。短短几句,却是王振堂既定不变的人生信条。笃实践履,修身为本,在王振堂看来,比起不断追问得到了什么,他更关心在有限的生命里,自己是否勇敢天真地充分燃烧过。
>>>>>>>>>>
天眼新闻:王老师,您好。请问在怎样的机缘下,您选择成为一名播音主持?
王振堂:我从小就有一个新闻梦,当时我在北京市第八十三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是学校广播站的小记者。于是我暗暗定下目标,大学一定要考新闻系。

王振堂在长城
高中毕业后,我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现中国传媒大学)录取,在学校学完一年基础课程后,当时国家根据形势需要,提出北广要培养一批专业播音员充实到全国各地广播电台,传播好党和政府的声音,我们学校就根据要求,立即在学院组建了当时国内高校的第一个播音专业,并动员各系优秀学生改学播音专业。
我当时是学习委员,又是共青团员,便响应号召成为学院播音专业的第一届学生。1962年,我们播音专业的28名毕业生,除了一位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其余的同学都分配到了祖国各地的广播电台。我的工作单位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于是,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贵州,成为一名播音主持,开启了热爱的媒体事业。
天眼新闻:您从事广播电视播音工作达30余年,一路走来想必也是苦与乐并存的,在您初入行当时,遇到过哪些尴尬且难忘的事呢?
王振堂:每一位职场新人都有一个磨合期,我当然也不例外。因为电台常常都是直播,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会特别紧张。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发不出任何声音,嘴巴呈现一个僵化的状态,特别是以“硬气声”为主的词,总是卡壳。当节目录完,后背腋下都是一片冷汗。
但这样的状态没持续很久。为了克服紧张情绪,我每天下班之后就苦练,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每到开播之前,我就不断的吐气练声,放松嘴巴肌肉,保持最好的状态。后来,经过不断的打磨,我越来越上手,在业务上渐渐熟悉。

王振堂(右一)和同事们的留影
这些看似失败的经历,我反而觉得是生活中难得的有趣的事,当时是尴尬的,但现在看来,那是每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毕竟没有谁能一蹴而就。我当时负责在电台播报《贵州新闻联播》《报纸摘要》等栏目,那时候我使用的播音代名是“赵明”,后来很多观众问过我这个名字有何意义。其实,这对我来说的确有意义,一是因为我的奶奶姓赵,二是名字与“照明”谐音,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真正做到照明自己,也照亮他人。
天眼新闻: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差错率仅有万分之零点几,这个成绩在全国来说都是少见的。但在播音主持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突发情况发生,您是否也遇到过,如何解决?
王振堂:突发情况在播音室里是常见的事,但是作为一名播音员必须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播报新闻,其中一条是《国务院关于禁止乱砍滥伐森林的通知》,但是原稿上面漏写了“禁止”二字,这是十分关键的两个字,如果不负责的播报,必定会造成严重影响,当我发现了的时候,就及时纠正过来。突发情况是预料不到的,这就要求播音员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和反应能力,以不变应万变。
还有一次,是1979年11月的早晨,我领到一组播报报纸摘要的任务,因为稿子来得很迟,我们没来得及录音,只能当场直播。稿件内容是全国第五届人大开会等重要消息,属于国家大事,红灯一亮就没有备稿时间。但我记得那天,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当时值班的台领导都夸赞我“直播比录音效果还好”。这对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对我平时学习的一次测试,是一次很宝贵的实战经历。
天眼新闻:您后来从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调去了贵州电视台,面对新的媒介,您如何适应,拥有哪些新的体验?
王振堂:1984年,我正式调入贵州电视台工作,在台里刚组建的总编室担任副主任兼党支书。其实,从1972年开始,我就已经陆续参与过电视台的直播工作,对于镜头,我是不陌生的。

王振堂在播报《贵州新闻》
我第一次电视直播是1977年,那时我以主讲身份向观众讲解消防知识。在没有提词器的年代,那20多分钟,我全凭理解记忆和多年积累的播音功底完成任务,那也是贵州电视台历史上的首次电视直播,印象非常深刻。
我调入贵州电视台时,那时候只有一档《贵州新闻》栏目,形式很单一。为了丰富内容,我组织策划了知识类栏目《历史上的今天》以及贵州电视台的第一档音乐节目《歌海拾贝》,后来又陆续开办了《戏剧与曲艺》《艺林春雨》等。
还有一个有趣的体验是,我后来调去了译制部开展工作。我们陆续引进了动画片、故事片、专题片等200余部集,并且部门还自己翻译、导演、配音,建立了自己的配音人才库。我们当时译制的节目广受欢迎,故事片《天堂的雷霆》在全国译制片评比中获得三等奖。
天眼新闻:您在电视台工作期间,还曾机缘巧合地首次提出了“金话筒”名号,可以聊聊这件事吗?
王振堂: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吧。1992年,贵阳举行中国播音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出席会议的有时任国家广电部部长艾知生、贵州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领导,以及来自全国电台、电视台的相关负责人、播音主持人等100多位同行,会议十分盛大。

中年时期的王振堂
当时我作为中国播音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贵州省播音学研究会会长,参与了年会的承办以及组织工作。为了凸显年会特色,我便以“金话筒相聚在贵州”命名此次盛会。因为播音主持人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通过话筒传播人民的声音,传播真理和正能量,我认为这是一个极有意义且“含金量”很高的职业,所以才想到了“金话筒”一词。
那时,“金话筒”这一形象称谓得到当时参会同行的一致认同。如今,“金话筒奖”已是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我对“金话筒”的寄托和期望都实现了,每每想到,还是觉得自豪和骄傲。
天眼新闻:您退休之后,还去了各大高校授课,直到前几年才真正的停下来,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
王振堂: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如果说30多年的工作是在实践中学习,我退休后走上讲台便是在理论中获得新的认知。
到了学校,我更多的重心放在教学上,在教学生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些年,我在教学之余,主编了我国首部播音论著《中国播音学文集》(第一集)以及国内首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试用教材《广播电视节目语体学》,还编著出版了《你能做到标准规范读音吗》一书,收获很大。

王振堂和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播音主持三班毕业留影
人或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悲观和消极,但是通过学习和教授他人新的事物,可以重新找到生活的热情和动力。教书这件事带给我许多珍贵的感动。学生对于我而言,也是生命里的良师,我的观念是“二人行亦有我师”,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人格价值,所以在我的课堂上,学生可以畅所欲言,我的目标是都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最终的结果是符合预期的,我所教授的每一届学生,他们都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王爷爷”。
天眼新闻:您和播音主持事业打了几十年交道,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第二十三个记者节即将到来,您有什么话想对新一代的年轻媒体人说?
王振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不能用过去的眼光审视当下和未来。现在,媒介发生了诸多变化,新一代媒体人面临着无数挑战,同时也迎来了更多新的发展机会。未来如何发展,你们每一个人手里都握着决定权。我希望年轻的同行们能够坚守初心,有立场、有底线、有情怀,努力提升话语的文化品位及其艺术含量,郑重使用话语权,成为舆论导向的真正把关人。同时,年轻的你们也要对新闻怀有一颗真诚的敬畏之心,脚踏实地,深入生活,立足时代,做一个博学而专注、热情而冷静、慎知而笃行的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栏目策划/李缨
文、视频/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秋樾
刊头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浩宇
编辑/覃淋 郭睆秋
二审/李冰
三审/李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