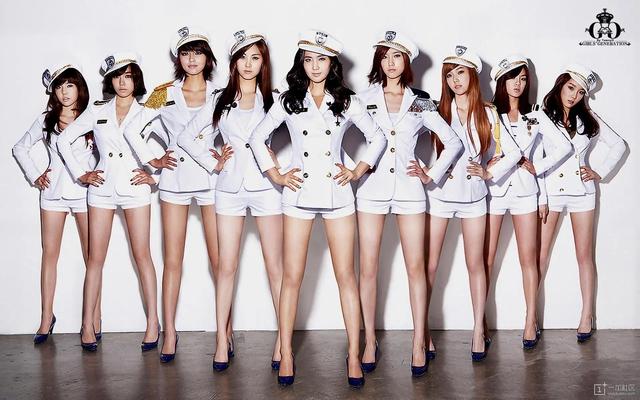【大家】
作者:李大勤(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韵佳(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学人小传
孙宏开,1934年生于江苏张家港。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兼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先后发现15种新语言,并就3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展开系统调查研究。著有《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羌语简志》《独龙语简志》《八江流域的藏缅语》等,主编“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汉藏语语音和词汇》等。

中国境内有多少种语言?这些语言有什么特点?相互之间有何关系?70年来,孙宏开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他登上苗岭,迈进十万大山,翻越岷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喜马拉雅山……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居住的一个个高山峡谷,都留下了他求索的足迹。通过数十年田野调查,孙宏开为世人描画出一幅幅中国语言的壮丽图景。
在田野中淬炼学问
1934年,孙宏开生于江苏张家港悦来乡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家庭。生逢战乱年代,他少年时的求学经历并不顺利,辗转于姨妈家、外祖母家等多地,读了范贤、悦来、天福、合兴四所小学,才勉强完成了小学学业。
那时社会动荡,孙家的经济状况也相当窘迫。学校离家远,他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午饭常常是家里前一天剩下的麦细饭(一种用类似青稞的元麦做成的饭食),再配一点咸菜。如果某一天家里没有剩饭,他中午就只能饿肚子,得一直等到晚上放学回家才能吃上一口饭。三饥两饱是家常便饭。
“那时候我最害怕雨雪天上学,路途遥远又泥泞。夏天光脚走路,问题还不大。一到冬天,尤其是风雪交加的时候,寒风刺骨,那又滑又陷、带着冰碴的泥巴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赤足踩在上面,那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从小学到中学,这样的日子我整整经历了近十个年头。”孙宏开这样回忆。

2005年,孙宏开在四川木里调查史兴语。
1952年,孙宏开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风华正茂的他,对未来有无限憧憬,还曾想过当米丘林那样的科学家:“在高中阶段,我甚至想做这样一个实验:将棉花籽放到凤仙花的根部,棉花籽吸收了凤仙花的养分,会结出像凤仙花那样五彩缤纷的棉花来……”然而,他却被分配到了语言专修科。那是北京大学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设立两年制语言专修专业。
尽管思想有过一段时间徘徊,但在罗常培、袁家骅等师长的开导和影响下,孙宏开还是接受了这个安排。在北大,一位位博古通今、德高望重的学者,一门门量身定制的专业课,指引着孙宏开一步步迈入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广阔天地。罗常培和王均两位先生为他们合开了“语音学”“音韵学”,唐兰先生上的是“文字学”,高名凯先生讲“普通语言学”,俞敏先生上的是“现代汉语”,费孝通先生为他们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金鹏、王辅世、李森分别上藏语、苗语和维吾尔语的语言调查分析课,而给他们开“语言和方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课的是袁家骅先生。孙宏开一直把袁家骅先生视为恩师。袁先生不仅在学业上给他指导,还在生活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精神上不断给以鼓励和鞭策。从那时起,孙宏开就确立了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奉献终生的信念。
大学毕业后,孙宏开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到语言所后不久,吕叔湘先生就要求他写一篇稿子,讨论汉语有没有词类、怎样划分词类。孙宏开交稿后,吕叔湘先生用红笔密密麻麻写了许多批语——“这个分析有点道理”“你这支箭射歪了”……最后,还有一个总评语:“文章下了一番功夫,有些看法有可取之处,但铺排太甚,不够规范,要好好练习写文章的格式和方法。”吕叔湘先生的谆谆教诲,对年轻的孙宏开影响很深。在袁家骅、罗常培、吕叔湘、丁声树、傅懋勣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培养下,孙宏开有了足够的信心和底气投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又经过一次又一次田野调查的淬炼,他逐步成长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民族语言学家。

1976年,孙宏开(左一)等在西藏察隅调查达让语。
1956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组织了一次民族语言大调查活动,600多名民族语文工作者组成了七个工作队分赴全国各地开展调查。孙宏开被分到了第七队,主要任务是调查藏、羌、嘉绒、普米等语言。当年5月,孙宏开就开始在黑水、汶川一带做语言田野调查,走遍了黑水、汶川、理县、茂县等地高山密林中的大多数村寨。1960年,正在四川阿坝调查羌语的孙宏开接到研究所电报,要求他去云南调查独龙族和怒族的语言。他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打起背包直奔云南西部边疆。在几乎没有路的路途上,孙宏开与马帮同行,翻雪山、睡草地、过藤桥、爬天梯,穿过重重原始森林才到达目的地。路上要时时提防毒蛇、蚂蟥的袭击,宿营时则有蚊虫飞扰,常常整夜难眠。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孙宏开完成了对独龙语等语言的深入调查。
记录一种陌生的语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拿羌语来说,从1956年到1958年的这三年,孙宏开和同事们遍访34个调查点,记满了十几个厚厚的本子。调查大都是按照提前准备好的大纲进行的,大纲上列有3600多个常用词。当时羌语没有文字,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反映羌语的实际情况,他都是用国际音标来记录。除了记录词汇,语言调查还要记录句子(一般在400句以上),并尽可能记录长篇故事或会话语料。接下来,就要根据这些语句分析语音、归纳词类,提炼句式、句型和句类等,通过丰富的语言材料全面、清楚地反映出该语言的系统面貌。
民族语言大调查前后积累的丰富语言材料,后来陆续被整理成书稿,纳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出版。其中,孙宏开不仅撰写了《独龙语简志》等三部著作,还参与了这套丛书的日常组稿和审定工作。2009年再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则是由孙宏开主持修订的。
1976年,刚动过胃部手术不久的孙宏开开始参与对门巴、珞巴和僜人语言的调查。在前往调查点的过程中,恶劣的高山环境,让他本就欠佳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加之疟疾、肠胃炎轮番来袭,孙宏开经历了多次虚脱。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下繁重的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他们带回了门巴语、仓洛语、达让语、格曼语等语言的珍贵材料,为学界理清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考察各语言的方言差异情况、客观评估各族群间的远近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80年出版的《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就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孙宏开编著的《羌语简志》
在此前后,孙宏开还受云南、四川等地民委的邀请参与了对白马人、尔苏人的民族识别工作,连续发现并确认了尔苏语、木雅语、尔龚语、史兴语、扎巴语、纳木义语、却域语、贵琼语、白马语、柔若语等新的语言,为后来对这些空白语言的描写、研究奠定了基础。
丰富的语言调查实践触发了孙宏开对语言识别的理论思考,他在《语言识别与民族》(1988)、《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语言识别问题》(2005)等文章中提出并发展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语言识别理论。2009年美国《科学》杂志有专栏就此发表评论,认为应该在孙氏理论的基础上就语言识别问题进一步展开探讨。
调查之后重在保护
根据逐渐建立起来的语言识别标准,孙宏开不断组织学术力量对中国境内语言进行识别。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被识别出来的语言只有48种;民族语言大调查后,增加到了59种;60年代初的补查又将这个数字增加到了64种;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分册》认定的中国语言,也不过80来种。2007年,孙宏开等主编的《中国的语言》出版,收录中国境内语言129种,其中近60种是1976年以后新发现的语言。2017年,由孙宏开参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140种语言百科全书》(英文版)出版,书中共介绍了中国境内5个语系、10个语族、20多个语支共140种语言的情况。该书不仅为人们了解中国语言资源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也以更为详细的材料和明确的语言识别标准回答了“中国语言知多少”这个谜一样的问题。
在调查的基础上,孙宏开很早就开始呼吁并参与濒危语言抢救。20世纪80年代,他在调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就一直致力于保存和保护中国境内各种濒危语言。1992年开始的“中国空白语言调查”、1994年立项的“中国少数民族新发现语言深入调查研究”都是针对中国濒危语言调查研究而提出的研究计划。此外,2003年、2011年,孙宏开先后受邀参加全球濒危语言专家会议,并建议制订《保护濒危语言公约》。

孙宏开撰写的《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
2006年,孙宏开发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一文,把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分为6类:1.充满活力的语言,如蒙古语、藏语;2.有活力的语言,如苗语、哈尼语;3.活力降低,已经显露濒危特征的语言,如羌语、纳西语;4.活力不足,已经走向濒危的语言,如仡佬语、鄂伦春语;5.活力很差,属于濒危语言,如赫哲语、畲语;6.无活力,已经没有交际功能的语言,如满语。通过对民族语言活力排序,孙宏开希望能够分清轻重缓急,率先抢救处在最濒危状态的语言。这篇文章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已被翻译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多个语种,成为各界了解中国民族语言生态现状的重要文献。
在展开深度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大型系列丛书“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陆续出版。孙宏开不仅承担全部书稿的审稿、定稿工作,还撰写了《阿侬语研究》《柔若语研究》《白马语研究》《史兴语研究》等书稿。
“这套丛书比语言简志难度要大得多,主要是这些小语种发现难、调查难、鉴定难、出版难。”作为主编,孙宏开深知丛书编纂的困难,但仍坚持不懈。到目前为止,丛书已经出版了近50本专著,涵盖了中国境内45种以上过去没能得到系统描写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境内语言描写的不足,不仅为世界语言宝库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源,也为国家制定语言文化政策提供了扎实的语言国情依据。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研究也是孙宏开研究的一个重点。20世纪80年代,为了揭示语言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孙宏开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研究”丛书,刘光坤的《麻窝羌语研究》、周毛草的《玛曲藏语研究》、黄成龙的《蒲溪羌语研究》等近20种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专著随之面世。另外,在孙宏开的推动下,由他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也先后出版了《白汉词典》《黎汉词典》《汉嘉绒语词典》等一些小语种的双语词典,以及《汉苗词典(黔东方言)》等一些方言差异较大语言的双语方言词典,总数达20多部。这两套丛书的编纂出版,不仅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专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正式启动,孙宏开参与了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实施及推动工作。彼时已年过八旬的孙宏开,在负责第一期语保工程濒危语言组21个语言点的同时,还身体力行,申请了濒危语言阿侬语的项目,“如果不进行调查和视频记录,这些口头语言很可能就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孙宏开等著《白马语研究》
孙宏开深知,从事民族语言调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留在这个领域,也希望各民族都能够培养出更多本民族知识分子从事本民族语言的保护与文化传承工作。
“要培养一支专业素质好,精干、有事业心、能打硬仗的队伍。这支队伍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能脚踏实地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为培养民族语言研究的后备力量,孙宏开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如今活跃在中国民族语言学界的中青年学者,都是在他的激励、培养、扶持之下走上民族语言研究道路的。
孙宏开对民族语言学界学术力量的培养,从不局限于自己的学生。一个学者,不管你来自南方北方,无论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愿意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并且具备一定语言学基础,孙宏开都一视同仁,热心把他或她引入民族语言研究的队伍中来,不遗余力地加以培养。这样一来,在民族语言学界,有相当一批“跨界”学者——从事白马语调查的魏琳教授是孙宏开从古典文学队伍中拉过来的,从事尔苏语调查的张四红教授来自外语学界,从事贵琼语调查的宋伶俐教授则来自汉语学界。
构建汉藏语历史类型学
早在19世纪,就有语言学家认为汉语、藏语、苗语等在历史上具有亲属关系,由此提出了“汉藏语系假说”。后来的学者又将汉藏语系分为汉语、藏缅、苗瑶等语族,每个语族下又有若干语支、语种。然而,对于汉藏语系有何特征、应该如何分类、语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孙宏开常年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他调查的语言中有很多是汉藏语系的语言,这为他开展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9年1月,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上,孙宏开提交了一篇题为《羌语支属问题初探》的论文,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在川西一带,尚有木雅(弥药)、尔苏(多续)、尔龚、贵琼、纳木义、史兴、扎巴等语言,与羌、普米、嘉绒语也比较接近,很可能划为一个语支。”1985年后,孙宏开又陆续开展了一系列语法专题研究,就羌语、羌语支在藏缅语族里的历史地位,羌语支语言的文化共性展开了进一步讨论。羌语历史地位的确定以及羌语支语言的发现及其定位,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得到国际语言学界尤其是汉藏语系语言学家的高度认可,其学术影响已经扩展到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
在考察汉藏语系语言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孙宏开发现,类型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语言由于分化时间久远、分化线路不同等原因,最后可能各自演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能够把各种语言的演变脉络、各种语言类型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各种语法范畴的语法化路径及机制搞清楚,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构拟出不同层次的汉藏语系语言各类特点(包括同源词和形态标记)乃至汉藏语系的总体特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宏开在吸收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藏语历史类型学”这一新的学术思想。
汉藏语历史类型学涉及汉藏语系音节结构类型及其演变、语法结构类型及其演变、语义的历史演变等多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田野调查所得语言材料的深入分析,孙宏开发现藏缅语中存在着“趋向”“互动”“人称领属”等新的语法范畴,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些语法范畴在藏缅语中的独立语法地位。通过科学严谨的分析,他确认了诸如“体”“态”“式”“人称”“格”等语法范畴也同样存在于藏缅语的各语言之中。此外,孙宏开还对藏缅语中“使动”“数”等语法范畴展开深入研究,揭示出一些不同于印欧系语言同类语法范畴的特点。例如,他在《论藏缅语中的使动语法范畴》(1998)一文中指出,藏缅语的使动语法范畴不仅有使用黏着手段的,还有使用屈折手段及虚词等分析性手段的,而且其中的屈折手段几乎贯穿于声母、韵母和声调等全部音节要素之中。以这些扎扎实实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为基础,他对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展开研究,成功地从语法结构类型演变的共性和差异中透视出了藏缅语内部各语言之间存在着的发生学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与藏缅语音节结构的类型演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只不过不同地域由于受不同环境的影响,演变的速度、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尽管现有语言之间差异程度各不相同,但不同语言中的历史遗存和共同创新都可以成为汉藏语系语言分类的依据。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撰写《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导论时,孙宏开就尝试通过揭示藏缅语同源词背后的主要语音对应规律来建立藏缅语族语言语音演变类型的理论框架。而后,在讨论藏缅语部分音变源流、原始汉藏语复辅音类型、原始汉藏语音节构拟等问题的过程中,孙宏开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汉藏语各语言中复杂多样的语音变异现象体现的是各种语言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或演变阶段。
为了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手段在整理汉藏语系资料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孙宏开的指导和推动下,“130种语言的词汇和语音数据库及检索系统”“汉藏语同源词数据检索系统”“东亚语言词汇语音数据检索系统”等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平台先后问世。这些平台在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汉藏语研究尤其是汉藏语系假说的论证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汉藏语研究在语料的积累、整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基于新发现语言材料的同源词研究和语音对应规律的提取也开始取得更多的共识;对汉藏语系语言在语族、语群乃至语支层次上的分类较之前人也更加细致、具体、科学,对汉藏语系在历史遗存和共同创新两个方面的总体特点也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而在理论方法的探索方面,以孙宏开提出的汉藏语历史类型学为代表的基于中国境内语言事实的理论创新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都为最终解决汉藏语系假说的论证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孙宏开先生已是米寿之年,他没有停下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脚步,还在拓展着他的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研究。他始终践行着年轻时的那个誓言——“把一生献给我热爱的民族语文研究事业”。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9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