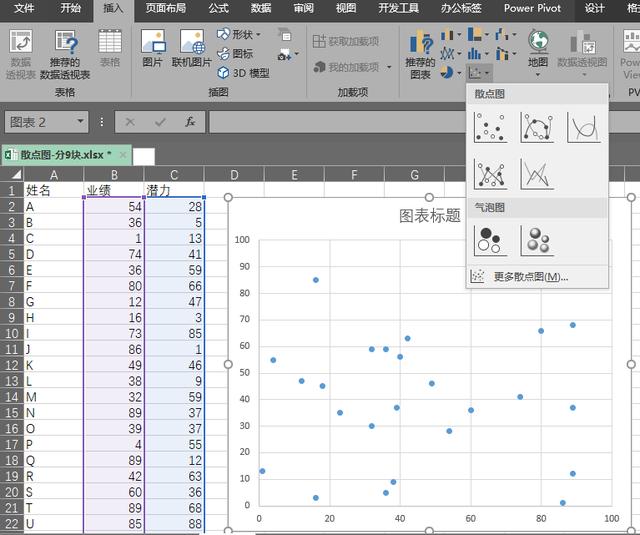一
黛青色长衫松垮地搭在烟绿色的长袍上,一条窄窄的丝绦随着主人春山上下台阶的步子左右飘动,若有似无地缠绕着腰间的秋香色葫芦。
“半晌不见人影,不在殿内诵经,又钻哪个竹林子里去了。”
音尘和尚伸手拂去对方青丝上沾着的蛛网,轻抬脚步朝她走来时,落在乌桕叶上的声音如同蚊呐。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佛家中人以杀生为戒,故而处事谨慎,对生灵万物抱有敬畏之心,唯恐一足失慎,徒造杀孽。
“我在这山上已经几日滴酒未沾了,还不准我去后山挖个陷井,逮个野兔子烤烤。”
春山就着爬满青苔的石阶坐下,摸起腰间的葫芦,就要往嘴里倒水,一滴,两滴,最后一滴迟迟不落下。
“半点荤腥未沾着,呜呜,这水也见底了。这破庙——”就差点说出晦气两个字了。
“既来之则安之。”
风吹动乌桕叶的影子,斑驳地映在音尘和尚光亮得一闪一闪的脑门上,洒落几星子滴在缝制了琥珀色绣线的袈裟上。
春山跟在音尘和尚的身后不言不语,像是有人往她嘴里塞了几大坨棉花。
飞流激泉在山间小道拢成轻烟薄雾,仿佛天然的屏障隔绝了山脚下扑上半山腰的热气,晃晃悠悠地又绕到音尘面前,一场山雨欲来。
二
一场不期而遇的山雨像个未晓世事的孩童,扑湿了晒在藏经阁殿外的经书。
雨霁初晴,春山和小沙弥一块儿吃力地将昨日被雨水打湿的经书从小楼阁里搬出来,一本一本地摊开。
“音尘师父去了何处。今儿个怎么没个人影?”
春山的纤纤细手上薄薄的茧子摩挲着经上的佛语,目光却落向了远处。
音尘师父袈裟上的琥珀色绣线在红烛与风的纠缠下忽明忽暗,施施然朝对面女施主行了一礼。
“今儿个元宵,是庙里的盛会,师父自然忙些。”
小沙弥说话的时候,脸上的嫩肉就微微颤动,叽叽喳喳的像林子里早起的雀儿。
“那位女施主可是大手笔呢,前些日子在庙里设了往生灯,那灯芯和蜡油都是外邦的贡品呢。”
春山蝴蝶似的睫毛上下扇动,停下了手上翻书的动作,饶有兴味地问道了一句。
“空明,那往生灯祭奠的是谁,好生尊贵。”
小沙弥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佛说:“不可说。”
那日,音尘和尚忙着为香客诵经解签,直到暮鼓和着山间清泉泠泠作响,飘去渺远的天外。
佛教中认为,“钟”对于修道是有大功大德的,“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味”。
三
春山和空明在庙里的长阶上放上琉璃盏,陆续注入香油,点燃后听火舌摩擦着空气,发出哔剥哔剥的声音,在暗夜里炸出鎏金似的灯花,散落细小的星子。
殿内传来打坐的大师们唱乐的经文声,伴着空中旋转着的水花一圈一圈地涤荡着众生心中的杂念。
音尘跪坐在藏书阁的案牍边,一袭袈裟在烛火中明明灭灭,不知是已经抄了几卷经文,累成了厚厚一叠,不知是在替谁超度生前的罪孽。
春山于朦胧的光影里,隔着迷雾的雕花镂空的扇页里,隐约瞧见音尘光亮的脑门上长出了长发,像蔓草似的缠绕过耳边,爬了满肩。
“如此,也算是个风华绝代的少年。”
正是神往之际,似有人轻拍她的肩膀,睡意朦胧之际回眸一瞥,音尘的身影跌入她的瞳孔中,恍若银河落入九天凡尘。
疲倦已极的春山歪头睡去,音尘的样子与梦中的好多个她日思夜想的身影重叠。
“春山,我捡了只兔子回来,晚上给你最做爱吃的红烧兔头。”
一张朴实的沾着灰尘的脸,套着一件旧麻袋改成的短衫,他提了提手中的酒瓶,又道:“从酒庄赊了半壶梨花酿。”
可是音尘大师不吃肉也不喝酒,哪里会是同一个人呢?
细雨飘进楼花的窗棂,斜斜地打在脸上却并不冰凉,轻微不察。
长生殿遭遇雷霆之击,一时间飞石碎瓦如无头苍蝇般乱飞,击碎了好几盏往生灯,琉璃盏碎片飞溅,扎在墙上的经文里。
和尚们都急急起来,拽了灯笼踏雨前去,闹哄哄一片。
春山掀开锦衾欲前往查看,却惊觉玉足消失,只能如薄纸片般任风驱使。
原来,她已经死了,长生殿里日日供奉的往生灯是为她燃着的,哪里是空明胡扯的什么女施主供奉的,那或许是空明作为出家人打的唯一一句诳语。
她看见音尘光亮的脑袋从雨天的泥坑里冒出来,拖着沾满淤泥的布鞋猛地冲进长生殿内,望着将将熄灭的往生灯,痛哭流涕。
原来,那不是梦,音尘曾蓄着长发由春山仔细地绾起,插上一根木簪。
今儿个是头七过后的第三天,我记起了孟婆汤掩藏起来的我和音尘之间琴瑟和鸣的时光。
我的身形在鸦青色的夜里消散,此后只有很少的人会记得有个情根深种的人为我做了和尚,日日为我抄写经文,诵经超度。
关注公众号辞忧馆,看更多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