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学在宋代开始形成。作为一代文坛宗师,欧阳修的晚唐诗学观是宋人晚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关于晚唐诗的说法有二,均见于他晚年所作的《六一诗话》。其一云:“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其二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尽管欧阳修关于晚唐诗的看法不过寥寥数句,却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涵,涵括了“晚唐”之名、晚唐诗风和晚唐诗批评等几方面的内容,并且在当时和后世的晚唐诗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唐”之名
诗学中的“晚唐”之名,大约在北宋中后期出现。在此之前,已有许多与之相关的说法,欧阳修所说的“唐末”和“唐之晚年”是其中的两个。“唐末”在宋初出现,是当时论诗的常言,欧阳修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并无独异之处。有独异之处的用语是“唐之晚年”,该说法最早见于欧阳修壮年时所作的《朋党论》中,他在晚年作《六一诗话》时,沿袭了“唐之晚年”的用法,大约正是从这个用法中衍生出了后来的“晚唐”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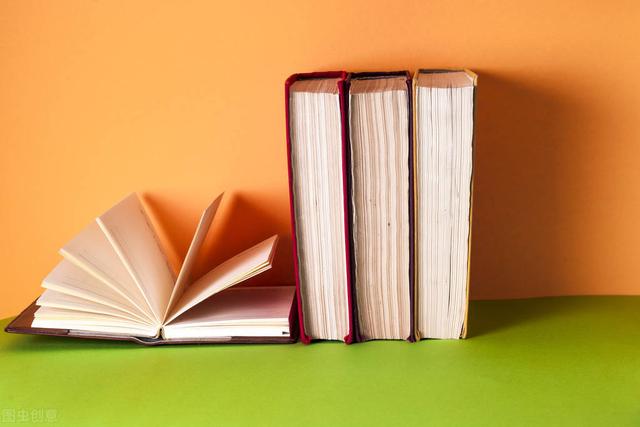
“唐之晚年”的说法对后人的晚唐诗论述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的论者沿用这个说法而内容有所变换,比如张耒把“唐之晚年”的代表诗人,由作诗重视构思和“锻炼”的周朴,置换为“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的孟郊和贾岛。周朴与孟郊、贾岛虽都刻琢苦吟,但从他们在后世的知名度来看,孟郊、贾岛远胜于周朴。欧阳修与梅尧臣在长达二十年的诗歌唱和中,频繁以韩愈和其门人孟郊、贾岛自比,并影响了苏轼,催生了著名的“郊寒岛瘦”之说,孟郊和贾岛成为当时谈诗者的话头。就此而言,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把刻琢苦吟的代表从周朴置换为孟郊、贾岛,也就不足为奇了。南宋中后期,“永嘉四灵”学习姚合、贾岛等人,其诗被称为具有晚唐诗风。此后,贾岛、姚合被归为晚唐诗的代表,南宋的刘克庄和宋元之际的方回持此类议论最多。相比之下,周朴逐渐不为人所知,到清代乾隆年间李怀民撰《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时,列贾岛为“清真僻苦主”,而周朴则已不入图。有宋一代,论及晚唐诗的代表,绝大多数人均以贾岛为代表,追溯起源,则辗转与欧阳修有关。
有的论者如清人彭端淑在引用欧阳修之说时,直接将“唐之晚年”置换为“晚唐”。还有许多论者撮述“唐之晚年”而得出“唐晚”之说,在宋人杨万里《朝天集》、方岳《深雪偶谈》、姚勉《雪坡舍人集》乃至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皆有此说法。更有甚者如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衍生出“入晚唐”“不特晚”“不止晚”“晚唐之尤晚者”等说法,充分发挥了“唐之晚年”的意涵。
晚唐诗风
欧阳修列举的晚唐诗风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以郑谷为代表的俗白易晓,一种是以周朴为代表的重视构思和“锻炼”。
在欧阳修看来,郑谷诗的佳处在于有意思、多佳句、易于理解,故可教小儿,短处在于诗格不甚高。“晚唐”之说兴起后,“格卑”的论断便由评价郑谷而扩大化,成为整个晚唐诗坛的标签,这是宋人的普遍看法。比如,孔平仲谓“唐末”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诗老妪能解,近于鄙俚,其说跟欧阳修一样,皆就诗歌在文字方面的俗易浅近而论。蔡居厚也说,“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但其说已由着眼于文字之俗转变为批评文字之工巧。这种转变与当时论诗讲究文字工拙的风气有关,这就涉及欧阳修所说的第二种晚唐诗风,也就是作诗重视“锻炼”。
关于晚唐诗风讲究构思和“锻炼”,是更为著名和影响深远的说法。欧阳修的这一看法在当时及后来皆有响应,而且成为主流意见。比如,以欧阳修门人自居的刘攽说,“唐人为诗,量力致功,精思数十年,然后名家”,其意与欧阳修论周朴近似,但所论已由晚唐诗人扩展为整个唐代诗人。沈括也说,“所谓旬锻月炼者,信非虚言”,推而广之,他把“锻炼”当作所有诗人作诗之法,而唐人尤其如此。后来南宋张镃引沈氏此说时将“旬锻月炼”写为“月锻季炼”,这一有意或无意的转写正说明,在张镃看来,沈括之说取自欧阳修。等到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在诗坛蔚为大观时,他们讲究“点铁成金”和“活法”的诗法大行于世,比之讲求构思和“锻炼”的晚唐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杨万里作诗曾取法晚唐诗和江西诗派,极夸晚唐诗“锻炼之工”,故周必大称道杨氏,“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对比欧阳修所说的“月锻季炼”、沈括所说的“旬锻月炼”和蔡居厚所说的“日锻月炼”,周必大一变而为“岁锻月炼”,苦吟的时间更为久长,也更切合贾岛自陈“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诗经验。因此,对于晚唐诗之“锻炼”,他们是深为心契的。
晚唐诗批评
欧阳修将“李杜豪放之格”与“唐之晚年”之人如周朴的“月锻季炼”作比较,只是显示两种诗风的不同而未有高下之分。李杜与晚唐诗人的对比,后来成为一种模式。比如,刘克庄说,“郊、岛辈旬锻月炼而成者”,“与杜公相颉颃”的岑参“谈笑得之,辞语壮浪,意象开阔”。至于清人王士祯所说,“予尝观唐末五代诗人之作,卑下嵬琐,不复自振,非惟无开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韵兴象之妙,以视陈、隋之季,盖百不及一焉”,更是直接模仿了欧阳修将李杜与晚唐诗人进行比较的思路。
李杜与晚唐诗人的对比,在欧阳修看来只是风格的不同,并未妨碍他对二者各有赞赏。但这种比较后来演变为“杜甫与晚唐”的对举模式,包蕴着诗学价值等级高下之意,后世论者往往取杜甫而弃晚唐。李杜与晚唐诗人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由黄庭坚所建立。他在给赵伯充的信中写道:“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其弊若何?”作为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的这一说法很有分量,响应者不少。比如,曾学江西诗派的陆游便说:“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作为江西诗派殿军的方回,更是批评“晚唐诗千锻万炼”,却只知“色相声音”,颇为拘束,不如师法杜甫的江西诗派,更远不如杜甫。因此,面对江西诗派、晚唐诗人和杜甫时,所当取法的对象不言自明。方回还以贾岛诗为例,批评“晚唐诗多先锻景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换言之,“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与之相反,“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元人牟巘感叹“世之为晚唐者,不锻炼以为工,则糟粕以为淡。刻鹄不成,诗道日替”,正是掇拾欧阳修、黄庭坚的观点而成说。
江西诗派之后,代之而兴的“永嘉四灵”带动了晚唐诗风的盛行,产生诸种诗弊,论诗者又返回李杜尤其是杜甫,要求以之为法。持论激烈者在主张以杜为法的同时,还以晚唐诗为戒,如陈著便说,“莫向晚唐中入局,须从老杜上加鞭”。即便是喜爱和学习晚唐诗之人,也在不废弃晚唐诗的同时,以学杜甫为主。比如,陈鉴之赠人诗云:“今人宗晚唐,琢句亦清好。碧海掣长鲸,君慕杜陵老。”承认晚唐诗“琢句”和“清好”的优点,其“琢句”对应的是欧阳修谓“唐之晚年”诗人“月锻季炼”之说;第三句用杜甫《戏为六绝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对应欧阳修谓李杜“豪放”之说;末句卒章显志,认为受诗者应师法杜甫掣鲸碧海的雄壮之风。陈必复也说:“余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澹自赏,要皆自成一家。及读少陵先生集,然后知晚唐诸子之诗,尽在是矣,所谓诗之集大成者也。不佞三薰三沐,敬以先生为法。虽夫子之道,不可阶而升,然钻坚仰高,不敢不由是乎勉。”这段话虽含有晚唐诗与杜甫高下等级不同之意,但未否定晚唐诗的价值。察其意,陈必复初时爱晚唐诗,后来读杜诗而知山外有山,于是努力师法杜甫。
至宋末,严羽提出以李白杜甫作为盛唐诗人群体的代表,要求“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由此发展出将盛唐与晚唐对照并尊盛黜晚的论述框架,构建起了唐诗学分期批评中最重要的批评模式。后来不管是元人杨士弘,还是明人高棅,在初、盛、中、晚唐四期之说中尊盛黜晚,都遵循了严羽在唐诗学分期批评中建立盛唐与晚唐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并将其绝对化的做法。而追溯其来源,这一批评模式正是在欧阳修以李杜和晚唐诗人对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欧阳修的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研究”(FZW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裕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