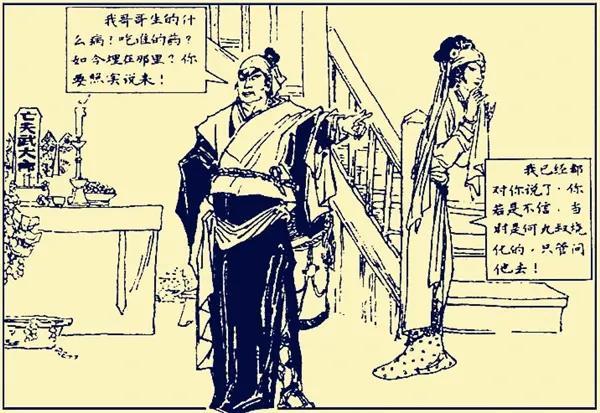一
鲁迅对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作过高度的评价。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明代「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称赞《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他不同意对该小说进行贬低或作歪曲事实的错误评论。他的如下见解是正确而全面的: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他肯定并称赞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世情,尽其情伪」,「爰发苦言,每极峻急」。他不否认作品中「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但他反对世俗评论者「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
显然鲁迅是不同意给《金瓶梅》一个「恶谥」,把它骂作「淫书」的。
鲁迅指出作品中有「猥黩」的描写,「在当时,实亦时尚」,故而不应作苛刻的责备。
本来在评论文学作品时,就应该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在尚未弄清《金瓶梅》作者全人的情况下,至少也应该了解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和顾及《金瓶梅》全书,这样总可以避免较多的片面性。
鲁迅还称道「《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我们自不应因为书中「间杂猥词」,而一笔抹杀「其他佳处」。
《金瓶梅》这个婴儿的出生,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者们对此作过详细的阐说。
凡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婴儿身上有污秽和血,就连婴儿一起抛掉。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明代讲世情的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
并称赞「《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这也是赞美「《金瓶梅》作者能文」之意。
鲁迅还在〈论讽刺〉一文中,把《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的情节内容,评为「直写事实」而具有讽刺性的典范。这些论述精当而深刻,对广大读者都有指导性的意义。
但毋庸讳言,鲁迅在论述《金瓶梅》时,也有一些失于严谨之处。
这些失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有的已经指出,有的却未指出。同时,在该版《鲁迅全集》中对《金瓶梅》问题作注时,也出现了一些谬误。
这些,都有待于以后再版时予以修订改进,以使《鲁迅全集》更臻于完美。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鲁迅全集》
二
鲁迅在论述《金瓶梅》问题时,大体上有以下一些失误:
1. 应据明代《金瓶梅词话》本,而不应据清康熙时张竹坡刻本。
《金瓶梅》的版本很多,而存世的主要有三大版本:
(一)《新刻金瓶梅词话》(明万历至天启刻本);
(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明崇祯刻本);
(三)《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清康熙时张竹坡评刻本)。
鲁迅于1923 至1924 年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时,《金瓶梅词话》本尚未发现,崇祯本也很难见到,社会上通行的是张竹坡评刻本,鲁迅只能依据后者。
《金瓶梅词话》1932 年发现于山西省介休县。到北平后即发出征订通知,于鲁迅于同年便预订了一部,并付了款。
次年(1933 年)春,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了一百零四部。鲁迅于同年5 月31 日在上海收到了一部(见《鲁迅日记》)。
1935 年《中国小说史略》出第十版时,鲁迅应依据《金瓶梅词话》,将小说引文和其他有关文字作一番改订;但由于鲁迅当时太忙,未能做这一工作。
鲁迅是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讲〈明之人情小说〉时,论述《金瓶梅》的。
《金瓶梅词话》是存留于世的该小说最早的刻本,它最接近作者创作的这一小说的原貌。
崇祯本与张评本与这一小说的原貌较远,在小说的价值上远不如词话本。因此,在论述时应该以《金瓶梅词话》本为根据。鲁迅在1935 年所作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
「改订《小说史略》的机缘,恐怕也未必有」。因为鲁迅当时已实无余暇。
他又谦逊地说:「但愿什么时候,还有补这懒惰之过的时机。」可见他还是很想做一番改订工作的。
可惜的是鲁迅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间,1936 年就逝世了,遂未能补做这一工作。
词话本与张评本的文字很不相同。举例来说,下面左栏鲁迅据张评本所写或引用的文字,都应按右栏词话本中的文字予以改订:
鲁迅据张评本
「又得两场横财,家道营盛」。
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
又称敬济为弟,
敬济亦列名军门,
「……想起一件事来,我要说又忘了。」
藏春坞……」
那秋菊拾着鞋儿说道,
「……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
去,……」
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
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
西门庆即令书童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
(表1)
应据词话本
「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
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经济,
又称经济为弟,
经济亦列名军门,
「……我想起一件事来,要说又忘了。」
…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坞……」
那秋菊拾在手里说道,
「……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了。」
向前花枝招飐磕头。
因索纸笔,要留题。
西门庆即令书童连忙将端溪砚研的墨浓,
(表2)
另外有的引文是词话本中所无的。

《新刻金瓶梅词话》
以上均须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说明鲁迅依据的不是词话本。
2. 袁宏道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逸典」,而非「外典」。
鲁迅说《金瓶梅》「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觞政》),故声誉顿盛」。
按此处所写有误。袁宏道在《觞政‧十之掌故》中说:
「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等为内典。
《蒙庄》《离骚》《史》《汉》……,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见《袁中郎全集》卷三)
显然,鲁迅说袁宏道称《金瓶梅》为「外典」,当是「逸典」之误。此误是从沈德符《野获编》而来的。
《野获编‧金瓶梅》条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
鲁迅沿用沈说,而未核对袁宏道原文,致有此误。
- 3. 万历庚戌年(1610)尚无《金瓶梅》初刻本;初刻本最早付刻在万历丁巳年(1617)冬,刻成于天启元年(1621)。
鲁迅说《金瓶梅》「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
鲁迅已注明他的这一论断来自《野获编》卷二十五。然而鲁迅的这一判断是有疏误的。
《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条中说: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
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文中说的「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合公历为1606 年;「又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公历1609 年;后面有「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鲁迅以为这「未几时」,当是「己酉(1609)」的次年,即万历庚戌(1610)。
于是他根据推断,下结论说:「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但鲁迅忽略了「未几时」之前,还有「马仲良时榷吴关」之事。
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指出:马仲良(名之骏)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以户部主事之职,派苏州浒墅关榷收船料钞(见魏着〈《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 年8 月初版本)。
据此可知,鲁迅说1610 年「吴中始有刻本」,是不对的。
大陆学者刘辉、黄霖、周钧韬、李时人等先生也指出了鲁迅此误。

《万历野获编》
明‧薛冈在《天爵堂笔余》中说自己见过《金瓶梅》初刻本,「简端」有东吴弄珠客所写的序文一篇。
而此序末尾所署的时间是「万历丁巳季冬」,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冬季。可见《金瓶梅》初刻本不可能刊行于1617 年冬以前。
《金瓶梅》初刻本刊行的上限为1617 年冬,下限为天启元年,即1621 年。
据刘辉先生引清康熙十二年序刻本《浒墅关志》卷八〈榷部〉所载,马仲良「榷吴关」任期仅一年,即万历四十一年(见刘着〈《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如果按公历算,万历四十一年当是1613 年至1614年。在这之后的「未几时」,显然不可能是1610 年。
我发现《金瓶梅词话》中先刻有几次坏人花子由,后来十多次改刻为花子油,是为了避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所以十多次把「由」改刻为「油」,全书一百回应刻成于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
4. 武松误杀者为李外传,而非「李外傅」。
鲁迅在叙述《金瓶梅》故事情节时写道:「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按:这里的「李外傅」系「李外传」之误。
《金瓶梅》第九回〈西门庆计娶潘金莲武都头误打李外传〉中云:
「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专一在县、在府绰揽些公事,往来听气儿撰钱使。若是两家告状的,他便卖串儿;或是官吏打点,他便两下里打背。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叫做『李外传』。」
以上是词话本中的文字。崇祯本和张评本第九回〈西门庆偷娶潘金莲武都头误打李皂隶〉中的此段文字基本相同,均作「李外传」,不过是将「撰钱」改为「赚钱」而已。「撰」「赚」
在此处音、义相同。因为这个姓李的皂隶善于把县、府里的消息送到外面去赚钱使,所以人们送给他一个诨名为「李外传〔zhuàn〕」。
这里的「传」,谐的是「赚(撰)钱」的「赚(撰)」之音。
鲁迅误为「李外傅」,是由于「传」的繁体「传」与「傅」的形体相近似所致。
5. 春梅买孙雪娥而折辱之,并非因「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将雪娥「旋卖于酒家为娼」的「酒家」,应作「洒家店」。
鲁迅在复述小说内容时说:「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
其实《金瓶梅》中写春梅买孙雪娥而折辱之,是为了「报平昔之仇」。
春梅与雪娥结仇甚深,远在第八十六回「雪娥唆打陈经济」之前。例如第十一回,雪娥与春梅就曾对骂,以致潘金莲激西门庆踢骂了孙雪娥,接着又打了她几拳,后来又采过她的头发,尽力打了几棍。
小说中并没有写春梅在买雪娥之前,知道雪娥曾唆打陈经济之事。因而说「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是无根据的,不具有科学性,出于记误或想当然。
后来春梅叫薛嫂领出雪娥,嘱其务必卖于娼家;薛嫂不忍,卖给了山东卖棉花的客人潘五;没想到这潘五并非是真正的卖棉花客人,而是一个「水客」(人口贩子),买她来做粉头,载到了临清的洒家店。
第九十三回介绍这「洒家店」说:「有百十间房子,……妓女都在那里安下」。
第九十四回也说这洒家店「有百十间房子,都下着各处远方来的……娼的」,其性质正如该回所说,是一个「娼店」。
鲁迅写为「酒家」,显然不够恰当。「洒家店」的「洒」字,和「酒」字形体相近,这当是鲁迅将「洒家店」误为「酒家」的原因。
6. 春梅「夙通」的不是周守备「前妻之子」,而是周守备的老家人周忠的次子周义。
鲁迅在叙述故事情节时说:「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按:此处所写内容有误。周守备(名周秀)前妻无子,其妾孙二娘亦仅有一女。
庞春梅册正为周的夫人后,常与周秀的老家人周忠的次子周义(年十九)私通(亡年二十九岁)。
无论是在《金瓶梅词话》本中,还是在崇祯本、张评本中,都是这么写的(均见第一百回)。

影松轩本
7. 成化时,有方士名「李孜省」,而非「李孜」。
鲁迅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按:「李孜」之名有误,应是「李孜省」。
《明史》卷三○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中有李孜省列传和继晓列传。〈李孜省传〉云:
「李孜省,南昌人。……时宪宗好方术,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
……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益献淫邪方术,与芳等表里为奸,渐干预政事。
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监事。……故事,寄俸官不得预郊坛分献,帝特命以孜省。
廷臣……无敢执奏者。……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然权宠皆出孜省下。
居二年,进左通政。……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
可见鲁迅所说的「在当时,实亦时尚。……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
其基本论断是正确的。但他所写的「李孜」人名有误,「孜」下夺一「省」字,应作「李孜省」。
8. 《金瓶梅词话》被发现于山西介休,而非「北平」。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
按:《金瓶梅词话》实于1932 年被发现于山西省介休县,是由北平琉璃厂古旧书店「文友堂」太原分号的员工在介休县收购的;到北平后,为北平图书馆所购买。
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兼北大教授马廉(隅卿)先生集资,用「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于1933 年3 月影印了一百零四部,鲁迅在上海订购得一部。
但发现地点不在北平,而是在山西省介休县。
9. 鲁迅在上序中说《金瓶梅词话》中的人物对话「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未免绝对化了。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他对山东话并不熟悉。他的这一论断是受有郑振铎、吴晗文章的影响。
郑、吴也是浙江人,也都不熟悉山东的方言。实际上《金瓶梅词话》自始至终,包括人物对话在内,既有山东话,也有江苏、北京、河北、河南、山西话。
已有研究者们举出了不少的实例。该小说语言现象很复杂,何况是四百多年前的语言。

山西介休本《金瓶梅词话》1932
三
2005 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关于《金瓶梅》问题,也有一些错误、欠妥或失注之处。这些地方大致是:
1. 应该注明「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之推断有误。
关于这一问题,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我在前面对鲁迅此处推断之误已言之甚详,这里不再重复。
《鲁迅全集》第9 卷页186 在「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之后,应加注解符号〔4〕,应在页193 加注〔4〕,注明鲁迅的这一推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一事,因而在时间上是不对的。
《金瓶梅词话》应刻成于天启元年(1621)。
2. 未将「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注出。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金瓶梅》「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
由此复生谰言,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
《鲁迅全集》第9卷页194 注〔5〕中,只注明了传说王世贞置毒于纸,以杀唐顺之(号荆川)之事,而未注明「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出自何处。按此传说亦见佚名《寒花盦随笔》。其中说,某日唐顺之遇王世贞(号凤洲)于朝房,
「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尔。荆川索之切。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
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指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
此处所说的「东楼」,即严世蕃号。鲁迅所叙「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当本于此。
《鲁迅全集》第9 卷页194应将这一传说补注进去。否则,广大读者不易明了鲁迅的这一表述出自哪里。但在《寒花盦随笔》中是否定这一传说的,而它只肯定毒死唐荆川之说。其实唐荆川也不是被毒死的,见《明史》卷二0五。
3. 应注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金瓶梅》时,依据的不是《金瓶梅词话》本。
在2005 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以前,197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一种《中国小说史略》征求意见本。
该书页268 注〔2〕解释《金瓶梅》时说:「此书有词话本和非词话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有关《金瓶梅》内容介绍和摘引的原文,均据非词话本。」
这段说明很有必要,但《鲁迅全集》后来的注释本都把它删掉了。
以后《鲁迅全集》出新修订版时,应将这样的说明性文字再加进去。
4. 应该注明「李外傅」系「李外传」之误。
关于这一点,前面也说得较详,此处不再赘述。《鲁迅全集》第9 卷页194 应当加一条注释,说明「李外傅」是「李外传」之误。
5. 应当在《鲁迅全集》第9卷中增加注释。
注明春梅买孙雪娥而折辱之,并非因「憾其尝『唆打陈敬济』」,而是为了「报平昔之仇」;应注明「陈敬济」在《金瓶梅词话》中作「陈经济」;并注明将雪娥「旋卖于酒家为娼」的「酒家」,应作「洒家店」。
关于此,前面也已详谈,这里不予重复。
《鲁迅全集》中应该增加一条注释,予以订正,以使读者能够准确地了解有关情节内容。
6. 应注明春梅「夙通」的不是周守备「前妻之子」,而是周守备家人周忠之次子周义。
关于这一情节内容,前面亦说之甚详。《鲁迅全集》中对此也应该增加一条注释,说明鲁迅叙述的这一情节内容有误,指出「前妻之子」应作「家人周忠之次子周义」。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日文版封面)
7. 应注出「李孜」系「李孜省」之误。
鲁迅所写的「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鲁迅全集》中失注。,应该增加一条注释,将《明史》中的本事写出。
如前所说,鲁迅此语中有误,「李孜」应作「李孜省」,在注释中须对此作一订正说明。
8. 鲁迅所写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无误,而《鲁迅全集》注释中说「应作北平古籍小说刊行会」实误,应予订正。
鲁迅1933 年5 月31 日日记中写道:「上午收到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景印之《金瓶梅》一部二十本,又绘图一本,豫约价三十元,去年付讫。」鲁迅的这段文字本无误。
然《鲁迅全集》第16 卷页381 注〔24〕却云:「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应作北平古籍小说刊行会。……」
我复核了这种影印本及其翻印本,扉页有「二十二年三月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字样;影印本还在第一回开始和第一百回结尾处,各印有一颗同样的竖式长方形篆体红色印鉴,文字是「古佚小说刊行会章」。
可见鲁迅所写的「古佚小说刊行会」是正确的;而《鲁迅全集》的注释中说「应作北平古籍小说刊行会」,反倒弄错了,应该在以后重印时订正过来,即应将以上此注文中的十一个字及句号删掉。
9. 将《金瓶梅词话》注为「万历年间刊行」不妥,应改为「万历至天启年间刊行」。
《鲁迅全集》第6 卷页361 注〔5〕云:「……明万历间刻印的《金瓶梅词话》」,第12 卷页447 注〔1〕也说「《金瓶梅词话》……万历年间刊行」,第13 卷页148 注〔1〕也说「明万历刻本的《金瓶梅词话》」,第17 卷页367 末二行与页368 首行更说「金瓶梅词话……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这些注释都不全对,是都需要改正的。
《金瓶梅词话》只是付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冬,而刻成于天启元年(1621),正确的、科学的称谓应是「明万历至天启间刻本。」
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认为「《金瓶梅词话》于天启初年改成刻出」[1]。
论据是第七十回与七十一回写西门庆到东京后的冬至,恰好是泰昌元年和天启元年冬至的两个日子。
第一个日子(十一月廿八日),只是魏先生的「推想」,而且说「不是十一月廿七日,便是十一月廿八日」;第二个日子(十一月初九日)的推断,却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只是第二个日子可靠。
这有可能是《金瓶梅》作者所写正好与天启元年冬至的日子巧合。我认为《金瓶梅词话》刊行于天启初年,论据与魏先生所说不同。
我的证据是:东吴弄珠客作的序末署的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冬,这是付刻时间;刻板中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于1620 年夏历九月初六日登基,《金瓶梅词话》从第十四回到六十一回,一个刁徒泼皮花子由的名字出现了四次,但第三十为了避天启皇帝「由校」名讳,十多次把「由」改刻为「油」。
这就证明了《金瓶梅词话》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冬付刻的,而刻成于天启初年(1621)。
《鲁迅全集》中多次把《金瓶梅词话》注为万历年间刊行,依据的是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末尾所署「万历丁巳季冬」,但这只是付刻时间,并不是刻行时间。
因此,《鲁迅全集》中的这几处注文有误,应当改注为「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刻行」。
10.将「兰陵」注释为「今山东峄县」,或「今山东枣庄」,都不够全面,也不符合科学;「兰陵」实有两地,另一处在今江苏武进。
《鲁迅全集》第9卷页193 注〔1〕说:「《金瓶梅》兰陵笑笑生撰,真实姓名不详。兰陵在今山东峄县。」
第6 卷页361 注〔5〕说:「《金瓶梅词话》……欣欣子的序文则说是『兰陵笑笑生』作。按兰陵,即今山东枣庄。」
峄县今已划归枣庄,说是峄县或枣庄,是一个地方。
其实「兰陵」的另一地在今江苏武进,见《读史方舆纪要》《隋书‧地理志》《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注释不应片面,而应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金瓶梅》作者究竟是山东峄县人,还是江苏武进人,学术界尚有争论,现正在继续探讨中。
这两条注释应作修改,这才是对科学负责的态度。研究者们指出:《金瓶梅》,屠本畯读后,抄本最初于万历二十年(1592)以高价卖给江苏金坛的王肯堂二帙(二册)又到王穉登苏州的家中见到抄本二帙。
万历二十四年(1596)江苏华亭人董其昌已有抄本全书之半,江苏吴县令袁中郎借而抄之。
后华亭徐阶家已有抄本九十五回,徐家的女婿刘承禧抄录之。万历三十七年(1609)刘承禧客居江苏镇江,袁小修去拜访他,本年袁小修从镇江去北京考进士,已携有《金瓶梅》抄本九十五回,缺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五回。
万历四十五年(1617)冬,抄本「凡一百回」付刻于苏州。天启元年(1621)《金瓶梅词话》刻成印行于苏州。
由以上看来,抄本暗卖、借抄、付刻、印行是在江苏,而不是在山东。
「兰陵」应是江苏武进。研究者们指出该小说中有江苏话、浙江话、山西话等等,语言大师侯宝林说该书中基本上是河北方言。鲁迅说是山东方言,其实鲁迅并不懂山东方言。
我是山东人,长辈们都说山东话,都不认为该书中是山东方言。明清小说基本上用北方话写作,《金瓶梅词话》亦然。
1981 年版《鲁迅全集》在〈出版说明〉中说:「虽然我们作了努力,但差错仍在所难免;有些应注的条目由于缺乏有关的资料,尚待今后补注;校勘方面,可能仍有粗疏和错漏之处。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2005 年版《鲁迅全集》在〈出版说明〉中说:「《鲁迅全集》注释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和繁杂,虽然作了努力,但疏漏还会难以避免,我们仍期待读者的指教。」
笔者将自己的阅读、研究心得写出以上若干条意见,将它们奉献出来,这对于今后《鲁迅全集》的进一步修订,对于国内外广大读者,可能都会有裨益。

《鲁歌<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封面
1 见〈论《金瓶梅》这部书─导读〉,刊台湾增你智公司版《金瓶梅词话》书前。
文章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鲁歌<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