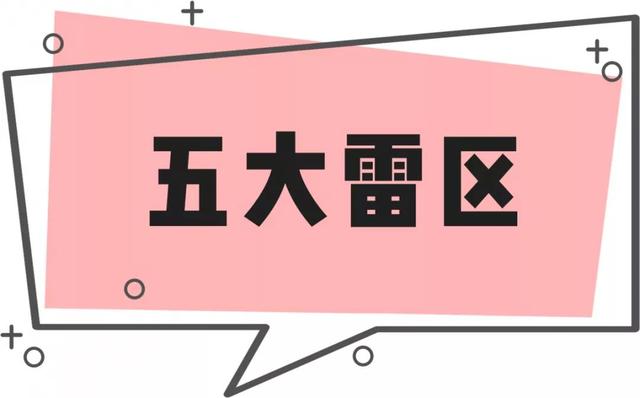马萧
我关注在华韩国人群体将近十年,仍对第一次访问北京望京“韩国城”的经历记忆犹新。2011年夏天,我带着满满的想象走出北京地铁15号线望京站,以为自己将置身类似韩国明洞的异国空间中:鳞次栉比的韩式服装化妆品店、韩式烤肉食堂、咖啡甜品店,与单眼皮戴棒球帽的韩国欧巴擦肩而过,“안녕하세요”(你好)的韩语问候不绝于耳。然而,我却失望地发现这个地方并不是“很韩国”。主干道两旁有韩文标识的商铺并不占多数,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也大多说的是普通话。接待我的居委会张阿姨更是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好多韩国人都走了,你还研究他们做什么?”
极度的沮丧激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声名远播的“韩国城”会是这番模样?果真只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地方效应吗?欧美学者已经在“唐人街”、“韩国城”的研究课题上有丰富的成果,那么中国情境中的“韩国城”与之有何异同?进一步而言,我关心的三大问题是:“韩国城”到底是不是一个发展成熟和制度完善的“族裔社区”?韩国人的族裔经济形态和族群关系的状态如何?族裔企业家的个人生命历程如何与族裔社区和经济的发展历程相互纠缠和影响?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韩国人是中国最大的外国人群体,达到12.08万。而韩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华韩国人的数量在2007年达到顶峰51.8万之后,就一直呈下降趋势,2011年统计为36.9万,2017年则下降到34.9万。其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国际金融和贸易形势的巨变之外,还与变幻莫测的中韩外交关系、中韩两国各自的经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尽管在华韩国人总数与庞大的中国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他们集中在大城市的特定区域,已经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居住区和商业区,其中包括本文提及的北京望京地区和上海虹泉路一带。
2014-2015年,我在望京地区进行了将近1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又有过三次短期访问。田野调查期间,我寻找各种机会接触和参与韩国人、朝鲜族和汉族的日常社会和经济生活。我曾长期租住朝鲜族开设的民宿,给韩商和韩企干做过翻译,在韩国人开设的补习班里当过兼职汉语教师,还担任过韩国主妇汉语学习小组的志愿教师。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我又对经营者、被雇佣者和消费者三个群体进行了深度访谈。今年初开始,我带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研究团队开始对上海虹泉路的韩国街进行调研,并有了初步的成果产出。
“韩国城”:都市化、国际化与士绅化
2014年5月,我在北京望京访谈了来华将近15年的韩国人柳先生。尽管在华打拼多年,他还是决定结束一切,举家回国。他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汉语流利,在北京某高校任职韩语教师的同时与人合伙经营小生意。柳先生坦言,决心回国主要原因是他在高校任职的工资不高,爱人也没有工作,再加上越来越高的生活和经商成本,一家人在北京越来越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
柳先生特别提到了休闲娱乐消费方面,他喜欢看话剧,在韩国时每月都要去看一两次,但在中国一次也没看过。原因之一是票价太高,另外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也导致他无法享受包括话剧在内的文化商品和服务。言谈之间他用了“望京岛”的比喻,形容许多韩国人因语言和经济的障碍生活在望京这一文化孤岛之上,不敢去外面,“就像犯人被关在监狱里一样。”
2020年5月底,与韩国老公共同经营中韩物流代理生意的中国人小玉将设在望京的办公室搬到了地下一层,这样每个月可省下6000元房租。小玉告诉笔者,受今年疫情影响,超过半数的公司都在搬家,大公司从高档写字楼搬到中低档的,小公司则往地下、郊区搬,都是为了尽量减少支出,挺过经济萧条的难关。小玉说,望京当地很多韩国人经营的饭店、学院(补习班)、美容院都关门了,没有收入支付不起房租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多韩国人走了就没回来。
小玉说,其实疫情前生意就不好做了,疫情加剧了这个情况。小玉夫妇从事中韩物流行业20年,80-90%的客户是韩国企业和个人;公司是“夫妻店”的形式,雇佣几个固定的小时工负责包装和拉货。小玉告诉我,过去中韩物流是“进多出少”,有竞争力的韩国商品、机器配件等输入中国的情况较多;但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因为各大电商的一站式全球购平台极大冲击了跨国物流代理的业务。他们现在的主营业务是将中国生产的服装、日用品等输出到韩国。疫情之下,外资私营小企业显示出更明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对此,小玉感慨地说,“我们在夹缝中生存。”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韩国城”、“唐人街”等少数族裔移民聚居区的研究视角之一为族裔社区的视角,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对美国少数族裔移民社区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威廉·怀特描写波士顿意大利人贫民区的《街角社会》,是无数社会学专业学生必读的经典著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类学家Caroline Brettell 发出了发人深省的疑问,“族裔社区是必然发生的吗?(Is the ethnic community inevitable?)” 。她比较并发现在多伦多和巴黎的葡萄牙移民群体存在显著的不同,前者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后者则松散似乌合之众。通过分析差异的原因,Brettell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受到移民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当地社会对待移民的态度以及政府移民政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Nina Glick Schiller、Andreas Wimmer)都开始强调,族裔社区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分析单位是存在问题的。
那么,北京的望京地区是一个发展完善的“韩国城”族裔社区吗?位于北京东北部四环与五环之间的望京开始作为一个“韩国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始于2002年中韩建交十周年之际,当时中韩的主流媒体(例如新华网、The Korea Times)都纷纷报道了韩国人聚集望京居住,以韩式餐厅超市为特征的族裔经济的繁荣。
“韩国城”的诞生与北京郊区的都市化进程紧密相关。19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解决内城住房紧缺的问题,市政府将包括望京在内的几个城市郊区规划为“城市新区”,并开始在望京兴建高层公寓住宅小区。新建的小区干净整洁、安保规范、有涉外性质且租金较外交公寓便宜,非常符合当时韩国“新城市中产阶级”的房屋消费偏好,因而吸引了许多韩国和朝鲜族商人聚集居住。
2000年中期开始,望京地区新一轮房地产开发项目展开,通过打造低密度和中高档公寓小区,吸引中外商业文化精英租住和购买。随着望京当地公共交通和生活设施逐步健全,韩国使馆和大企业开始将在亚运村和使馆区居住的外派员们安排到望京,进一步带动了以韩国人为服务对象的族裔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市政府并没有将望京“韩国化”作为城市规划的目标。例如,最新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强调,望京等地要朝着“国际人才社区”、“创意文化景观区域”的方向发展。由于“国际化”的定位,望京不断吸引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进驻,当地房价和房租也随之大幅上涨。以50平米左右的单人公寓为例,受2016年阿里巴巴进驻望京的影响,一夜之间租金从5000元涨至6000元。受房租上涨影响,许多中低收入的韩国人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居所,开始迁往顺义、通州甚至是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镇。
当地政府主导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直接推动了都市的“士绅化”过程。城市士绅化(gentrification)指的是,由于上涨的经济和生活成本,低收入的(通常是)外来移民群体被中高收入的群体置换的都市空间发展过程。城市为外来移民企业家提供经济机会的同时,也将他们裹挟进国际化的洪流中,令他们与本国企业家一样,共同承担了城市士绅化的成本。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则加速了士绅化的过程,增加了移民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随着北京韩国人居住空间的分散,“韩国城”正在演变成一个边界模糊、千疮百孔(porous)的城市空间;曾经如日中天的韩国人经济也在被欣欣向荣的网红打卡店、连锁美食店不断蚕食。柳先生的离去和小玉的挣扎反映了韩国人经济社会关系网络的脆弱,他们在势不可挡的国际化洪流中,或坚持,或放弃。北京“韩国城”并不是一个发展成熟的族裔社区。

望京“韩国城”消费场所,2016年夏。

逐渐缩小的望京“韩国城”消费场所,笔者摄于2019年冬。
“韩国街”:首尔夜市、“K-Beauty”与族群化
上海闵行区虹泉路的“首尔夜市”于今年元旦开市,因疫情沉寂三个月后,以“明洞De夏天”为名,趁着五一假期“强势回归”。白色棚顶的花车沿虹泉路一字排开,中韩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装饰品、首饰、服装、特色小吃、韩语培训机构等应有尽有。
“首尔夜市的确吸引了大量人流,但很多人都是在室外逛街消费,真正进入大厦的人还不多。”在虹泉路的主要商务楼宇之一的井亭天地生活广场卖化妆品和服装的韩国人金先生说道。金先生5月份的营业额达到疫情前的一半左右,尽管还不理想,但比前两个月要好得多。考虑到疫情影响,井亭天地生活广场的业主主动减免了2个月店租,大大减轻了租户的经济压力。

虹泉路韩国街,笔者摄于2020年6月1日
今年是金先生来沪的第十六个年头了。作为公司外派员来华工作的他五年前与太太一起接手朋友的店,开始从事韩国化妆品和服装生意。金先生认为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的优势在于,在韩流文化的推动下“K-Beauty”(韩国式的美丽)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特别是中国人的皮肤状态与韩国人很接近,因此相较欧美化妆品,韩妆在中国市场更有竞争优势。 同时他也感到有明显的语言、文化和性别方面的障碍。他的大部分顾客是中国年轻女性,尽管他中文流利,还将每种化妆品的中文名字和效用背得滚瓜烂熟,但还是无法自由地与顾客进行深入交流,给出化妆和穿着方面的建议。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雇佣了一名朝鲜族女性做店长接待顾客。金先生说,大厦里许多韩国人老板都雇佣了汉族女性看店,因为她们能够在语言和文化上与顾客建立有效的沟通与连接。
作为上海第一个涉外商务区和居住区,古北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是绝大部分在沪外国人的主要居住地。2003 年上海解除了对外国人居住地的限制后,古北的外国人开始四散,古北新区向西5公里左右的龙柏地区成为韩国人的集中去向。龙柏地区的房租比古北便宜,而且具有离韩国总领事馆、商会和韩国学校近的区位优势,又紧邻通往市中心的高架,因而成为许多韩国人的居住选择。1990年代中期开始,龙柏新村、锦绣江南、井亭苑等一系列居住小区先后建成,为中韩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居住资源。
据2006年8月《新民晚报》报道,当时上海有3万多名韩国人,至少三五千人住在龙柏,龙柏是人数最多的韩国人聚居区,龙柏新村西面的紫藤路从一条普通的美食街在短短几年间发展成特色鲜明的韩国料理街。2008年,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并将总部设在距离龙柏不远的徐汇区宜山路,带动更多韩国公司外派员到龙柏地区居住。
2009年11月,龙柏新村往南约2公里的虹泉路第一次出现在韩国媒体的报道中。为了庆祝日据时期流亡中国的朝鲜人在上海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90周年生日,韩国人在虹泉路上的协和双语国际学校内举办了盛大的“中韩亚细亚超级模特大赛”。
2013年起,虹泉路开始摇身成为韩式商业娱乐一条街,韩流文化与跨国资本的推动是其成功变身的重要因素。当时,韩国热播的电视剧《绅士的品格》、《继承者们》带动了韩国咖啡甜品连锁店mangosix落地虹泉路,韩粉们排队几小时购买剧中出现的蓝色汽水和芒果椰奶;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则带动了韩式炸鸡啤酒的火爆消费。
据金先生回忆,炸鸡啤酒的文化消费带动了各类韩式餐饮生意的同时,也拉高了当地的店租,有餐厅的店租涨了五倍之多,许多韩国企业家因难以实现收支平衡而选择离开。金先生认识一家烤肉店的韩国老板就因为无法承担两层店铺的租金,把整个店搬到了房租和人工费用低廉的崇明岛。虹泉路上一家房地产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2017年左右开始,当地韩流消费的热度就有所降温了。那时,中韩关系正因“萨德”遭遇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尽管如此,2018年发布的《上海市闵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明确了将“虹泉路韩国街”作为当地四大特色商业街区的地位。 2020年初,虹泉路“首尔夜市”的问世和沿街迎风招展的中韩两国国旗都表明了当地政府积极利用韩国文化元素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举措和决心。对此,金先生毫不犹豫地说,“这里已经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韩国城了。”
美国华裔社会学家周敏的代表作《唐人街》从族裔经济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美国唐人街华裔制衣业的研究,发现了华人移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族裔聚居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这是一种通过空间聚集形成的、以自雇佣经济为主并为同族裔(也可以是其他少数族裔)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形式。此外,另一种备受关注的族裔经济形态是“中间人少数族裔经济”(middleman minority economy),主要指某些外来移民群体集中从事商贸、中间人等职业,他们处于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雇员、房东和房客的一种居中的经济角色和地位。美籍韩裔社会学家Min Pyong Gap运用这个概念分析了美国韩裔小商人被夹在白人和黑人间的种族化的经济困境。
从族裔经济的研究视角来看,上海的“韩国街”兼具以上两种经济形态的特征。它不仅是内聚、排他的,也是开放、连接的。一方面,韩国企业家扮演了“文化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将韩国流行的商品和服务输送到中国,满足了大批当地韩粉们对流行文化元素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它不仅为同族成员提供生活必须的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还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社会关系的开放或封闭取决于参与者是否能从开放或垄断关系中获得自我改善的经济机会。
北美的唐人街不仅为华裔移民提供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机会,而且帮助他们在不丧失族裔特质的情况下站稳脚跟,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最终融入主流社会。不同的是,我国的“韩国城”、“韩国街”体现出的是“发展主义”的取向,它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外国人政策相契合;即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鼓励招商引资,利用外资和技术发展我国经济。 但是,北京与上海在具体做法上存在微妙的差异。前者通过倡导国际化,引进外企外资与外国人才,实现城市空间转型升级;而后者则采取了通过利用和强化韩国文化元素,刺激消费、吸引外资的发展观。

虹泉路韩国街,笔者摄于2020年6月1日
此韩国城?彼韩国城?
从族裔社区和族裔经济的视角切入,我们发现了在华韩国人的族裔社区和经济与北美“唐人街”、“韩国城”的显著差异。尽管如此,近期被翻译成中文的人类学家陈志明和王保华编写的《唐人街》一书更令我们看到了两者的相似和可比之处。《唐人街》一书中,多位研究者分别深入地描述了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唐人街的发展历程以及影响其发展历程的力量。他们将移民社区置于一个动态变化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族裔经济,而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区背景下进行审视。从社区发展的视角切入,我们可以在洛杉矶的韩国城曾经走过的道路中找寻到中国的“韩国城”和“韩国街”正在经历的相似过程。
1970年代末开始,韩国企业家开始向加州和美国其他地区进行投资,E-2投资签证能够令他们携带配偶、子女,并享受自由出入、居留以及特定的免费教育权利;与亚洲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也给韩国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1980年代初,洛杉矶政府正式将韩国人居住和经商的区域定名为“韩国城”,并推动它从一个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发展为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的结点。经济的发展令洛杉矶韩国城的经商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高收入的中产阶级新移民逐渐取代早年到来的小企业主和小商人。
士绅化是洛杉矶、北京和上海的韩国人企业家共同被卷入的社区历程,而当地政府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北京望京地区,士绅化的原因是政府主导的都市国际化,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和外资进入,挤压了韩国小企业主的生存空间,这个过程是去族群化的。相比而言,上海的虹泉路的“韩国街”首先是作为一个较古北地区廉价的选择出现的,算是都市士绅化、韩国人居住空间分散的可视结果和解决路径。在韩流热度和资本逐利的推动下,它更快又被卷入一轮新的士绅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当地店租上涨和许多韩国店主的离开。目前,当地政府采取了韩国街族群化的经济发展策略,特别作为后疫情时期刺激当地消费的手段。首尔夜市在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同时,也会带来更激烈的经济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小企业家是否能够真正得利还未可知。
此韩国城,似彼韩国城,又非彼韩国城。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团队成员游震豪、季婧源、范博琳、李献伟对本文均有贡献。)
参考文献:
Brettell, C. (1981). Is the ethnic community inevitable? A comparison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portuguese immigrants in toronto and paris. The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9(3), 1–17.
Lett, D. P. (1998).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俞凯,五五购物节·全闵嗨起来: “韩国街”首尔夜市强势回归,澎湃新闻,2020-05-0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246568
周雯婷、刘云刚,2015,《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地理研究》第11期。
孙云, 2007,《上海龙柏“韩国城”》. 王孝俭主编,《闵行年鉴》,学林出版社,2007:569-571。
李子慧,没有了欧巴的上海韩国街, 这些年过得不太好, 界面新闻, 2018-06-07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203595.html
2009 한중 아시아슈퍼모델 대회, 슈퍼모델의 미소, 韩国经济每日新闻,2009-11-06,
http://bntnews.hankyung.com/apps/news?popup=0&nid=02&c1=02&c2=02&c3=00&nkey=200911031707173&mode=sub_view
《特色街区与节日市场:井亭虹泉路韩国街》,《上海商贸年鉴》,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6:178-179。
《2018年上海市闵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网站,2019-03-15,
http://www.shmh.gov.cn/shmh/tjsj-tjgb/20190315/423948.html
Min, P. G. (1996). Caught in the middle: Korean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Pbk., 2nd pri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樊鹏,2018,《国际化社区治理:专业化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方案》,《新视野》第2期。
Kyeyoung Park & Jessica Kim (2008) The Contested Nexus of Los Angeles Koreatown: Capital Restructuring,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Amerasia Journal, 34:3, 126-150.
Angie Chung (2007) Legacies of Struggl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Korean American Politic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0-43.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