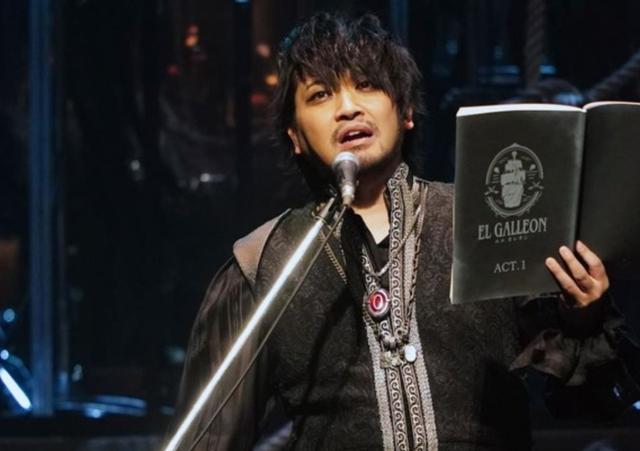《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由美国女作家哈珀.李于196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背景是1932年大萧条时期的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小镇居民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消遣,只有宽裕的时间、种族歧视以及关于怪人拉德利的谣言。

对于经济危机下的梅科姆镇的居民来说,没什么钱也就没什么好恐惧的事情,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而对于小镇里的孩子来说,离群索居的拉德利家的怪人,是恐惧的源头。
“据说他会在夜里等到月亮落下去的时候溜出来,偷偷往人家的窗户里窥探。如果谁家的杜鹃花被寒流冻坏,那肯定是他往花上吹了口气。梅科姆镇发生的所有小偷小摸之类的勾当,他都摆脱不了干系。有一段时间,一连串病态的夜间犯罪让镇上的居民心惊肉跳:人们家里养的鸡和宠物不断惨遭毒手。虽然作案者疯子艾迪掉进巴克湾里淹死了,但人们仍然盯着巴德利家,不想打消他们最初的怀疑。”
莫迪小姐说,这里面有四分之三是梅科姆镇的黑人编造的,另外四分之一是长舌妇斯蒂芬妮的谣言。那么,关于拉德利的谣言是怎么来的呢?

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对谣言的定义是: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
多数谣言首先都有一个娱乐功能,一个维持聊天的功能,一个消除忧愁和空虚的功能。所以不是拉德利家需要这个谣言,而是梅科姆镇的居民需要谣言来调剂他们乏味的生活。
离群索居、与小镇居民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拉德利家,原本就给喜欢闲言碎语的人提供了谈资,而阿瑟.拉德利在小镇捅了篓子被父亲囚禁在家更是引起轩然大波,此后十几年,邻居们再也没有见过阿瑟,连他的生死都变成了谜。拉德利家紧闭的门窗,沉默寡言的老拉德利,没有一丝生气的房子,把喜欢探听隐私的人都拒之门外,为了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平静无波的小镇生活需要的谣言开始了。
在孩子们眼中,传闻变得可怕而怪异:怪人长着活像骷髅头的脑袋,生吃松鼠和猫,手上总是血迹斑斑,脸上有一条长长的锯齿状的疤痕,牙齿又黄又烂,眼珠子向外鼓,一天到晚都在流口水。
《谣言心理学》认为,在每次新的信息都含糊不清的情况下,这个信息就会接受下一个听众对它作出的个人解释。人们很少自觉地去证实消息来源,通过不同的人的转述,每个人对信息的重新加工,于是在流传过程中,谣言离真实越来越远。
而那些明知这是谣言还不停地扩散和传播的人,是因为他们通过信息交换可以缓解自己心中的不安,以此来发泄自己的心理需求:他们从中得到满足,内心紧张通过社会的一致赞同而消失——假如人们相信我,那是因为我有道理。于是这样荒诞的谣言,竟然被梅科姆镇的大多数人接受了。
尽管在莫迪小姐的印象中,小时候阿瑟.拉德利总是很有礼貌,彬彬有礼,像一只知更鸟一样无害,但是在梅科姆镇的居民口中,在愈演愈烈的谣言中,已经是一个恶魔般的幽灵。每一个新来的人都被告知离拉德利家远点,黑人宁肯绕远路,也不愿意从他家门口经过,甚至连他家掉下来的胡桃都没有人吃——怕有毒。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谣言的助推剂。梅科姆镇还是有一些像阿迪克斯、莫迪小姐这样的人对谣言免疫。然而阿迪克斯的态度是,让芬奇家的人过好自己的生活,让拉德利家的人过好自己的生活。而莫迪小姐虽然当面反驳了长舌妇斯蒂芬妮,但对于沸沸扬扬的谣言,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尽管不参与,但对谣言的沉默令他们成为同谋。
谣言终会消逝。在事实面前,谣言一击即溃。在小说的结尾,阿瑟为了挽救两个孩子的生命,杀死了持刀的歹徒。现实中的怪人,是拥有着常年不见天日的惨白的肤色,不太健康的身体,以及一颗善良而高尚的心。

所以在梅科姆镇,谣言是小镇居民的一场惊梦,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遣。但对于可怜的阿瑟来说,却是一场噩梦:这些谣言彻底将他与世隔绝。他尝试过给孩子们送可爱的小玩意儿,替他们缝补过裤子,披上过毯子,但是一开始他们最直观的感受是抑制不住的恐惧和恶心。他尝试与这个世界联接,但世界却拒他千里之外。
好在最后他终于走到现实中来,与孩子们成为朋友,谣言也烟消云散。
人言可畏,言论自由保障每个人说话的权利,但是谁能保障我们,不被别人说话造成伤害的自由呢?
谣言止于智者。即使做不到不信谣不传谣,也希望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始作俑者,更不要伤害像知更鸟一样善良无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