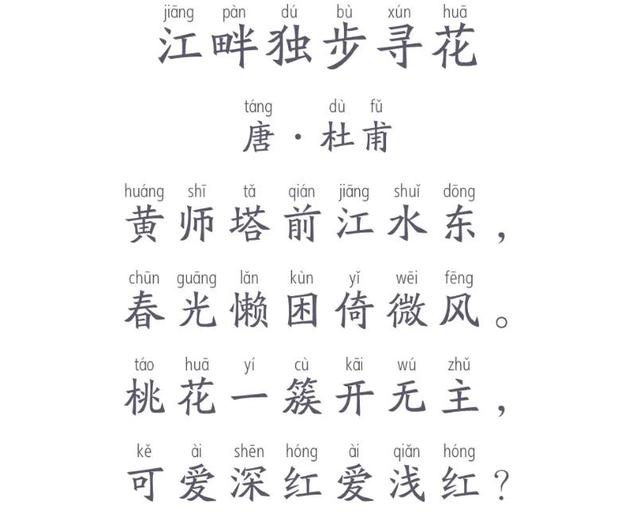《红楼梦》研究中与“情”关系密切的三大缺陷(一),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红楼梦人物关系细解?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楼梦人物关系细解
《红楼梦》研究中与“情”关系密切的三大缺陷(一)
杨若文
摘要:《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着与“情”关系密切的三大缺陷:一是“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在研究中“情”却被边缘化,导致研究本身灵魂的失缺;二是不少学者对“续40回”的贬低以及对“高鹗”的“情”与“理”上的不公,源自于对“续作难于创作”存在认识盲区、对“高鹗”敢于续作的责任担当以及“给残缺的《红楼梦》以一个完整”存在认识误区与偏见;三是诸多学者有着共识的《红楼梦》“反封建社会”、贾宝玉“叛逆性”均为伪命题,由此连带的《红楼梦》主题划定不应在政治层面而应在“情”的层面。
关键词:情感;感情;《红楼梦》研究;续作;伪命题;贾宝玉;大观园
中图分类号:I207.411;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7-0129-06
笔者曾在《西部学刊》2022第3月上半月刊的《从“情”的层面对〈红楼梦〉原著与87版电视剧的对照评析》(简称《评析》)一文中,对“原80回”中“情”的类别、“情”的表达和“续40回”中“情”的体现进行了梳理,并在认定“87版电视连续剧从‘情’上切入是抓住了《红楼梦》的灵魂”的前提下,对原著与87版电视连续剧进行了“优于何处、劣又何在”的对照评析。本文是在《评析》的基础上(包括沿用《评析》中分类了的“情感”与“感情”两个概念),对红学研究中的三大缺陷提出商榷性意见。
一、《红楼梦》研究中,对“情”应该怎么把握?
曹雪芹通过空空道人响响地道出《红楼梦》“大旨谈情”,曾用的书名《情僧录》中含的正是“情”。他去世后被改为现名的《红楼梦》,突出的也是红楼佳人之“情”。脂砚斋多次评点中强调了“情”,认定了《红楼梦》是“因情得文”的“表情文字”,并将其区分为“儿女之情”即爱情、“世情”即人情冷暖的感情。可见,书中的“情”在作者自己以及当时最活跃的评论者心目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红楼梦》中,“情”不仅浓浓,且是复杂多样,笔者在《评析》一文已有详述,不再赘言。要说的是,情,是个人性格的重要组成。一者,性格亦曰“性情”,本身就是“个性”与“情”结合的产物;二者,左右人行为的,除了理,“情”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人品修养中,勇敢与怯懦、善良与暴戾、谦虚与傲慢、包容与排斥等等,无一不与“情”密切相关。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不抓住“情”,其性格的分析难免表面化、空泛化,主题的表达也不易于向深层次开掘。《评析》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贾府“爱情观的颠倒、爱情环境的恶劣,尤其主子之间亲情的病态、友情的疏离”与下层奴仆情感、感情的洁美相比,更加显出了上层主子“情”的污劣。笔者并不认定学者们在《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与主题划定中对“情”的基本丢失,有些学者如李传龙先生几度对“情”予以充分肯定[1-2],涛每、薛瑞生少数几位先生对“情”也予以较多关注,但在《红楼梦》研究的大盘中,对这部巨著大旨所谈的“情”,被边缘化了,理解上也只限于爱情、感情,相对单一。还有,常用的“情感”“感情”,二词是异还是同,好像也无人去分辨。
“情”的被边缘化,意味着什么?答曰:无异于丢掉《红楼梦》研究的灵魂。要知,文学作品是由“知”“情”“理”融合而成的,《评析》的头一句就是“文学作品能动人者,‘情’也。”作品是生活有血有肉的反映,其“有血有肉”,是由“情”充而盈之的。如果文学沦为单纯的告“知”而将“情”排斥在外,也就成了干瘪的文字推砌,灵魂必当失之无影了。既然“知”离不开“情”,那么“理”与“情”又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之动是前提,理之晓为后果。作品中的“理”,如果没有“情”的参与,说服力将会打个大大折扣。请问,“知”“情”“理”相融合中的“情”被置于边缘,《红楼梦》研究岂不掉魂?
研究界对宝黛爱情的看待,也出现偏差。笔者认为,宝黛的爱情,不只情浓意真、缠绵无尽,而且有着诸多小说中罕见的宏阔飒爽与始终如一:从青埂峰到灵河畔的“天恋”,到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神恋”,到大观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人恋”,无论虚恋还是实恋、暗恋还是明恋,男女知己间的甜蜜互享、心心相印,能不让人心动魂动?笔者的《评析》对二人爱情之甜蜜已有论述,尽管无婚姻的爱情不完整,但在“容得偷情却容不得爱情”的恶劣环境中,能到这一步也就够了,不应对二人的爱情以“悲”论之。《洛神赋》中的曹植与洛神之间也是无婚姻的挚爱,就没有听说有谁认定他们是爱情悲剧,这就是个参照!相反,有婚姻而无爱情,即使同床共枕,也应认定为爱情悲剧,薛蟠与夏金桂、孙绍祖与贾迎春就是如此。除了袭人嫁蒋未带“悲”字,整本《红楼梦》全是婚姻悲剧,就不能以此将好几对的浓浓爱情统统归之于“悲”的。“红学”界不少人之所以认定宝、黛爱情为“悲”,是否错以婚姻成败为标准?专著与评论中还出现了“爱情婚姻”二词并肩,究竟是分清了爱情与婚姻的泾与渭,还是仍然混为一溪?笔者猜疑:错以婚姻成败为标准来捆绑爱情,是否“情”在“红学”专家头脑中被边缘化的体现?可以说,“情”在研究中被边缘化,是丢掉了西瓜。
那么,对“情”应该怎么把握?
二、对“续40回”的续作人的严苛、贬损,甚至抡起学术界不该用的那种大棒,是否值得反思?
“续40回”的推出不能排除“高鹗”(学者们否定了高鹗为续作者,笔者无异议。但因拙文中所引用的资料,不少涉及高鹗,为了叙述方便,暂用加引号的“高鹗”代替续作者)对“原80回”的关爱以及对这一巨著身残的惋惜等情感驱使。而“红学”的研究也是源于对此书的痴爱,其中不少研究者还融入了厌高爱曹的感情倾向,这些全都与“情”密切相关,因而此题也被纳入本文论证范围。
(一)续作的难度,比起创作要大很多
创作是思维放飞的产物,续作不然,要按原作者的框框依葫芦画瓢。葫芦一眼就能看准,而续作还有对原著理解上的不到位乃至偏解,是个捆起手脚的弄棒。环视古今中外,笔者只晓得美国亚历山德拉在别人的《乱世佳人》后成功地推出了续集《斯佳丽》。在我国,因其作者“出师未捷身先死”而留下那么多“烂尾工程”中,仅褚少孙补过《史记》散失的几篇,班昭、马续接手去世的班固完成了《前汉书》,文学界唯有苏轼干过这个买卖,他记忆中的孟昶《洞仙歌》仅有开头三句,将其续为一首整词。《西游记》续作虽有好几部,皆因货色欠佳而销声匿迹。悠悠历史、大千世界,能拿出像样的,也只区区这么几人,况且我国上述续作仅仅局限于书中的个别篇章。这从另一角度证明,续作确是不易。
(二)《红楼梦》的续作,又难一层
曹雪芹是万人难及的高手,没有硬棱棱的金刚钻难揽他的瓷器活儿。再说,《红楼梦》已厚厚的六七十万字堆在那儿,主题、结构、人物、写作手法等都已定型,续者自由处理的空间狭窄、有限,要走出独特的精彩,难比上天。况且,“高鹗”将要啃掉的,可能是几十回、长达几十多万字,这就在本来的难上又加了一层。当时及后来的续书有《红楼补》《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圆梦》数十种,昙花未现就已枯萎,《红楼梦》续作的成功率如此之低,其难度还用明言吗?
(三)“高鹗”确实可赞
其一,他的最大贡献是将《红楼梦》缝补为完整的作品而广传于世,内容设置仍在曹公原有“情”的层面而没有脱缰远去。笔者冠以“最大贡献”,缘于“高鹗”给了这部残书一个完整。要知,《红楼梦》的残缺,远不像前文提到的《史记》《汉书》仅缺小枝小节,而是胳膊腿的不全甚至腑脏的缺一缺二。《史记》《汉书》即使不补仍然是《史记》《汉书》,而《红楼梦》则成了“烂尾工程”,能不能流传也只有老天晓得。有人会说,“原80回”曹雪芹在世时不就流传开了?但要弄清,那时人们的传抄,是在此书将会完整面世的认知下而为的,若能料到将是缺那么一大块子的严重“残疾”,会有人疯抄吗?未必!事实上,那么多续作被淘汰,唯有“高鹗”续作经历住了大浪淘沙而蕾俏枝头。百十年来,包括现代人的补作,没有哪个能够替换,“高鹗”功劳确是不小。
其二,当初面对这么个烫手山芋,“高鹗”接手了。或许他还有别的目的,但至少反映出他对这部巨著“有头无尾”的同情惋惜以及对其完成的勇于担当。他不会不晓得这一硬骨的难啃,但他没有退缩,是个好汉子。谁若不服,不妨试试,给《红楼梦》续个更漂亮的与“高鹗”比个上下,可乎?“高鹗”对残缺《红楼梦》同情惋惜的情怀、责任担当的精神、敢于硬啃的胆识、拿下40回30万字的苦功,有几人能比?笔者要朗声说说,“续40回”尽管存在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它是个成功,“高鹗”不该赞吗?不赞,您的情感过得去吗?
(四)“红学”界对“高鹗”的贬低与诋毁,很是不该
应该承认,曹雪芹比“高鹗”高明,“原80回”优于“续40回”,其差距尚是不小,这几乎是学者们的共识,笔者也很认同。但坦直而言,“红学”界确实存在扬曹贬“高”、抬高“原80回”、矮化甚至苛责“续40回”的现象,有的贬者语言还带棱带角,笔者同意有识之士所认定的“这是一种偏见”。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将续书也看成创作。续书者是在不伤害原著前提下有着自由发挥的权利,应该予以认可。借用两例: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对原赋内容略有变动,王维的《桃源行》也没有完全依照陶渊明原意,后人认定此二例同样也是创作,对其与原作的比较是依据水平而言的。同一道理,对续作衡量应以创作水平是高是低说话,不应像一些学者一味地以是否符合曹雪芹原意苛求,如同千百年来无人苛求《洛神赋图》与《桃源行》一样。因为曹雪芹再伟大也不是不能超越的。评论家往往站在评论者角度这本无错,没有同时站在创作人角度用换位思考来发声,“情”的关怀也就缺失了。另一种是超出苛求而在诋毁了。“红学”界影响不小的周汝昌老先生竟“把‘高鹗’的文化活动‘上纲’为政治问题”[3],甚至要“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4]。笔者将周汝昌老先生的观点亮出来,不是想向这位老前辈讨什么说法,而是就此现象想做个分析。因为这不再是简单的苛求,猜测是老先生的情感反应。笔者曾因扬曹贬“高”的氛围,一度对曹雪芹崇拜而对“高鹗”反感且在情感轴线上分别接近极的两端,以至于“原80回”拜读好几遍而“续40回”一目十行草草而过、知其大概再也不愿目触。如果当时动笔来上一篇,必定是大骂“高”而大赞曹的病态体现。何以如此?好、恶之情在作祟!“情”层面的喜好和厌恶可以左右人们的行为,且是很难一下子用理智来控制与扭转的。而那位要控诉“高鹗”之“罪状”的周汝昌老先生,用“诋毁”二字来表述他对“高鹗”的态度也显得分量不够很难到位,他是抡着学术界不该用的那种大棒,要置“高鹗”与“续40回”于死地的。人们大凡在喜好与厌烦中陷得很深,就演化为心态上的固化而处于情感反应的泥淖很难拔出脚来,出现一种“不爱死谁、不恨死谁”就吃不下、睡不着的身不由己。笔者不敢贸然说周汝昌老先生在情感健康上有了什么,但不能不做这一方面的推测。庆幸的是,诋毁者仅仅是极少数。笔者憋在内心不吐不快的是,对于有功之人“高鹗”,学者们非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贬低者不乏其人且贬得很低,而理解续作之难者罕矣,对续作人很是不公。是否“情”有点薄、心有点冷?
对此,该不该反思?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