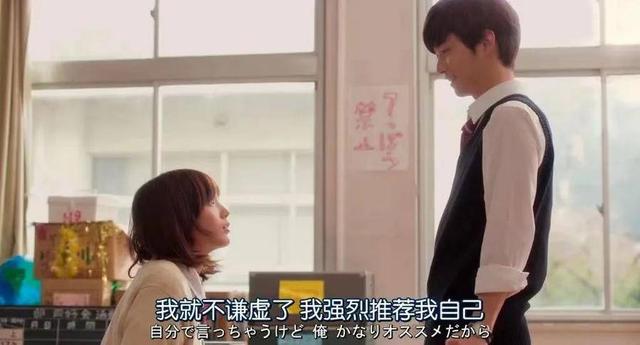关于《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的作者等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方认为此词作者是岳飞,一方认为不是,而是明人的伪托;一方认为此词涉及到了民族问题,今天应当避讳,一方则认为这一问题并不存在。同时,还牵涉到了英雄、爱国与忠君等诸多问题。
若列举宋词中深入人心的作品,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应当是其中的一首。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对宋词作品进行排行,这首词高居排行榜的第二位,其地位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古往今来的所有选本和课本,凡入选这首词的,署名都是岳飞,基本没有对其著作权及相关问题发生过疑问。但这仅是在大众接受的视界。在学术领域,半个世纪以来,围绕这首词的著作权等问题,却有着非常热烈的争鸣和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这场争论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产生影响之大,在我国当代词学研究史上绝无仅有。本文即试图对这一著名争论作一综述和回顾。
一、作者是不是岳飞?
1962年2月,夏承焘在日本《中国文学报》(第16册)发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对岳飞《满江红》词的著作权问题提出质疑。文章“怀疑”这首词不是岳飞的作品,而是“明代弘治年间人”的“托拟之作”。
夏承焘的质疑,实际上来源于近代学者余嘉锡的疑说。余嘉锡在1958年出版的《四库提要辩证》卷二十三《岳武穆遗文》条中,首先对《满江红》的作者发生疑问[2]1443-1445。其依据是:此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是据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杭州岳坟词碑收入;其不见于“宋元人之纪载,或题咏跋尾”,“沉霾数百年,突出于明中叶以后”,故“来历不明,深为可疑”。岳飞之子岳霖、孙岳珂,搜访父祖遗稿“不遗余力”,但岳珂的《金陀粹编.鄂王家集》却没有收录此词。
夏承焘认为余嘉锡的这两点论据“都很有力量”,并进一步就余嘉锡“《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之言指辩说:“我以为《满江红》也有其可疑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便是。”其理由是:从地理常识来看:“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所以,“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唐人、明中叶诗人用贺兰山的,“都是实指而非泛称”。“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头又一秋’等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而南宋人是“决不会这样说的”。“《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他们西攻甘、凉,便多取道贺兰山后……。”据此,“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再结合弘治十一年明将王越打了“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一事,文章推导出了最终的结论,即:《满江红》词的写作时间在“英宗天顺初年(1457)至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这四五十年之间,也就是鞑靼初入河套逼近贺兰山以后、下至赵宽写这词之年”;其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对余、夏的观点及依据,不少学者提出疑义,特别是在夏承焘一文发表之后。
学初首先在《文史》创刊第一辑(1962年10月)发表《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一文。文章首先指证,早于弘治、嘉靖年间,汤阴典教袁纯在景泰六年(1455)编写的《精忠录》中,就曾录有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尔后指出:“宋人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只见于明人之书者殊不少”,“此词纵有可疑,只以文献不足,如遽认为伪作,或难免有流于武断之嫌”,所以“似以审慎为宜”。谷斯范也同时发表了《也谈岳飞〈满江红〉词——与夏承焘同志商榷》一文(《浙江日报》1962年10月14日),认为对《满江红》中“贺兰山”一词的理解不能太狭隘;岳词中用“贺兰山”,是“泛指边塞”。程千帆也在稍后(1963年5月)撰写的《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一文中,对夏文进行了反驳。文章首先澄清了所谓“实指”的概念,认为:“所谓‘实指’,按照我们的理解,应当是实际存在的地名和某一诗篇中所反映的实际发生过的具体事实(不论它是大的或小的,国家、社会的或个人的)相一致的意思,如果脱离了这种具体情况,那就无法分别孰为实指,孰为泛称。”然后,又分析了夏文中所举提到“贺兰山”的唐人诗例(如王维的《老将行》、卢汝弼的《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等),认为“这些地名虽然都是实有的,在本诗中却并非实指的”,并指出:“以唐诗中之贺兰山之皆为实指来断定《满江红》中之贺兰山也当为实指,这种逻辑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文章同时认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句“应当和下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两句联系起来并等同起来看”,“它们都是用典故来借古喻今。匈奴即胡虏是汉朝经常与之斗争的对手,贺兰山则是唐朝和外族交锋的战场。既以匈奴比金源,又以贺兰山比东北边塞,这是完全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而且,“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句词不只是用了古典,同时还用了今典”,如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三所引《古今诗话》就曾记载:“姚嗣宗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韩魏公安抚关中,荐试大理评事。”此事及此诗在宋代流传很广。
针对谷斯范文,夏承焘再撰《再谈岳飞〈满江红〉词——兼答谷斯范同志》(1962年10月21日《浙江日报》)一文,迅速给予回应。文中说明了撰写《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的缘由,以及为什么把“踏破贺兰山缺”认定为明代中叶以后的抗战口号,为什么认为《满江红》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的原因。
十数年之后,1979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仍将《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收入其中(只取消了“三十功名尘与土”与岳飞身世不合一说)。另外,俞平伯在其编写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中,也坚持删去了本已入选的岳飞《满江红》词,称其“存疑”,“系明代人伪托”。这使得本已停歇的论辩又重新展开。新一轮的辩驳规模更大,参与的研究者和发表的文章更多(约有六十余篇),涵盖的地域更广(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当下),并有一些新的成果出现。
20世纪80年代,是双方——可称为“疑伪者”和“认真者”——交锋最激烈的时期,新的观点、新的论据、新的论证角度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出现。而这些新点,又几乎全是“认真者”,即维护岳飞著作权一方提出的。试撮其要如下(大致以相关文章发表的先后时间为序):
1.唐圭璋《读词札记.宋邵公序赠岳飞词》、《读词续记.岳飞“怒发冲冠”词不能断定是伪作》(二文原分别发表于《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后收入《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69、第673—674页):前文说,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一中,有载宋邵公序赠岳飞《满庭芳》本事及《满庭芳》词,“词中‘笑谈顷、匈奴授首’句,显然是檃括岳飞词‘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句”。后文举例证明“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载籍者甚多”,说明岳珂等人书不载岳飞此词,“不等于岳飞即不可能作此词”,并举出岳飞的另一首《满江红》词作为旁证,说:“岳飞另有一首《满江红》(遥望中原)词,亦不见于岳珂、陈郁二书,但其墨迹,经过宋魏了翁,元谢升孙、宋克,明文徵明等人收藏,流传至今。可见岳飞词翰犹有遗翰,亦不能谓之为伪作。”
2.徐沁君《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新探》(《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以辛弃疾词、汪元量诗、关汉卿剧曲为据,来证明岳飞《满江红》词并不是“无声无息”,而是在文学史上曾“发生过一定影响”,在宋元人载籍中“留下过痕迹”。
3.李安《潇潇雨未歇——〈岳飞的满江红?〉读后》(台湾《中国时报》1980年9月21日):《金陀粹编》没有收入《满江红》等作品,是因为岳飞被赐死时,家存文件“全被查封没收”,后来虽蒙准发还,但“并不齐全”。有赖于“民间崇敬岳飞之私藏者逐渐公开”,明清出版的岳飞文集,所收作品才会“较《金陀粹编》为多”;而且皆都有《满江红》词,“未可以岳珂未能收入即生疑认为非岳飞作品”。而且,岳飞冤死后,“秦桧仍然秉政十余年,而其余党位居要津者到了孝宗年间方被革除”,其作品无法流传是很自然的事;到了元朝,统治者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岳飞又以其“民族性强”的形象而“遭受压抑”。所以,直到明朝,岳飞的声誉才会“隆盛”起来,他的《满江红》等作品也才得以大白并广布于天下。
4.邓广铭《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原发表于《文史哲》1982年第1期;后收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406页):南宋人赵与时《宾退录》载有岳飞《题新淦萧寺壁》的一首七绝句诗,岳霖、岳珂就没有搜集到,从中可见他们对于搜访岳飞遗文,并“不够辛勤认真”。“假定说赵与时的《宾退录》失传了,诗是被明朝人抄录,流传下来的,我们是不是也就可以对这首诗产生疑问呢?”“既然有岳霖父子遗漏的实证,就不能排除《满江红》是他们当时没有搜集到的可能。”《满江红》的作者不可能是王越。首先,“既然王越填词夸耀自己的战功,为什么嫁名给岳飞呢?那时候作《满江红》这首词决不会犯什么忌讳,要写自己的战功,完全不必借用岳飞的名字”。其次,“如果王越是在实写,那末,‘靖康耻,犹末雪’句竟可以是泛写的吗?亡国是何等重大事件,词人岂能泛用?而且,如果泛用,则其所影射的究竞是明朝的什么事体呢?何况此句之后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句,又将如何解释?这一句,也只是符合岳飞当时的情况,南宋当时连淮水以北的土地都没有了,岳飞才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责任感。明朝的鞑靼只活跃在河套以北的地区,‘旧山河’都在明朝手里,为什么竟要‘从头收拾’呢?和当时的情况极不相符。”所以,“如果把《满江红》词后半阕全部文句进行通贯的理解,而不仅仅纠缠在‘贺兰山阙’这四个字上,则由明朝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的这种说法就很难讲通了”。从确为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看,“也可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如《五岳祠盟记》和《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就有“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会二圣,归京阙”,“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等句,词意与《满江红》词“相同”。“把这种思想用韵文的形式用词的形式写出来”,就“正是《满江红》”。对《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臧克家极为赞赏。他在给作者的信中说:“一气读完你的大作,大快我心……。我痛心于《满江红》著作权之被剥夺,此感情作用也。而你的堂堂大文,则给以科学上的论证。甚得我心,甚得我心!”信中,臧克家并就“三十功名尘与土”句意,与邓广铭饶有兴致地展开了讨论,认为“尘与土——风尘奔波之谓,非视功名如尘土”,并得到了邓广铭的赞同。(见《臧克家、邓广铭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通信》,原发表于《文史哲》1982年第3期,后分别收入《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0页、《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09页)
5.李安《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与纪念岳飞驻兵的“岳城镇”》(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五卷第九期,1982年3月),王克、孙本祥、李文辉《从贺兰山看〈满江红〉词的真伪》(《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前文依据《磁县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认为岳飞词中“贺兰山”的正确位置,应在现今河北境内的磁县。宁夏和甘肃境内的“贺兰山”,其山虽较磁县境内者为大为高,驰名寰宇,但仅属同名而已。“断定”《满江红》为伪作,只是一项“大胆的假设”,而忽略了“小心的求证”。后文又结合磁县在宋金交战史上的重要战略位置,以及“贺兰山”一带曾是岳飞早期军事生涯的活动中心(是岳飞驻兵岳城时的练兵场)、岳飞转战江淮时曾与“贺兰山”一带义军密切联系、“贺兰山”一带曾是岳飞预计与金敌决战的战场等几个方面,对李安的观点予以阐发,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中出现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之句,不仅不能成为怀疑此词出自岳飞之手的依据,正是它,恰恰有力地证明了,此词只能出自岳飞之手。”对《从贺兰山看〈满江红〉词的真伪》一文,缪钺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此文“以丰富的资料,精密的考证,提出了新的见解”,“论证详覈,其结论是可信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是岳飞所作,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其实,缪钺先此也发表过《论岳飞词》一文(原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后收入《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362页),表明自己对《满江红》真伪问题争论的看法。文中说:“近来学者有人提出疑问,认为此词并非出自岳飞之手,而是明人拟作;也有人进行驳辨,认为此词确是岳飞的作品。我同意后一种说法。”
6.喻朝刚《也谈岳飞的〈满江红〉》(《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文章把质疑者否定岳飞作《满江红》的理由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外因”(如出现时间、流传情况)和“内因”(如词的内容、风格、情调等),并进行了一一反驳。文中特别指出,如果把《满江红》假名岳飞的作伪者认定为书写杭州岳坟词碑的赵宽,那么就会有一个“作伪集团”,因为“当时主持立碑的麦秀,赞助立碑的夏言、邢某等人,如果从未见过此词竟肯轻信赵宽之言,又不问明出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他们是处心积虑地一起刻意作假。而这个“假”,在“游人如云、文士荟萃之处”的杭州,“恐怕早已被人揭破、露出真相了”,“想要掩人耳目”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合理的设想只能是麦秀、夏言等人都对岳飞写的这首词深信不疑”。而且,如果作伪者是赵宽,而作词者却是王越或其幕中文士,则又会生出许多问题。比如,如果“作者”本人知道并同意赵宽的作伪行为,这个“作伪集团”的成员就又要扩大;如果“作者”知道却不同意,赵宽玩弄的张冠李戴的把戏就很可能会被当场揭穿;如果“作者”本人不知道,那么“他”的朋友或后人总会知道,知道后就很难保持缄默;除非是“王越(或别的文士)写作这首词后,严守秘密,不给其他任何人看,专给赵宽让他拿去刻石立碑,欺世惑众”,而这种情况又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的。
7.基多《关于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王清波、司丙午《岳飞〈满江红〉词考的一个重要例证》(《河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前文称,“最近”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汤阴县岳飞庙碑林中有一碑刻,时间上与赵碑有很大不同”。此碑嵌砌在岳飞庙肃瞻亭院东南隅墙壁上,上面刻有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是明代天顺二年(1458)春二月“庠生王熙”所书。此碑比赵宽所书杭州岳坟词碑早了四十余年。后文认为:“这块词碑的发现,不仅否定了关于《满江红》最早出现于明弘治年间之说,而且也否定了出自‘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之手的推断。”同时,“王熙之高祖王公辅曾任国子监司业,元代之国子监隶属翰林院,……居此职位能看到前代的图书典籍,可能接触到有关岳飞奏疏手迹的文献资料。但是,直至元末,这些资料是不能公之于世的。所以,《满江红》词在元代虽存在也只能暗中流传。”“袁纯典教于汤阴,而王熙为县学庠生,则《精忠录》所收与词碑所书之《满江红》所据当同出于一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所谓《满江红》词“来历不明”的疑问。
8.谷斯范《王越与〈满江红〉词无关》(《文史哲》1983年第2期):夏承焘“把王越和弘治十一年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入侵的战事,都过分夸大了”。关于“战事”:根据宁夏天一阁藏明版书《宁夏新志》,弘治十一年那次战事称“蒲草沟之捷”,但并不象夏承焘所说的,“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在此之前,明朝对鞑靼已有“虚武口之捷”、“五并之捷”、“花果园之捷”、“大坝之捷”等数次胜利。而且,这次“蒲草沟之捷”仅用兵六千,战果也仅“斩首四十余级,获牛马羊器仗甚众”而已,实在没有夸饰的必要。关于王越:夏承焘称王越辈“身分和岳飞相同”,这并不符合事实。明朝的王世贞对王越就有“天下咸贵其才而秽其行”的定评。王越结交宦官并因结交宦官获罪,还用金钱、女色等笼络将士,其行径“很少有跟岳飞相似之处”。“那首千古传诵、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名作,跟岳飞的英维气概相一致,洋溢着出自肺腑的真情实感,这不是别人能托名代作的。”
9.李庄临、毛永国《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南开学报》1986年第6期)、周少雄《祝氏谱及岳飞〈满江红〉词考议》(《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前文称,“近来在浙西江山县收集得《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一部,在其卷十四之《诗词歌赋》集中,发现了一首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赠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的和词”。此首《满江红》与后来流传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有同有异,后者当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后文介绍了《祝氏谱》撰修与流传的一般情况,并考析了谱中祝允哲资料的出载年代,认为:“祝氏谱所载资料,有一定可靠性,有可能存录了宋代佚文”;“无论如何种种存疑,岳、祝唱和词并非凭空捏造,当有出处。……退一步说,即使祝氏后人伪作唱和词,岳飞《满江红》词也不可能虚构,其当日流传者也必有另一版本,祝氏所录便是源出异本”。
10.周汝昌解说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见《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8页;后收入《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13页,题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说岳飞〈满江红〉》):文中,作者指出《满江红》词不可能是他人作伪。“今之考证家,动辄敢断此词不见宋人称引,至明始出于世,则伪作何疑,云云。不思作伪者大抵浅薄妄人,笔下能有如许高怀远致乎?”文章还就“贺兰山”方位问题,举赵鼎《花心动》“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句和张元幹《贺新郎》“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句为旁证,说:“这都是南宋初期的爱国词人,他们说到敌人金兵时,能用‘西北’、‘楼兰’,怎么一到岳飞,就用不得‘贺兰山’,用不得‘匈奴’了呢?我自然不敢‘保证’此词必定真是岳将军手笔,但用那样的逻辑去断言此词必伪,怎敢欣然而同意呢?”
上列诸种观点和论据,“疑伪者”只进行了个别的、有限度的回应,如朱瑞熙《〈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的伪作》一文(原发表于《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后收入《疁城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424页),认为祝氏祖谱有造假嫌疑等。“疑伪者”一方当然也有新的提法,如孙述宇在《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台湾《中国时报》1980年9月10日)一文中就提出:“岳飞用自己的事迹、典故”是匪夷所思;“三十功名”和“尘与土”先是自矜,后是“不够诚实的轻视”,语意有矛盾;《满江红》与岳飞的《小重山》格调有异,不会同出一人之手。又如沈克尼《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谈〈满江红〉不是岳飞所写》一文(《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l期),也对“长车”提出疑问,认为战车(即“长车”)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作战工具,后来被步骑兵代替直至明朝,岳飞作战也没有使用战车的史料,故《满江红》不会出自岳飞之手而只能为明人所拟。但这些说法一经提出,就遭到“认真者”一方的猛烈反击,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就大多数疑伪者而言,只能坚持余、夏旧说,或稍有发挥。出现的较重要的文章,如有徐著新的《不是岳飞的〈满江红〉》(香港《明报月刊》1980年10月号)、吴战垒的《难以推倒的疑案——谈岳飞〈满江红〉词》(《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张政烺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1985年)等。但无论从研究者和作品的数量,还是论辩的质量、气势以及效果来看,“认真者”一方都是明显占了上风的。另有主张断语不可轻下的,如王瑞来《断语不可轻下——也谈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实际上也是倾向于“认真者”一方的。
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10年代,论争的余波依然存在,发表的相关文章也有二十余篇,但已属于消歇期。其中,较重要的文章,有郭光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489-501(1997年)、王曾瑜的《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等。郭文以南宋人陈郁《藏一话腴》一版本有岳飞“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等材料为据,认为其词“不是赝品”,“而是岳飞抒怀言志的代表作”。王文则进一步把此词的作年定于岳飞“绍兴四年(公元1134)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疑伪者”一方也有不同程度的反击,甚至有提出《满江红》作者为于谦者。但综观双方的论辩,新的真正有分量的观点和论据很少,进一步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论争,似乎只能期待新材料的发现与问世了。至于2010、2012年又有人提出《满江红》词为岳飞作于阴沙(今江苏靖江)或南京牛首山,论证的效力都比较弱,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二、《满江红》词今天是否应当避讳?
1984年8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熊锡元《岳飞〈满江红〉今天应当避讳》一文,把《满江红》词的“避讳”问题提了出来。文章认为:“岳飞是一个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满江红》词也是可以读的,但是若要对岳飞形象无限拔高,百般渲染,并把《满江红》词加上曲谱,引吭高歌,在今日却未必恰当。”理由是:“激发爱国情绪以对抗国外敌人可能的来侵”,“引用昔日国内民族争斗的事例”不妥。“这样两件时代不同、性质各异、应当内外有别的事情,用同样一种爱国主义感情把它们串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满江红》词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两句,所指对象都很明确具体”,“今日引吭高歌这样的词句,对民族关系无疑只能起到刺激感情的消极作用”,“这样的古为今用,少数民族是不会赞同的”。“当时岳飞写出‘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词句,是可以理解的;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抗御外敌入侵的场合,此类词句却是不宜提倡使用,大可不必返回原始去的”。文章最后强调:“今天我们援引历史上有关国内民族纷争的材料,有必要考虑是否会影响今日的民族关系”,“有所选择,有所避讳是必要的、正常的、合乎事理的、有益于现实民族关系的”。而且应把这一点作为“研究民族关系、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的“一个原则”。否则,“不加选择,不是有所避讳,表面上是尊重历史,实际上却成了客观主义”。
针对熊锡元的观点,赵勤轩发表《岳飞的〈满江红〉词与爱国主义》(《光明日报》1984年10月31日)一文,进行驳难。(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肯定岳飞“是爱国民族英雄”。认为:“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以黄河、长江一带中原政权为中央政权,联合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在稳定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形成之前,中国地域上的民族战争既是国内民族争斗,也带有国与国(包括宗主国与臣属国)之间相争的性质。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在这些争斗中产生的热爱本民族生息的故土、致力于中国统一的英雄人物,都是爱国民族英雄。而衡量这些争斗的是非功过,终究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统一和完整以及各民族的团结和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岳飞保宋抗金,具有历史的正义与进步的性质,是爱国的民族英雄,值得也应该加以宣扬”。(二)《满江红》“在长期的流传中,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激励了无数“爱国的志士仁人”,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两句,是“形象、夸张的文学手法”,“只是形象地表现了岳飞抗敌救国的雄心壮志,并非真的吃人肉、喝人血”。岳飞“好贤礼士”,“治军主张‘仁、信、智、勇、严,缺一不可’”,“经常告戒部下‘慎勿妄杀’,对俘虏的金将‘察其可用者结以恩义,遣还’”,“如果根据‘饥餐’、‘渴饮’的诗句,就推断岳飞茹毛饮血,这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臆测”,也“没有人会把它呆板地理解为‘返回原始去’”。(四)关于传唱此词是否会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文章指出:“《满江红》传唱至今,并没有影响民族关系,也没听说那个少数民族‘对号入座’,提出异议。”现在提出唱《满江红》“刺激民族感情、少数民族不会赞同”并无“事实根据”。(五)文章还辨证地分析了爱国主义,认为:“祖国、爱国主义,都是历史范畴。现代国家都有其古远的形成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既有一脉相承的共同之处,即对祖国——本民族生息的故土的热爱,也有具体历史条件规定的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前者经过历史的抽象升华、凝固为民族的精神美德,后者则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失去意义。我们继承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当然是继承其精神,热爱今日之祖国,而不是照抄某些历史细节”,“机械地用现代国家概念和民族政策去衡量、取舍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文章最后反驳道:“如果岳飞和他的《满江红》也要避讳,那么文天祥、秋瑾、孙中山和汉唐时期的边塞诗,势必也都在避讳之列,而秦桧、吴三桂之流倒成了民族团结的功臣。这岂不是历史的颠倒!这种不分历史是非无原则的避讳,不仅不能减弱民族矛盾,反而只能使广大群众的思想更加混乱,不但不能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只能导致取消爱国主义。”
十数年后,陈英武也发表《〈岳飞〈满江红〉词今天应当避讳〉一文质疑》(《渤海学刊》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对岳飞《满江红》词的评价“关系到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古代文学遗产和如何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大原则问题,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就作出结论”。文章引用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做理论依据,具体分析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事实,以此来否定熊锡元的观点。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岳飞《满江红》词作者问题进行大讨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这首词可能牵涉到的所谓“民族关系”问题。关于1962年2月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撰写和发表的初衷,邓广铭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一文中就曾透漏道:“夏老认为现在北方少数民族的人对岳飞这首词很反感,如果断定不是岳飞作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当时此一问题没有明确提出,因而也没有展开具体的讨论。
三、《满江红》词涉及到的英雄、爱国与忠君问题
1994年12月,《名作欣赏》(1994年第6期)发表王富仁《诗与英雄——对于岳飞〈满江红〉词的一点异议》一文,从“诗与英雄”的角度立论,对岳飞《满江红》词所涉及到的英雄、爱国问题提出质疑。该文认为,“美的不一定是英雄的,英雄的也不一定是美的”,“那些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伟大的业绩、表现出了英雄气概的人,却又往往并不建立在崇高的精神基础上,就其灵魂的美和道德的纯而言,反而表现着明显的不足”,“就以岳飞的《满江红》为例,我认为人们便常常只注意它表达的英雄气概,而并不注意它的意识基础,从而对这首诗普遍作了不适当的、过火的赞扬”。首先,“吃人肉、喝人血的场面是不美的,将人肉如饿鬼一般地大嚼大咽,一边喝人血一边狂笑嘶叫,就更令人胆寒”,而且,岳飞“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两句所指向的敌人,“已不是作为整体的敌人,而是作为一个个的人,这使人感到的不是战争本身的残酷,而成了诗人自己的残酷”。其次,“‘臣子’一词在该词中具有强大的颠覆作用”,这首词在“思想意识的网络或结构”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即:“自我的生存价值就是要建功立业,所谓功业就是要为君主排忧解难。这个思想意识的结构不是审美性的,而是实利性的。它把诗人自我与读者、与整个人类的精神需求和美的理想的追求隔离开来。诗人的自我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功名,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君尽忠、为君效力。”这使得“我们”“感到它的感情是无根的、虚浮的,外壮内不壮”,“像‘怒发冲冠’,像‘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都缺乏底气,是自我感情的夸张性表现”,“就全诗而言,则觉得如观勇士献技,虽见其勇,服其志,感其气,一时情绪振奋,心神俱旺,但终觉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数年后的1998年,王振泰对此文“仍如骨鲠在喉”,于是撰写《渴饮饥餐原磊落——谈岳飞〈满江红〉兼与〈诗与英雄〉一文商榷》一文(《名作欣赏》1998年第5期),进行反驳。文章指出:“对于专门从事美学艺术理论研究但又本身无创作实践的人来说,有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主观而自以为是,实则往往都似是而实非。从美学角度鉴赏之,一定要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进入如同原作者当时那般的创作氛围,而不是要原作者服从审美主体”。文章认为,岳词中,“‘臣子恨’,即君主恨,天下恨也,民族恨也”,其词“气足神完”,其气“充塞天地,至刚至正至大”,不是无底气,而是“满有底气”,是“大底气”。此底气,“便是其母刺字‘精忠报国’,便是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便是光复中原河山的决心”。在封建社会,英雄人物“莫不忠于君”,要“正视历史存在的客观实际”。至于“饥餐”、“渴饮”之夸张、写意、激烈语,文章认为,这在史书、小说、诗词中“毫不鲜见”,“因为是写战争这种特殊的残酷题材,一点也不足怪”。作者还举出现代的例子:“《义勇军进行曲》高声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多么激励中华儿女之心!其谁曰: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是宣扬战场中真的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呢?此乃正是表现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誓言!无疑最具有号召力!怎么当年的岳飞的‘饥餐’‘渴饮’便不能接受呢?”最后,文章又列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中方在北京招待会上安排演唱岳飞《满江红》词,以及伟人毛泽东喜欢这首词的事实,认为:“岳飞这首词集中地代表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代表了光荣的英雄传统。”
针对王富仁的观点,周桂峰也发文逐一进行反驳(《时代之子与时代之声——也谈岳飞的〈满江红〉》,见《集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文章认为:“要准确理解、公正评价一个艺术作品,前提便是要把这个艺术作品放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那个原生环境里加以评判。”如果将“饥餐”“渴饮”的形象“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移放到一个天下太平、春和景明、鸟语花香的环境里,便会因为与环境格格不入而显得不美”。但是,“如果将它放在一个血火交迸的背景里,则会因为与环境协调而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美。而一旦将这种形象与一个民族的尊严联系在一起、与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存权利联系在一起,则毫无疑问是美的”,就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是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而歌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是抗日战争年代里最美的形象”一样。
在争论中,一些文章已经不限于《满江红》词,而是扩大开来,把眼光放在岳飞以及文天祥、史可法等与岳飞相类的历史人物身上,就英雄、民族英雄以及爱国、忠君等问题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探讨和论争。
早在1981年,《安徽教育》(1981年第4期)就发表了《邓广铭教授对岳飞评价问题的复信》,认为“岳飞称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并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与阐释。但之后,一些人又一度对岳飞民族英雄身份的认定发生了怀疑,以致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颁布后,有关方面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学习指导》,也以要利于民族团结为由,不再称反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侵略的岳飞、文天祥等人为民族英雄,而只称像郑成功、林则徐这样反对外来民族入侵的历史人物是民族英雄。此论一出,舆论哗然,使得教育部有关部门不得不召开记者招待会,郑重对此问题予以澄清,称这只是学术探讨,是某些专家、学者“个人”的看法,并不是“《教学大纲》文件本身的内容”,教育部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都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岳飞文天祥是否是民族英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就高中历史教育中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见《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10日)。后来,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还在《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新闻实践》2009年第1期)一文中,回顾当时的情形说:“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这个问题难道还用说吗?……有人不懂,学者随便说说都可以,问题是国家教育部门代表政府,该是什么态度。事关民族大义、历史评价、青少年教育、爱国主义传统。可惜教育部门的发布会含混其辞,不敢大声说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而是说:我们在大纲里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还说,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分歧,不宜引入中小学教材。这篇稿(按有一篇稿件已经排定《人民日报》版面)被我坚决撤了下来,虽然是一个部级正式的新闻发布会的稿子还是不能用。……岳飞、文天祥已成了民族精神的代名词,成了正义的化身。……从哲学上讲,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普通的常识,从政治上讲,这种事还能搞新闻发布会?”
和民族英雄问题相关联的,还有岳飞等人是否“愚忠”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较为重要的争鸣文章有龚延明的《岳飞是“精忠”还是“愚忠”辨析》(《学术月刊》2002年第4期)、降大任的《民族英雄问题再思考——从岳飞、文天祥的评价说起》(《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叶文宪的《忠奸之辩——以岳飞和秦桧为例论忠君与爱国》(《探索与争鸣》2004第6期)、孙果达的《岳飞是铁定的民族英雄——与叶文宪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04第10期)、叶文宪的《中国古代有没有爱国主义——论国家与王朝、爱国与忠君、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探索与争鸣》2006第1期)、王曾瑜《岳飞、文天祥不该称为民族英雄吗》(《北京日报》2006年7月24日)等。
这种争论甚至还波及到了国外。刚进入21世纪,在新加坡就开展了一场岳飞是否精忠报国的大讨论,连政界高层也涉入激辩之中。一派认为应借岳飞宣扬爱国主义;另一派则批评岳飞愚忠,认为其忠弊多于利,甚至妨碍当下民主社会的建设,不值得提倡。副总理李显龙(2004年任总理)则态度明确,他大声疾呼,号召年轻人学习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为建设新加坡做出贡献。
四、这场论争的意义与启示
关于这场论争的意义,最积极的方面,是基本解决了由《满江红》一词连及的民族情感、民族英雄问题,廓清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一些不确当认识。这一问题不仅是学术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涉及到了如何看待民族历史、民族情感、民族英雄和如何爱国等重大问题,勾连历史与现实,意义重大。这一问题的基本澄清,有效地阻止了某些糊涂认识的发酵和扩散,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梁衡《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一文的发表和《新华文摘》(2009年第8期)对此文的全文转载,可视作对这一争论的收结。此后,在公共媒介,再也没有发出过对此问题进行争论的声音。
而关于《满江红》一词论争的基本方面,即该词著作权是否归属于岳飞,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虽然2009年之后,“疑伪者”一方已没有文章发表,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至于“认真者”一方,更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原初主张,虽然2007年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一文发表后,也只有零星的文章见诸报刊。从表面上看,自上世纪90年代后,双方短兵相接、剑拔弩张的交锋场面已基本不见,但各自所持的观点还在森严地对立着,且不存在调和和妥协的可能性。这充分表现在,不仅没有任何参与者公开修正或改变自己的原有看法,而且双方重要人物的重要文章,很多还在发表的几年、十几年之后,收入了他们重要的文集中,特别是双方主将夏承焘和邓广铭的《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和《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更是在发表二、三十年之后,分别收入了他们各自的总集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论争双方所具有的可贵的学术自信和学术精神。他们似乎都在以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为范例,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坚守质疑和反质疑精神,如何从“疑”开始,展开有成效的学术研究。这,应该是这场论争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至于启示的其他方面,如学术争论要感性服从理性,可以充满感情、满怀热情,但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等等,也应该特别注意。据相关人士回忆,论辩之初,邓广铭曾劝夏承焘:“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但本也景仰岳飞和重视《满江红》词的夏承焘并没有接受。他说:“实事求是地考证它的作者作年,是我们研究这首词的一方面;估计它的时代意义、创作动机和历史价值,是它的另一方面”,“过重感情不愿意说它不是岳飞之作,或者因为它不是岳飞之作便一笔抹杀它的历史意义,这都不是严肃的科学精神,不是对待这首历史名作的正确的态度”。而“认真者”一方在论辩中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并不是一味地强辩回护,而是针对对方的质疑,遵循论据和论证原则,极力爬梳历史材料,进行合理的反质疑,带有很强的客观性。当年邓广铭就《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给臧克家的回信中就曾说:“你说《再论》对《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已‘给以科学上的论证’,这却大有‘内台喝采’之嫌。我在文中所作出的论断,尽管在我是具有自信的,而且也已经得到你的赞同,但是,一个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我的论断究竟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否,毕竟还得看看有怎样的反应,不能遽尔视为定论。”再则,参与论辩者还在一定程度上抛却了门户之见,也给这场论辩增添了一些亮色。余嘉锡弟子靳极苍就曾在发表《关于岳飞〈满江红〉词》(《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时说:“我爱吾师,我敬吾师,但不同的意见,还是要说出的。”至于论辩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下过断语,且坚守自己的观点,也算不得通常意义上的武断和固执,而被视作论辩中的瑕疵。相信一旦有可以作为直接证据的可靠材料出现,无论哪一方,都会泰然接受,并修正或改变自己的看法的。因为,这是一场纯然的君子之辩、一场纯粹的学术之争。
目前,大众接受者依然高唱着岳飞的《满江红》,并从中汲取力量,就像半个世纪前那样。而一方面,《满江红》(怒发冲冠)词著作权的学术争论还在或显性或隐性地持续着。两种景观、两样声口,都魅力无穷,可赏可赞!
原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作者:郭红欣。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