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
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

文/郭声波
“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扬雄《蜀都赋》以寥寥十字,形象地描绘了汉代成都壮丽的河流景观。有人说,“两江”指的是当时的郫江和检江(流江);也有人说,“两江”指的是内江和外江,内江离城较近,靠内,外江离城较远,靠外,故名。其实在成都境内,内江就是郫江,外江就是检江(流江),名虽殊而实皆一,只不过内江和外江是后起的别名,见于记载要晚到魏晋南北朝罢了。
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有关巴蜀的历史文献中,却常常提到有“内水”、“外水”,它们与内江、外江又是什么关系呢?
四川盆地“内、外水”河名的实际出现时间不晚于东汉。据陈寿《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至江州,分遣赵云“从外水上江阳”。江州县在今重庆市中区,江阳县在今泸州市中区,则,外水必指今川江无疑。有“外”则必有“内”,“内水”一名虽尚未见到汉人记载,但可由《水经注》引晋人庾仲雍所谓“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加以间接证明。其“左”、“右”方位要么是记载有误,要么是古人有与今不同的方位指说习惯,但无论如何,既然指明了内水的上游是涪(今绵阳),外水的上游是蜀(今成都),那么内水指今绵阳以下涪江段及合川以下嘉陵江段,外水指今成都以下岷江一川江段,必然是确凿无疑的。正由于这已成为常识,所以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二、卷三三反复提到:“涪水至此(垫江,即今合川)入汉水,亦谓之内水也”;“江水自武阳(今彭山)东至彭亡聚,……亦曰外水”。这使我想起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这么一句话:“垫江县,郡西北,中水四百里”有人不理解,以“中水”指今沱江,怎么会跑到巴郡西北的垫江县来了呢?于是把此句断为“垫江县,郡西北中,水四百里。”也有人干脆把“郡西北中水四百里”合为一句,但是都不能解释什么水有四百里。任乃强先生认为“中”字是“内”字之误,一下就使问题涣然冰释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垫江县在巴郡西北,境内有内水四百里。垫江县内水应是指今潼南至北碚—段涪江水道。
此外,关于巴郡城以上涪江—嘉陵江段称内水,岷江—川江段称外水的记载,还见于《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卷四八《朱龄石传》,《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周地图记》等,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
这两条水道何以称作内、外水,至迟清代以前没有人解释。我以为,最起码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内、外水分别是“内江水”和“外江水”的简称,或者说是“内江”和“外江”的早期叫法。《隋书·地理志》云:“僰道,后周置,曰外江·大业初改日僰道。”《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亦名﹝外﹞ (水)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这都是南北朝时成都、僰道(今宜宾)一带的外水又叫外江的明证。至唐宋时代,人们已完全放弃了“内、外水”的称呼,而专用“内、外江”了。如杜甫《送十五弟使蜀》诗云:“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寄岑嘉州》诗云:“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自疏。”自古中原、江南人由水路入蜀,最常用路线有二,一即经
三峡、巴郡(渝州)、垫江(合州)转涪江至涪(绵州)或梓州(今三台)上岸,然后取陆路人成都;即从巴郡(渝州)溯江直上经江阳(泸州)、僰道(戎州)、南安(嘉州)人成都。所以宋人为“百丈内江船”作注说:“水自渝上合州者,谓之内江,由泸、戎上蜀者,谓之外江。”又说:“内江在合州南百步,源出刚氐徼外。……南流至渝州人江,又名内江。”郭知达引赵氏语注《寄岑嘉州》诗说:“嘉州下临大江,汶水自叙历泸连夔,故云与
三峡相接。”这些都很好地解释了杜诗何以将
三峡与内、外江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也证明了唐代内、外江与汉晋内、外水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两条水道要用“内”、“外”来加以区别,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宋人章如愚虽然注意到,自汉晋以来大江为外水,涪江为内水,此为不易之者,但他也不能道其所以然。至清,始有人尝试作出解释。乾隆时,蜀人李元著《蜀水经》云:
按内江以汉、白、涪、梓、渠五源之水归合州而合流,《汉志》以汉为径流,而涪水逼近会城,晋汉用兵多由之,故庾仲雍称内水,独系以涪,后遂称此水为涪江,而汉名隐矣。
这是说,在嘉陵江水系五水之中,本以西汉水(今嘉陵江)为正流,但涪水最靠近蜀中都会成都,被称为内水,汉晋时为用兵要道,所以后来渐渐又把涪水视作五水的正流了。稍后成书的陈登龙《蜀水考》也沿用了这个说法。我认为这种解释是符合情理的。
与这种以成都为中心区分内、外相似的观点,还见于本文开头提到的对成都郫、检(流)两江别名的解释。
郫检(流)两江之别称为内、外江,最早见于晋杜预所撰《益州记》:“郫江为内江,流江为外江。”与唐初《括地志》所谓“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笮﹞(管)桥水,一名﹝流﹞(清)江,亦名﹝外﹞(水)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郫江亦名成都江,一名市桥江,一名﹝都﹞(中日)江,亦曰内江,西北自新繁县界流来。二江并在成都县界”大体一致,但是汉晋时大江正流是不流经成都的,大江从温江东决经流成都的时间大约是在刘宋、萧齐间,不晚于萧梁,因此确切地说,并非整条大江都叫流江,并非整条大江都可称外江,而是只有大江与检(流)江在成都县西界合流后流经成都城南那--段河流及其下游才可称外江。此即“二江并在成都县界”之谓也。宋人以为,“流江为外江,郫江为内江,此即成都一城言之也”(章如愚《山堂杂论》),虽然不够确切,但明确指出“内”“外”之义是相对于成都城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岷江—川江的另一条重要支流——乌江,至迟在晋代也被称作内江水或内江。《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涪州武龙县条记载:“内江,一名涪陵江,一名巴江,在县,屈曲北流。水自黔州信宁县界人。李膺《益州记》云:‘内江水自万宁西北二百八十里至关头滩,滩北百步,悬崖倒水,舟楫莫通。’”此外在黔州彭水,思州思王、思邛诸县条下亦记有内江或内江水。
李膺是南朝齐、梁间人;万宁县,在今贵州思南县境,本名永宁,刘先主时更名,刘宋时陷于蛮獠,因此推知乌江之始称“内江水”,不会晚于晋代。除《太平寰宇记》而外,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思州务川、费州涪川县条,宋代的《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涪州、思州条,都留下了黔江(即今乌江)又名内江或内江水的记载,因此,“内江”作为那时黔江的别名是毫无疑问的。与它相对应的“外江”或“外江水”,由于没有见到其他材料,因而只能认为仍然是指岷江—川江。
从地理位置上看,乌江之称为“内江”,无论如何与成都沾不上边,显然,乌江“内江”不是以成都得名。那么是不是相对某一腹心地区区别内、外呢?也不是。因为这种腹地,在全国一般指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在四川盆地一般指都会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对关中地区来说,四川盆地最近最大的河流是嘉陵江,而不是乌江;对成都平原来说,最近最大的河流是岷江,也不是乌江。显然,四川盆地内、外江的得名并不一定都与成都或成都平原有关系。
为了解开乌江“内江”得名之谜,我们不妨将眼光顺着长江下移。
长江流出三峡后,至今松滋老城西北三里开始形成分汊河道,先秦两汉时代,南江称为江,为干流,北江称为沱,为支津;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唐宋时代内江流经枝江县城,外江流经松滋县城;当明代内江径流量不断增大并超过外江之后,江、沱易位,“内、外江”之名遂成为
历史。枝江一名始于唐,在这里,沱、内江、枝江一脉相承,很明显都是“支津”、“支流”的意思,是相对江、外江、长江而言,而不是相对某个城市、某个地区而言。
回顾一下乌江与川江的关系,也是支流与干流的关系,它与枝江一样,都以干流长江为外江,自己作为支流或支津则称内江。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长江中上游一带居民特有的地名文化的一种体现。这样解释,许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
至于支流为什么称内而不称外,干流为什么称外而不称内,这也很好解释。有这么一个故事:南宋淳熙年间,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应召赴阙,舟次涪州(今涪陵),忽遇长江风浪,他只好移舟夜泊乌江,并作诗记其事:“黄沙翻浪攻排亭,渍淖百尺呀成坑。……水从岷来如浊泾,夜傍黔江聊濯缨。玻璃彻底镜面清,钓丝随风浮月明。”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江干流,一边是风平浪静的支流,航船踅入支流,就像躲进天然避风港,并且这条支流也可通航,航行起来比大江安全得多,因此对舟人来说,孰为内,孰为外,不就是明摆着的吗?当然,也不是说凡是岷江—川江的支流都应该称为内江,如大渡河、金沙江,它们平时的波涛激流就要险过岷江—川江,并且自身也不能通航,航船是不会到那里去躲避风浪的。
另外,川江还有一条重要支流——沱江,也曾被称作“内江”,不过,这条内江的得名,却与上述两种情况又有所不同。
沱江本名中江,隋文帝即位后,为避其父杨忠讳,乃改为内江,连带把中江县也改名为内江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但是沱江在金堂县大渡口(今金堂县城赵镇)汇合洛水、绵水后才叫内江,距成都最近处也有一百里,比外江到成都的距离还远,不可能像郫江那样因相对外江近于成都而称内江;另一方面,沱江没有大支流,也不可能像涪江那样因为在各支流中最靠近成都而称内江;再有,沱江水源虽主要来自都江堰之“内江”,但都江堰“内江”一名是清代出现的(详后),与隋代沱江之称内江无关。
那么是否因为它也是作为川江的支流,像乌江“内江”那样相对川江“外江”而称“内江”呢?从时间上看,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如《周书》卷二八《陆腾传》就有“资州铁山獠抄断内江路”的记载。但《周书》系唐人所撰,所用传记资料是否已依隋讳改“中”为“内”亦未可知。并且更多的迹象表明,隋朝避杨忠讳改动带“中”字地名的,除极个别情况如中都改用旧名榆次而外,基本上都是用“内”字代替“中”字,如云中改云内,阆中改阆内,中牟改内牟,中部改内部之类,可以说这是一条规律,多半是由于“内”为“中”之可替换近义词的缘故,这种“内”不一定要与“外”相呼应。
为什么四川盆地的“内江”涵义会出现以上三种不同的情况呢?
拙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经过详细论证,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四川盆地的居民作为文化构造者在不同的
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在秦灭蜀以前,四川盆地居民以蜀人、巴人为主,那时的河名基本上都是单音词,如江、沱、湔、沫等,决没有“内、外水”、“内、外江”之分。秦汉时代,来自关中、“山东”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与巴蜀土著一起创造着四川文化,这时的河名大多带上了通名“水”字、“江”字,显然是受了北方汉族系统地名文化的影响。涪江—嘉陵江之称内水,岷江—川江之称外水,与青衣江之称南江,绵阳河之称北江,江水之称大江,沱江之称小江一样,用方位、大小等限制词作为一些主要河流的别名,应该都属于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文化杰作。
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一个新的文化阶段。这时期的移民情况异常复杂,首先是人民移进移出及境内迁徙十分频繁,迄止隋统一 ,见于记载的不下20起,隋末唐初,唐肃宗时代、僖宗时代及南宋初年、末年,又有几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入蜀;另外在移民来源方面,既有关陇氐羌,又有西南蛮僚,当然更多的还是北方的汉民。这些移民活动大多出于自发,往往整郡整县,动辄数万家即为一批,在移入四川后,很容易形成分区聚居的状态,如关陇移民多居于成都平原及川陕通途一带,越雟百姓居于成都以南川滇大道一带, 牂柯僚人则散布丘陵地区,唐武后时川西汉民居地又向东扩展,宋末川、陕难民又集中分布于嘉陵,江一川江“y”型区。因此在地名文化上,既承袭了秦汉时代体现北方文化特征的命名习惯,又出现了杂乱无章各自为政的无序化特点。就如河名,一方面承袭了以“水”、“江”作通名,以“南、北”、“大、小”、“内、外”、“前、后等限制词作别名的命名习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重复命名、错误命名的情况。
关于重复命名,如南、北江就出现了两对,一对是青衣江与绵阳河,另一对是新出现的检江与郫江(见拙文《成都平原的南、北江补考》)。清水出现了四条,即今双流江安河、广元下寺河、巴中恩阳河、开县东河。流江出现了两条,即今成都清水河—南河、渠县流江河。巴江出现了两条,即今南江神潭河、涪陵乌江。沱江出现了两条,即今泸州沱江、汶川杂谷脑河。大江出现了两条,即今岷江—川江、达州前河—州河。内江如前所述,也出现了四条,并且河名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中沱江“内江”由中江更名时,四川盆地已经有三条内江存在,隋朝官方仍然要不厌其烦地取“内江”为名。这些情况不正好说明当时四川地名文化的无序化特点吗?
关于错误命名,主要是由于人民迁徙频繁,不少原住居民使用的地名不为后来移入的新居民所知,这些新居民往往要依靠旧有的文献记载来给山川确定名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文献记载有误,或者他们对文献记载的理解有误,都可能导致他们确定的地名张冠李戴,出现“地名搬家”现象。
其例之一,今中江县之中江,汉晋称五城水,唐宋元明清称罗江,清以后又称凯江,沿革清楚。然而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谓“梓州城,宋元嘉中筑,左带涪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冲要”以后,罗江又别称中江,宋人因之,真宗时避圣祖玄朗讳,遂改玄武县为中江县,并相沿至今。拙文《成都平原的中江与前后江》已论证其为《元和郡县图志》作者误解南北朝人“左带涪水,右挟中江”一语真正意指所致,并且由于这一错误, 连带把中江(即今沱江)的别名‘内江”也一并移到罗江头上。兹不赘述。
其例之二,成都两江如前所考,郫为内。流为外,本无疑义,然至南宋时,却有人反以郫江为外江,流江为内江,事见祝穆《方舆胜览》卷五一引《皇朝郡县志》:“初,太守凿离堆,又开二渠,﹝一渠﹞由永康过新繁人成都,谓之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人成都,谓之内江。高骈未筑罗城,内、外江皆从城西人。自骈筑城,遂从西北作縻枣堰,堰外江绕城北而东注,于合江﹝亭﹞复回内江水,循城南而与外水俱注。”按永康军治今都江堰市,由永康过新繁人成都者,即郫江,由永康过郫县人成都者,即流江。该记载既与前引《括地志》相悖,也与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九所谓“外江在今罗城之南笮桥下,内江西今子城之南众安桥下,自唐乾符中高骈筑罗城,遂作縻枣堰,转内江水从城北流,又屈而南与外江合,故今子城之南不复成江”不合。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此《皇朝郡县志》实即《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范子长《皇州郡县志》二,范子长为南宋光宗、宁宗时成都人,按理不应该对本地重要河名混淆不清,但是如果怀疑“内”、“外”倒置系祝穆转引有误,或系“传刻之讹”,从短短数句竟有五处“内”、“外”倒置的情况判断,也不大可能。因此我认为范氏原书就是如此,之所以与前人记载不合,其原因大概是成都两江“内、外江”的别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久已不用,文人著述时往往靠稽征故史,范氏尽管是成都人,但他恰好就在征引故史时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将内、外江的位置弄颠倒了。尽管卷帙浩大的《皇朝郡县志》(100卷)入元以后即已亡佚,但70卷本的《方舆胜览》却“盛行于宋末元明,不仅为缀文之士所重视,对当时的地志编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现存的元揭傒斯《蜀堰碑》,明、清《一统志》,四川、成都地方志及《读史方舆纪要》,无一不是采用的与北宋以前“郫内流外”说完全相反的“郫外流内”说,内、外易位遂成定案。追究其滥觞,显然范子长与祝穆难逃其咎。
与三国两晋至两宋间相比,元明清至今,由于新移民基本上都是来自淮河以南的湖广及东南地区,文化特性较为近似,都属于南方汉族文化系统,并且多有官方组织,移入地之间没有人为隔阂,呈大杂居状态,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反映到地名文化上,四川盆地的河名就要有条理得多了。除东、南、西、北等用于方位指示的词仍重复用于少数河流别名而外,其他如大小、内外、前后及实义河名的重复命名现象在主要河流中已基本消失。就如内江而言,流江“内江”改名走马河—清水河—南河,涪江“内江”专用涪江,沱江“内江”专用沱江,黔江“内江”改用乌江,罗江“内江”改用凯江,只有郫江“内江”仍继续使用,但其正名郫江已改称“府河”。至于外江、岷江—川江及流江已不再用此作别名,郫江“外江”也因为是沿讹得名,除方志中作为历史河名仍予转载外,实际上从未在民间使用过。元明时代真正与府河“内江”相对应并实际使用过的“外江”,是新起的沱江(湔江、蒲阳河)—青白江“外江”。有关记载见于元揭傒斯《蜀堰碑》:
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于外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堰,东入于彭、汉之间。
此万工堰又叫官渠堰,在今彭州市西与都江堰市相邻处之蒲阳河上。又,嘉靖《四川总志》卷一六《水利》云:“外江北经崇宁、彭县、新繁、汉州界出金堂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云:“北江北出宝瓶口,经崇宁、彭县、新繁新都而入汉州雒水东南流为金堂河者,此所谓湔水也,成都人名之曰外江”。“新都县有湔水,自新繁县东北流,过县北,入汉州境。湔水即府境之外江矣”。其所以名以“外”,很明显是因为府河“内江”距成都较近,而沱江(湔江、蒲阳河)—青白江距成都较远的缘故。由于府河中段在明末因修筑筑断堰(在今郫县东团结镇)截流东注沱江,致使府河下游独受油子河水,流量大减,航运中断,尽管清康熙间在筑断堰实行春闭秋开制度,但府河航运并未恢复到昔日景况,它在成都的地位日渐衰落,“内江”之名亦随之湮没无闻。
耐人寻味的是,一对“内、外江”消失了,另一对“内、外江”又代之而起。恰好也是从明末起,作为沱江江首段(即今鱼嘴至都江堰市城南太平桥段)别名的“北江”一名因为其下游改道而湮灭(见拙文《成都平原的南、北江》),大概这里的河名不可一日没有别名,人们又按照古老的习惯给这段沱江命名为“内江”,与之相应,岷江正流鱼嘴至新津段也加以“外江”的别名。有人说,其所以区别内、外,是因为鱼嘴内江水涨时余水会从飞沙堰外泄岷江。其实,这与鱼嘴内江作为岷江支津而得名是大体一致的,都是古老的深厚的四川地名文化的再现。看来,四川人特别是成都平原的居民对“内、外江”名称确实有特别的爱好。
总之,元明清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尽管内外江名称仍有迁移更改,但已基本消除了前一时期重复命名、错误命名的杂乱无章状态,对河流的命名明显地从无序化向有序化转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它再一次启示我们,在
历史地名的演变中,居民文化的特性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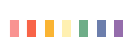
文章来源:《历史地理》第十七辑
第422页-428页
文章作者:郭声波
文章转化:白琳蔓
本期编辑:白琳蔓
终校:周辰
审订:杨振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请参照原文~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