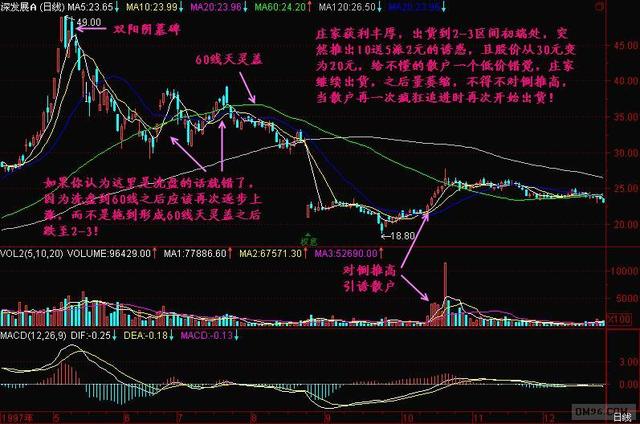———— 玄诚子言 ————
《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如果将“斯人”换成“是人”容易让人形成反义和对比。一读到“是人”马上联想到“不是人”。
《论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句话是不仅仅只是儒家的精神所在。在道家佛教里面也只有达到这种精神的人才能称之为“圣人”。
而孟子的话是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圣人”精神一脉相承的。
而“是人”对人的要求很低,远达不到要用来说的地步。
“斯人”却饱涵文学诗书的古文韵味。第二点“斯人”比“是人”在所指意义上较为悠长,品味更为高雅。更能体现古文信雅达的文字效果,为全文增色不少。

就像文中之眼,如果“斯人”换成“是人”,就像没有了这双炯炯有神的圣人之眼。
如果换成“是人”,全文的韵致就显得俗不可耐,意义也缺乏一种深刻与悠长,也与全文不连贯。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中的“斯人”和“是人”的意思都可以理解为:这个人、这样的人,但是此处为代词的“斯人”,指代前文中的舜、傅说、胶鬲、管夷、孙叔敖、百里奚。——也就是那些已经通过个人修身的努力获得成功的贤人。而“是人”却没有这层意思,对人的要求也与全文不符。

儒家的道统便是做君子,“斯人”与“是人”就是道统的区别。古文讲究韵味,这韵味是无法用文字的字面解释来解释的。它给人就是一种气质和感觉,并且通过文章的气质熏陶人的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古文要读出声来的原因。因为气质就在语音语感里面。而翻译是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为什么盛唐诗那么强烈——就是气质。李白有什么“意思”——意思很普通,但是盛唐诗表现的就是气质。
杜牧的诗与李白的诗很相近——但杜牧的诗多许多晚唐气:一种失落的哀怨,无可奈何的衰落。
李白的诗也有哀愁,王昌龄,高适等等盛唐诗中都有。但是他们的痛苦都是向上的,壮阔无私的。
而到白居易中唐诗人就多了许多“私”的东西。变得没有那么多壮阔和大气。
这就是文学文章与时代的相应性。
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与当时时代结合相应的“文气”。
而“是人”就很不像古人的语言表达方式。
如果只是作为一个人,只有活着就行了,何必还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而且贫穷的人本来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就ò“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不是在鼓励鼓励穷人去挨饿吗?
况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对管仲,百里奚这种士人君子说的,他们在社会阶层中也与“贫穷”沾不上边。
孔孟学说的主要对象也是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阶级,这是中国古代圣贤学说的时代局限性。是用来建立秩序,统治国家,修身养性的。
既使在八条目中最基础的“修身,齐家”中的“修身”普通人也难有机会做到。平民百姓根本接受不到这些东西,倒也不是孔孟偏爱管理阶层忽视平民百姓。而是时代的局限性就只能如此。
孔孟之道的目的在于教育统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把他们教育好了,平民百姓自然安宁祥和,趋向于理想中的大同社会。
古代的穷人很少有人读得上书,像朱买臣这种很可能就是故事和特例。
能吃饱喝足,合理的生老病死不就“是人”了吗?
也不必“斯人独憔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人的文字语言习惯就是“斯人”。
古文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解释,还要通过全文来理解。
而“是人”很像是现代汉语的翻译。在古文中“是人”一词很难找到与其搭配的高雅文章。我说的是“高雅”而不是庸俗,也不是看不起庸俗。因为语言文字不仅仅只是记录。
然而像《论语》《孟子》《易经》《尚书》《道德经》《庄子》《古文观止》《史记》……这样的圣贤学问怎么会用一些庸俗语词来与文章搭配呢?
古代的学问家也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就像董仲舒,朱熹哪怕他们的学问上再有错误和疑义。但是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文字失去信达雅的效果。
与此同时,在高雅诗歌,文学中也不会让自己的文字失去信达雅的效果,使自己的文章不能登大雅之堂。
“斯人独憔悴”与“是人独憔悴”——能够理解并解释唐诗宋词三百首的人都能觉察出这其中的奥妙。
#圣人言#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独憔悴

(图片来自于网络,可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