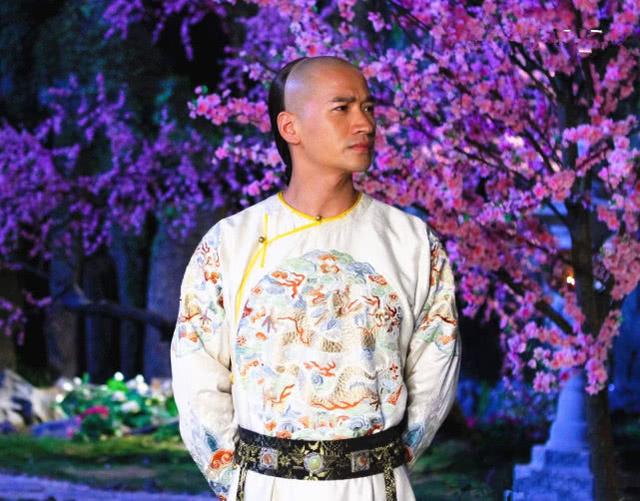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按】编者汇总董元奔在不同媒体发表的篇幅为1500字左右的原创文史评论,以便于保存。拟分80辑推发,凡999篇。作品为原创,欢迎转发,侵权必究(特别支持维权机制打击W易平台诸多作者抄袭本头条号原创文章的违法行为)。

(图片:作者2021年春节在书房)
董元奔文史评论-周安王至周慎靓王时期(前401-前315年)目录
【086】郭子的哲学
【087】张仪出生年考
【088】辞简意丰司马光
【089】卫鞅不死,新法不行
【090】司马光非圣人
【091】春秋战国重分野
【092】时代造就变法派
【093】卫侯称君,宋侯称王
【086】郭子的哲学
我国最近一次大规模出土的书简,是1993年10月从湖北荆门市郭店镇的一处战国楚墓发掘中得到的,该墓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00年。当时,一共出土了804枚竹简,字数达13000多,北大教授庞朴先生把它们整理成18篇文章。这些文章多为儒家著作,其中有的作品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少数为道家著作,有的文字同样发展了道家思想。目前没有证据能说明这些作品是战国以前的某人所作,因而只能断定是墓主人所作,而能够留下13000多字的学术著作,对于先秦学者来说,也算是大学者了。那么,墓主人就是一个介于孔子和孟子之间的大儒了。
然而,包括《史记》在内的中国古代史书并没有记载过孔子和孟子之间还有一位儒家学说的伟大传递者,先秦道家代表人物除老子庄子之外,也没有第三个伟大的道家学者。而郭店墓主人的墓很小,墓葬中除了这些书简之外,陪葬品也就只有两根拐杖和一套酒器等,可见,墓主人不是高等贵族,但是,他有拐杖,应该是年老的人,他有酒器,应该是爱喝酒的人。在战国时期,一位爱读书爱思考还创作了一批儒家道家学术著作的老人是受人们尊重的,而能够有饮酒的嗜好说明他虽然不是大贵族但是家境还不错,加之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三者结合,可以认为他是战国时期的民间大学者,一个研究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民间大学者。那么,他就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大学者了。
考古活动中没有得到这个大学者的姓名,考古材料上也没有给他使用代名。我不妨把他命名为郭子。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人躬耕田亩却仍然为后人所知的现象很多,那是因为他们起先或者后来做过大官,他们的文章和思想有意无意的通过行政手段传播开来。但是,像郭子这样始终躬耕田亩不求闻达,史书也没有留下一鳞半爪的读书人更多,他们大多如同浩淼的星星湮没于过眼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郭子的著作中有一篇论述道家思想的,全文是: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 ,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在郭子之前,哲学经典中早已论及宇宙生成问题。
《老子》以“道”论宇宙,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算我们能够勉强接受老子所谓的“道”的概念,这样的简单生法,也太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好像这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似乎这单调的“一”、“二”、“三”就是一些小“道”,万物则是更小的“道”了。
《易经》在谈到宇宙生成的理论时,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万物都是八卦的不同组合。《易经》的这个说法虽然也让人费解,但是,其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这个接近几何基数的说法总还是比“一生二,二生三”来得“科学”一点,而其八卦后来经过历代术士在官方和民间的传播,能够被中国古代人普遍接受。
然而,比老子晚了一百年左右的郭子的这个“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学说却是石破天惊的,我很惊讶,在那么早的中国古代,就出现了郭子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辩证法思想,这比黑格尔可是早了两千多年啊,人类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一共才多长啊?!
我们需要从三个层次理解才能参透郭子的宇宙观。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郭子继承了《老子》和《易经》的观点,他相信通过传递的方式一物生一物,也就是:太一生水,水生天,天生地,地生神明,神明生阴阳,阴阳生四时,四时生寒暑,寒暑生湿燥,湿燥生岁。
其次,郭子发展并强调了老子的“道”的思想。在老子的宇宙观中,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后,“道”并没有消失,它在生成其他物的同时,也始终存在于它的生成物中,所以,万物中都有“道”都分享了“道”。郭子认为:太一生水,太一还在水中;水生天,水还在天中;天生地,天也在地中;地生神明,地也在神明中;神明生阴阳,神明也在阴阳中;阴阳生四时,阴阳也在四时中;四时生寒暑,四时也在寒暑中;寒暑生湿燥,寒暑也在湿燥中;湿燥生岁,湿燥也在岁中。郭子举第一次生成例子总结为“太一藏于水”。
最后,郭子从以上两个层次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太一生水之后,水并不是直接生出天的,水是通过反辅太一才生出天的;天生出以后,天也不是直接生出地的,天是通过反辅水才生出地的;地是通过反辅天才生出神明的;神明反辅天生出阴阳;阴阳反辅神明生四时;四时反辅阴阳生寒暑;寒暑反辅四时生湿燥;湿燥反辅寒暑生岁。这就不是简单的基因(“道”或“太一” )的传递,而是物物相成相生以至于万物得以生成的,任何上一级的物都存在于下一级的物中,并接受下一级物的“反辅”达到相容再“共同”去生成更下一级的物。相对于“藏于水”的静态,万物的生成又是动态的,所以说“行于时”。郭子接着对“藏于水,行于时”进一步总结道,“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用词如此简洁,而思想表达得如此透彻。郭子以“反辅”作为特征的辩证法思想令人耳目一新。
我对郭子的这段文字一次又一次平心静气的凝视,我震惊于郭子的辩证宇宙观。一物生一物,两物相容再生他物,世上万物相互搀扶着,交融着,生成着。世上万物的生成如同生生不息的海洋一样波涛翻滚,以活泼的方式被产生着和产生着,这不正是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大自然的规律吗?
在郭子之前,中国哲学中已经有过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观念,我们知道,在阴阳观念确立之前,人类的思想还有一个很漫长的混沌和杂多阶段,是混沌和杂多演化出阴阳然后继续细化演化出五行,再演化出八卦。杂多——阴阳——五行——八卦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得出了相克相生的、静态动态相结合的万物生成结论。而郭子的“反辅”观则直接从“混沌”和“杂多”出发,省略了以后的阶段,走捷径同样得到了万物相克相生的辩证的理论。但是,可惜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没有看到郭子的学说,就仅仅沿着五行八卦的这一复杂的路子走下来了。试想,如果郭子的书简在当时就传播开来,与五行八卦学说结合在一起,它将成为五行八卦学说的雪橇,载着五行八卦学说快速的行驶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雪地上,这将会给后世的哲学思想发展带来多么大的便利啊。这一现象没有能够出现,这是中国哲学的悲哀,是五行八卦的悲哀,当然,也是郭子和他的“反辅”学说的悲哀。
【087】考张仪出生年考
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期两个最著名的纵横家,二人孰长孰幼和大概出生年,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司马光《资治通鉴》初次提到张仪和苏秦的年份是周显王十六年(前353),但是全书没有对苏秦和张仪二人的出生年或长幼作出过说明,也许司马光不同意历史上司马迁、王充人等苏秦年长于张仪的结论,但是他又缺少证据推翻他们。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对他们的出生年作了推测,即张仪生于周显王九年(前360)前后,苏秦生于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前后。这个结论推翻了司马迁、王充等关于苏秦年长于张仪的说法。
当然,司马迁、王充等人并没有确切判断苏秦和张仪二人的大约出生年,但是,我感觉,即便如此,许多资料仍然不能支持《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的结论。
据《史记》载,苏秦和张仪二人一起从鬼谷子学习,且先后学成出师。虽然苏秦略早于张仪出仕,但是苏秦认为张仪比自己优秀。苏秦学成后,“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而后他去“求说周显王”,希望获得一官半职,但是他没有得到周显王的认可。接着,苏秦来到秦国,这时,“秦孝公卒”。秦孝公之卒是一个关键年份。根据毫无异议的历史记载,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之后,卒于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苏秦学成数年后,秦孝公才死,苏秦学成之年应该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岁上下,由此可以推测,秦孝公卒年,苏秦的年龄已经超过三十岁,甚至三十五岁左右,那么就是说,苏秦生于公元前368年之前,甚至是公元前373年前后。
《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断定张仪生于前360年前后的依据主要是:(1)《孟子》中有称颂张仪为大丈夫的话,说明孟子在世时张仪已经出名,而孟子生于公元前385年左右。(2)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中假定了这时张仪三十岁。而根据《史记》记载,张仪相秦前,已经有很多政治活动。他曾出游楚国,楚相设宴招待了他;之后他还去过东周,昭文君对他很礼遇。这以后,他才来到秦国。而他到秦国之前,已经是秦相的苏秦曾有过“张仪天下贤士”的评论,可见,张仪来到秦国时不仅已经有过许多游历活动,而且已名贯天下,当不止三十岁。再者,如果张仪真的生于公元前360年左右,孟子长其二十五岁左右,而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曾说张仪为当代大丈夫,甚至感慨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功成名就的人生状态。《滕文公下》记录的是孟子第一次游历宋国时邂逅了途经宋国是滕文公时的对话,这是公元前329年的事。这一年孟子五十七岁,而且他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儒学大师。个人成就能够引起年近花甲的儒学大师孟子感慨的张仪不会还只是刚刚而立之人,张仪比孟子本人至多只是略小一些而已,再结合张仪跟苏秦同窗,张仪的出生年都不应该是公元前360年前后,而应该跟苏秦相近,即公元前373年至公元前368年之间,或许甚至年长于苏秦,也就是公元前373年之前。
【088】辞简意丰司马光
邹忌和田忌是齐国的一对著名将相,邹忌为文,田忌为武。邹忌重视法治,严惩奸吏,弘扬正气,他还一方面力劝齐威王纳谏,一方面鼓励群臣进谏。田忌知人善任,放手重用孙膑,以孙膑为自己的军师,多次打败此前号称第一强国的魏国。邹忌和田忌在齐国政坛上的组合堪比战国后期赵国的蔺相如和廉颇,然而,邹忌和田忌的组合却不如蔺相如和廉颇那么完美和有人情味。
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资治通鉴》向来被认为在文笔方面不如《史记》,但是,这一段短短的文字,却质朴而精炼,不仅写出了邹忌和田忌相争的广阔而复杂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和诸侯国内贵族权力纷争的政治背景,更准确的写出了邹忌和田忌的不同性格,即邹忌奸猾有谋,田忌勇猛无计。邹忌买通田忌身边人,施行反间计,又以买通、威逼等方式令卜者告密,终于陷田忌于叛国之罪,邹忌可谓阴险奸诈至极。田忌没有直接向齐侯申诉,如果申诉,齐侯完全可以亲自审理那个所谓问卜者,问卜者本是小人,扛不住齐侯的威严。但是田忌采用了孤注一掷的方式,率领自己的有限亲兵,攻打都城,欲擒杀邹忌,试想,即便田忌抓住了邹忌,又能在齐侯面前洗刷自己的污名吗?田忌虽然刚勇,却真的是过于天真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的美男子形象在《资治通鉴》的这一段文字中荡然无存。
邹忌当初是通过鼓瑟游说了齐威王才做上齐相的,虽然他能够坦坦荡荡治国,但是他对待自己却并不坦坦荡荡,田忌对此应该早已清楚,也应该早作防备才是。而根据《史记》记载,田忌逃亡到楚国,多年后又回到齐国,孙膑一直跟随着他。如此看来,田忌攻打祖国都城临淄的馊主意就是孙膑想的。唉!孙膑的谋略只适用于武功,而不适用于文功啊。
此外,司马光介绍邹忌和田忌争斗的这段文字,还折射出齐威王的性格特点。邹忌陷害田忌是在马陵之战刚刚结束后,马陵之战,田忌彻底打败魏国,齐桓公从魏国那里夺来的霸权在齐威王手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最高统治者历来对军功卓著的臣子怀有疑心,我想,齐威王这个时候是愿意相信邹忌的,聪明的邹忌掐准了火候。
【089】卫鞅不死,新法不行
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孝公既卒,秦惠王捕卫鞅而车裂之。
商鞅变法是秦国走向强盛的根源,这一点自然是秦孝公父子所了然的。那么为什么商鞅会在秦孝公尸骨未寒之际即被新君处死呢?史书对此有明确回答,那就是,商鞅变法触动了旧贵族利益。触动了旧贵族利益,新法仍然能够推行,而商鞅也一直贵为秦相,这是与秦孝公大力抵制旧贵族所不能分开的。那么如此看来,商鞅之死,责任就在于秦惠王不尊先君之故吗?
我认为其实不然。
商鞅变法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的,新法对秦国的好处,秦孝公自然知道。秦孝公知道新法对秦国的巨大作用,他难道不经常向协助自己理政的太子讲清楚吗?何况,作为新生代的秦惠王应该更加有变法图强的魄力。只是,秦孝公执政已久,权力巩固,能够抑制旧贵族从而可以保护得住商鞅的人身安全,而秦惠王刚刚即位,地位不稳,不能过于得罪旧贵族,所以他要杀商鞅以讨好旧贵族。秦惠王的这种处境和由此所要采取的措施,秦孝公作为政治强人,他在晚年当然是明白的,他之所以没有在驾崩前为商鞅安排好安全的未来,其实就是想用商鞅之死换取旧贵族对他儿子的支持。而他在驾崩前已经把新法向社会各个层次作了强力推行,新法已经逐步深入人心,商鞅的作用已经不再非常重要。而商鞅之死只能可以平息旧贵族的不满情绪,却不会动摇新法的基础。秦孝公真是老奸巨猾啊!
商鞅以自己的变法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非凡政治家地位,却又是自己把自己过早地推入了坟墓。商鞅之死是悲壮的,但是如果秦惠王不杀商鞅,旧贵族的纠缠会使新法不能继续顺利推行下去,商鞅以自己的死捍卫了自己的新法。而秦惠王也因为车裂了商鞅而模范的执行了先君的政策。
【090】司马光非圣人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载:周显王三十三年(前336),孟子往见魏惠王,跟魏惠王有过一段关于仁和利的关系的对话,而后,司马光对回顾孟子往事道:“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则生于公元前372年,就是说,子思死后三十年孟子才出生,孟子是不可能做子思的学生并当面向子思求教问题的,司马光显然是搞错了。
现在有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孟子是子思弟子的学生,其实我们如果计算一下孟子的年龄,依然是不能接受的。孟子生于子思死后三十年,孟子完成前期文化储备后才可能拜子思的弟子为师,这时候孟子的年龄不应该小于二十岁。我们无法想象子思死后五十年还有弟子能够有精力收孟子为弟子。
从中唐韩愈把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作为儒家两大思想主流砥柱之后,儒家学说逐渐被简单化为“孔孟之道”。为了使孟子的话有权威性,司马光可能就有意无意的把孟子作为子思的弟子向宋神宗介绍了。其实,我们仔细分析孔子和孟子,二人的学说还是有巨大区别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孔子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以周王为核心的天下大一统,而孟子学说的目的是让某个诸侯早日称霸,取代周王,完成天下大一统。二人的学说虽然都是儒学,但是出发点却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不亚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二者的可比性并不很高。
当然,历史学家司马光也许真的就没搞清楚孟子和子思的生卒年。司马光是孔孟学说在宋代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之一,但是,孔孟是孔孟,司马君实却不是圣人啊。
【091】春秋战国重分野
西周和东周的历史分期是以正统的周天子所在京畿地区的方位为标准的,也就是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界线历史上一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分法:一是以孔子的史书《春秋》记事结束后不久的公元前475年为战国时期的开始;二是却以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大权臣瓜分执政智伯的土地为战国时期的开始;三是以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取代晋侯成为三个独立国家为战国时期的开始。第一种分法被大多数人认可,但是仅仅参照孔子未完成的史书来确定春秋战国的分野,带有“追星”的意味,显得草率。后两种分法以韩赵魏三国取代晋国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为春秋战国时期分野的标志,看起来有道理,晋国只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国家,当时国家好多,国家之间的分分合合早就发生了,韩、赵、魏的诞生不能成为周朝政治生态发生质变的标志。
就是说,春秋战国需要确定一个新的分界线。我认为这个分界线应该是公元前334年魏国和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州南)之盟。
根据历史传统认知,西周和东周的分期原则是周王的地位变化,即周王由西周时期的众星捧月到东周时期的大权旁落;而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期原则是周王地位的继续变化,即周天子从作为大国小心挟持的称霸工具到这种工具意义的消失,所谓工具意义的消失,就是各大国不再需要周王作为吞并别国的遮羞布,各大国开始直接以王自居,周则成为一个小的诸侯国了。由这个思维出发,春秋战国的分界线就不应该是分智伯或分晋,因为韩赵魏三国国君并没有统一天下的观念,争取得到周王的身份认可才是三国的早期战略,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前403年之前,韩赵魏三国相较于齐楚等国更加尊重周王。因此,韩赵魏三分晋国之后,它们都还在延续着春秋时代各国的称霸和反称霸战略,三国分晋并没有改变春秋时代的政治态势。
然而,韩赵魏三家作弄晋国前,南方的吴、越两国已经崛起,南方后来先出现吴越争霸,又出现越楚争锋,且都试图问鼎中原的状况。而在北方,三分智伯时强大的魏国已经衰落,秦国的国力处于继续发展中,但还不够强大。而南方的国君早就都以“蛮人”自居,蔑视周王的权威,吴越两国仿效楚国,国君都称王,把自己摆在跟周王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但是北方诸国还是以周天子为王,各国诸侯都还是称公或侯,最起码在周朝的核心统治区中原地区,周王作为共主在名义上还是存在的。
在吴越楚三国相互争霸的同时,三国对北方诸国也一直保持着进攻态势。楚国不用说了,公元前660年楚庄王就有“问鼎中原”的典故了,此后三百年间,楚国逐渐吞并了北方诸小国,国土大大越过淮河,直接跟齐鲁二国接壤。吴国打败越国后也积极北上,先后吞并今江苏、安徽、山东境内的淮夷、钟离、巢、徐夷、钟吾等小国。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后就开始进攻齐鲁大地,公元前414年、前413年、前404年,越国直接吞并了今山东境内的郯国、滕国、缯国,并攻占了齐国的大片国土。
南方称王的楚吴越三国的进攻,北方诸国疲于应付,周王的作用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了。于是,效仿南方诸国称王,并加强北方诸国的联合,逐渐成为北方诸国国君的共识。于是,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南)会盟,二人效仿吴越楚三国称王,并互相承认对方。
北方大国魏和齐迎合南方诸国称王,标志着周天子作为北方诸侯国争霸的遮羞布直接被撕下来了,周作为一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此后的历史怎么演化,都是诸侯们的事,周天子算是可以洗洗睡了(如果能睡到寿终正寝也就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北方诸侯称王,跟周王成为地位平等的天子,这对于周朝来说,指标意义是远远大于韩赵魏分智伯和分晋的,所以我认为战国时期应该从公元前334年魏齐国君弃北效南的时候算起。
【092】时代造就变法派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楚怀王作为纵长,率楚、燕、韩、赵、魏五国军队伐秦,不料战败了。楚怀王在此次战败后深切感到楚国的大而不强,他决心振兴楚国,于是他责成左徒屈原在楚国实行变法。
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变法与战争是社会的两大主题。变法因应战争的需要,战争又进一步加深变法的迫切性和变法的力度。变法虽然可以在总体上增加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但是变法总还是要有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就总会损害旧贵族的既有利益。因此变法总是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推动,斗争的结果,一般是变法派的主要人物被打倒甚至被处死,而新法却得以先部分推行,后全部推行,甚至会继续深入下去。秦国的变法派商鞅被杀了,楚国的变法派吴起被杀了,但是他们的新法却被推行下来,社会就这样通过变法派的前赴后继,在一次次变法中走向未来,而这个未来就是越来越成熟的封建制度。
屈原在楚国的变法其实是早先吴起变法的加强版,就是进一步废除奴隶制,进一步削弱旧贵族势力,推行越来越完善的封建制度,实行更加开明和相对公平合理的法制,以提振被统治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和参军积极性,提振军队战斗力。
由于变法再次触动了旧贵族甚至楚王自己的利益,如同以往的变法一样,旧贵族疯狂抵制新法,不久,楚怀王扛不住了,屈原遭到流放。屈原被流放了,但他的新法如同吴起、商鞅辈一样,被部分推行开来。
其实,屈原生活在一个极端守旧的旧贵族家庭。屈原的祖父屈宜臼是个死硬的旧贵族,吴起就是在以他为首的反对派打压下被杀的。但是,争霸和打胜仗的需要迫使各国必须变法,于是,守旧派中的进步人士便逐渐加入变法派阵营,这是新事物以渐进式方式取代旧事物的必然结果,屈原的祖辈和父辈都是旧贵族,屈原早先也是反对变法的,他就是这样在时代要求国家图强的洪流中成长为变法派人物的。
【093】卫侯称君宋侯称王
周慎靓王七年(前314),“卫更贬号曰君”,两年后,“宋初称王”。
这两件事发生在战国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相持角力,在东周的华夏大地,数十个小诸侯国逐渐被并入十几个大国中,而秦国一家独大且与其他大国继续拉开国力距离的态势已经形成,各国对秦国基本上采取守势,合纵连横的战略格局也已经定型。如同下象棋已经度过中盘一样,更大规模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诸侯兼并战争正在拉开帷幕。秦国继于公元前330-前328年攻取魏国河西、上郡两地之后,正积极筹备发动灭亡巴、蜀二国的战争,以便对东方诸国实施战略包围。
在周的宗法制系统中,王的称号是周王独用的,侯低于王,君低于侯。楚国诸侯早在春秋时期就首先自称王,公然蔑视周王和周礼。战国前期,主要大国的侯相继称王。在周慎靓王时期的大国决战前夜,卫、宋两国的侯一家自贬称号,一家高调称王,显然,卫国的策略是正确的,宋则是错误的。
虽然宋的国力稍强于卫,但是卫、宋两国都还是小国,而且卫处于韩、赵、魏三大国之间,宋处于齐、楚、魏三大国之间,两国的战略回旋空间都非常小。在这样的形势下,卫、宋两国更应该以谦卑的姿态采取守势,才可以使自己的社稷能够存在的更长久一些。小国如果高调,显然就是不识时务,必然会给大国灭亡自己带来理由。
果然,宋称王不久,公元前286年,齐国出兵灭了宋国,宋国的侯称王只称了一代,算是过了一把称王瘾了。而卫国虽然先后被魏、秦两国所并,但是卫君的称号却一直保留着,直至秦始皇死后,秦二世才把卫君废为庶人。卫的国祚比宋国长了七十多年,卫成为最后一个被秦灭亡的国家。
由此我想到了与老子有关的一个典故。有人问老子,为什么人老了牙齿会掉而舌头不会,老子回答道,那是因为牙齿看起来坚硬而舌头看起来柔软的缘故。宋、卫二国似乎也符合老子所说的这个道理啊!
【作者简介】
董元奔,1971年生,传统文化学者,高等教育工作者,网络知名作家。
世纪初在教育主管机关做文字工作,后辞职创办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机构,又在某高校创办全日制特色系部,皆专事汉语言文学专业。十余年间有四千余名来自全省的学员获得本科学历。培训事迹被《中国教育报》、《中国考试》杂志、《新华日报》等多次作长篇报道,个人被教育厅《江苏自学考试》杂志两次作封面人物介绍,事迹还以专有名词形式载入《江苏教育年鉴》。
办学期间一直居教学一线,并笔耕不辍,2016年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者。主要写作文史论文、文化随笔、诗词等,已在各类媒体发表作品200余万字。世纪初有教育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并入选《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近年来有近六十篇文史哲论文获今日头条青云计划奖,获颁“青云获奖者”金质纪念章,并应邀成为头条参赛文章评审团成员。
编辑:董尧、霜婵、丰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