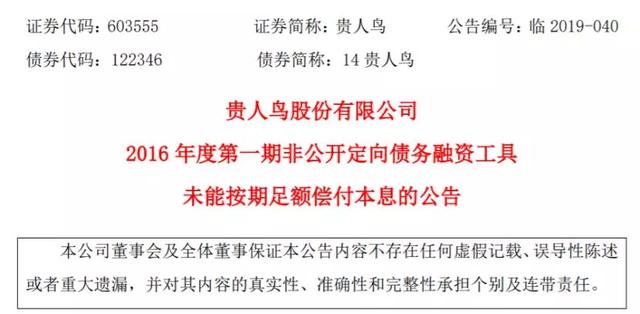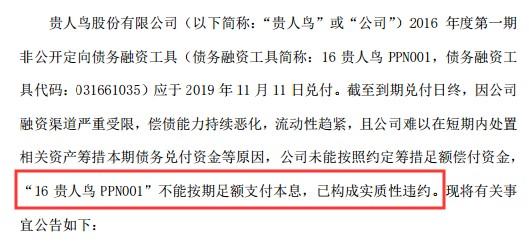王鸥一直在哭。
她听到导演喊了卡,泪水却始终止不住。几分钟前,她饰演的苏瞬卿被李光洁饰演的将军息衍表白,后者劝她放弃孤身坚守,回归自由。他还给她在山下湖边买了一栋房子:推开窗子,便是一望无际的湖水。
非科班的体验派女演员被说动了:“他跟你说我的牢笼是你,你不疯了吗?”但剧中的苏瞬卿不能被说动,这个悲剧人物最后要在执拗的坚守中死去。
于是,王鸥只能克制自己的情绪,猛抽着纸巾擦泪,冷静下来再拍一条。
孤绝的女杀手把王鸥再度带进观众的视野。她似乎天然适合这样的角色,美丽、独立、带着些决绝和悲伤色彩。真实的她也与这类角色有着某种共性,比如没有大把的朋友、不预备妥协将就的退路。
很多次接受采访,被问及至今最感谢的人,王鸥都说是“自己”。这次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她给出了一样的答案。在离异家庭中长大,她早已习惯自己做人生的大小决定。偶尔有无法释怀的事与朋友分享,她的内心也早就有了主意。
“当别人跟你有同样意见的时候,你觉得没劲;听到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我说好的,我知道了,然后我坚持我行我素。”她笑着调侃,说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后悔。
“做过错的选择么?”
“没有。”
她的笃定有些出人意料:“活着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不要天天给自己那么多负能量。你要相信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对的。”
美艳与疏离
保姆车空间不大,不到半平米的桌子两侧挤了四个人。
身形瘦削、坐在里侧吃饭的王鸥并不显眼,可当她抬起头打招呼时,你的注意力会被瞬间吸走——就像网友评价的那样,她的美直观有侵略性,很难让人忽视。

这种有侵略性的美一度是王鸥的优势。电视剧里的情报处处长、谋士、杀手,她演起来很出风头。综艺《明星大侦探》中,她从民国歌星演到足球宝贝,高冷女神的设定都能有效完成。
这些或狠辣、或冷漠、或温柔的王鸥,无不散发着一种生人莫近的疏离感。
眼前,忙着把最后一块臭鳜鱼放在嘴里的王鸥也的确不够疏离,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能让人忘了她是个从小说方言的广西人。
“演了这么多年戏,也不能再有口音了吧。”她音色低沉,语速偏快,回答大都直截了当。
侵略性的美也被她否定。王鸥说她不是从小被夸到大的,她长于南方城市,小时候又黑又瘦,母亲会对她说“你真丑,不像我生的”。在这种打压声中长大,她很难对自己的长相满意。
如今回忆儿时受到的夸奖,王鸥只想起了说过她条件好的舞蹈老师。当时她心中美的标杆是两个高年级的师姐,印象中,全校挂的都是两人特别美的照片。她觉得自己和两个师姐比,条件只算“还行吧”。
因此,从没觉得自己特别美的王鸥被观众夸“明艳动人”时,惊讶盖过了惊喜。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换了个口红就被觉得明艳动人了”,久思无果后,她把这归因于角色的赋予。同理,在她的理论体系中,这不属于她本人。
可就当以为她要推翻外界印象、树立热情开朗的形象时,她却一口认领了那股疏离感。
“天蝎座,就可能比较会有距离感。你知道吗,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很重,怕被伤害,完全自己给自己隔离起来的一个堡垒,别人进不来。”这是采访中王鸥用的唯一一处比喻,她边说边用双手圈出堡垒的形状,范围很小,几乎贴着身体。

渴求与放弃
儿时的王鸥没有堡垒。
在女儿最需要爱与陪伴的时段里,王鸥的父母选择各自为生计奔忙。于是,常年被寄放在各种亲戚、邻居家的王鸥早早学会了独立,代价是周围人日益减少的关注和担心。
父母和他人的认可一度是她疯狂渴求的生存证明。她变得胆小,生怕做错什么事。同学喊她溜旱冰,为了让人家以后还带自己玩儿,她满口答应,可到了溜冰场,她看同学遛个两圈就赶快打招呼走人——因为害怕和男同学一起玩,是让妈妈生气的禁忌条例之一。
可夸赞还是没有如期而至。期盼、等待、失望的无限循环中,夹杂着小女孩百思不得其解后,对父母的小怨念:既然生了我,为什么不好好教育我、陪伴我呢?童年的种种缺失,就像她之前喜欢一个玩具,怎么叫妈妈都不给买。
以王鸥的思路,这种无效傻事试一次就够了,“你就觉得,好吧,我还能做什么呢?我不能,那只有自己慢慢去适应。”
在无力感中浸泡得久了,王鸥尝试着挖掘自己的喜好。那是琼瑶剧大火的年代,《婉君》之类的梦幻爱情故事她最爱看。她发现自己想做个演员,因为“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的人生,是很精彩的职业”。只可惜,当时广西没有她想去的演艺类院校,她又说不好普通话,怎么看都离得太远。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她决定“曲线救国”:先学跳舞,再找机会学表演。她发了狠,上课、练功……多年来在心中积攒的“内劲儿”在艺校有了用武之地。
只是,父母的认可依旧求而不得。同宿舍的同学总是周五被妈妈接走,周日送回来,王鸥则自己坐公交车来去。偶尔的简短电话里,妈妈从没问过一句她跳得苦不苦。但那时的王鸥已经不再依附于此,父母的夸赞,于她只是意难平罢了,“没有家里的温暖就算了,我就自己生活呗,反正我在学校也挺开心的。”
幸运的是,远方的广西女孩终于拿到了属于演艺圈的首个“剧本”。在姐姐的鼓动下,身高170cm的王鸥报名了女性魅力大赛(一场模特选拔比赛),拿了冠军。之后的几年,她从走50元一场的模特秀起步,到2003年拿CCTV模特大赛的最佳上镜奖,越走越远。
“我不骗你,我那时候在南宁真的很红,我上街他们都认识我,我的广告满大街都是。”她正色道。
虽然王鸥的语气是骄傲的,但在2004年,好成绩给她带来的还有焦虑。她觉得自己在模特这一行已经到头了,身高也不会再长,注定成不了国际超模,还是“别闹了”。
她又想起“曲线救国”的事儿,发现心中疯狂渴求的东西早就被换掉了。这些年的经历让她摸清了父母对自己的心态:我们不知道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办法帮你成为更好的人,只能靠你自己,你自己看着办。
命握在自己手里,王鸥没什么好犹豫的,她还是要为自己的演员梦搏一把。

释然与崩溃
“广告才能拍几十年?演员才是终生的职业。”
坐在小方桌对面,王鸥理智地谈及在没有戏约时,一位模特经纪人想把她留在日本稳定发展,“这离我的梦想又远了,我怎么又回去了?”
那时她已身处北京,像大部分北漂青年一样,她的生活是艰苦和希望糅成的。靠广告、走秀养活自己的间隙,她会去剧组试镜。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卸掉了她所有的成绩和担子。
对目标近乎偏执的坚持没换来她想要的演戏机会。被问及那段生活,她挺直脊背,抛出一连串否定句:不会彷徨、丝毫没有犹豫、从不怀疑自己可能做不好演员。
那是一段低谷期。曾经风光的模特履历毫无意义,王鸥没有表演经验,经常在筛简历环节一轮游。有时绷不住了,她会在洗澡时小哭一下,只是,这种刹那性的失落都会在睡梦中格式化。
尽管嘴上说自己早就断了指望父母的念想,王鸥心中还是会记挂很多“别人家父母”的说辞,只是“没有人告诉我不要去碰这个壁了,都是‘你去吧’”,她有些动情,“路是我自己选的,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就算选)捡垃圾,你跪着也得把它捡完。”
哭没有用,这是王鸥儿时就明白的道理。为了坚持下去,她学着走向示弱的反面,渐渐自我包裹。
家庭负担是对北漂女孩的二重施压。在外多年,儿时的小怨念王鸥早已释然:“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也要享受新浪潮。可能他们做的并不合格,但他们有享受人生的权利。”
她意识到了在乎是因为爱,把第一部戏的片酬全都拿来给重病的父亲做手术。可就在为父母的养老计划奔命时,家里却传来了父亲过世的消息。
王鸥崩溃了,不只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做不出任何反应。“巨冷”的殡仪馆里,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却一滴泪都流不出。面对亲友,她只字不提北京的日子,人们不知道她过得是轻松还是辛苦,也找不到安慰的切口,只能说些注意身体类的过场话。
她睡不了觉,一闭眼就是父亲的脸。在刚刚搭建好的堡垒中,她大哭了一场,恨子欲养而亲不待。第二天,她顶着一张哭肿的脸回横店拍戏。
王鸥不知道可以请假,也不敢请假。得到演戏的机会不容易,作为女主角不放鸽子是职业操守。“父亲已经走了,我留下也没有意义,必须清醒过来。”她动作飞快地抹掉眼角的一点泪。
“所以有时候说演父亲死了的戏,你要号啕大哭什么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有人说)你爸死了你都不哭,你不是好演员你知道吗?特别搞笑。”
限制与争议
能接到稳定的戏约,是入行两年后的事了。王鸥的“侵略性美貌”开始发挥作用,在很多只在地方台播放的电视剧里,她都演最风光的女主角。
可她为此沮丧,觉得同行都在飞,只有自己在走。“我有时说,你让我演演女二吧。能不能女一是那种大明星,腕特别大,然后我去给她演配角。我接受啊,我可以啊,那时最火的赵宝刚导演,我可以去他剧组演女三号、女八号。但是他们就不会找我。”
直到现在,剧组里的“老戏骨”还是能让她兴奋很久。年初上线的《芝麻胡同》,她搭档何冰、刘蓓,跟着他们学北京话,“一部戏下来,像上了一学期表演课”;《九州缥缈录》里,她和张嘉译只有几场对手戏,但在片场一见面依然会拿着一堆问题去问。
只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她后来的表现还是很少能超过《琅琊榜》和《伪装者》。脱离两个永远无法回避的代表角色秦般若、汪曼春,带有女特务、女杀手等角色的人设加持后,她的演技不够亮眼,甚至被指责过“拖后腿”。
《九州缥缈录》的女杀手苏瞬卿很受好评,有人评价“王鸥让苏尚宫执念的‘魅’有了鲜活的脸”。
为什么独演这类配角出彩?她回了一句没研究过。尝试当场探讨,她唯一主动提供的线索是配角比主角更精彩:“主角往往人设趋于完美,这人一完美就少了很多意外,会显得有些无趣,配角则是有无限可能性的。”
观众的答案更集中,主要是她的“气质优势得以发挥”。

王鸥知晓这些观点,但她不愿意自己被定标签。“你抹上大红唇观众就好带劲,觉得我想看你这样,想看你时刻散发魅力。但是我没有遇到这样的角色就(说我)受限了,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了。”
“对抗过么?”
“对抗过,主要是对抗自己,和自己较劲。”她回想起住在堡垒里的自己:不送礼物、没有笑脸、不“哈”着别人、不懂人情世故……依旧是一连串的否定句,语气却软了很多。她认为,那是她身上疏离感的来源,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尊严,和怕说多错多伤害别人。
就像释然了对父母认可的执着,如今王鸥对观众的评价也没有太强烈的期待了。“就像演牧春花,很多人对这个角色的年代有很多不认同,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错。”
她把新一轮的释然契机归结于年龄。“现在成熟了,明白打个招呼也不是哈谁,热情一点有什么错呢?”具体的分隔线是《伪装者》大火后,她被记者一遍一遍地问红了之后的改变的时候。
她认定这根本不叫红,“还有很多观众没认识你呢。”结合这些年来的大起大落,她认定自己已经看透了。至于事业外的争议,她也无所谓了,“自媒体上,别的女演员(被写的)比我还夸张,我有什么好激动的呢?”
工作人员走进保姆车叫停,王鸥该去拍戏了。她站起身,穿上白衬衫、工装裤和靴子,变身美艳冷酷的女警察。
此时的王鸥并不是驱散了身上那股疏离感,只是在和人打交道时有意识地收敛。
“我妈现在还是不看我的戏。”她边向外走边聊起来,“她天天复制我经纪人(宣传剧集)的朋友圈,什么今天苏瞬卿上线了,明天苏瞬卿下线了。她朋友是我粉丝,都说你女儿演得好好啊,你女儿好美啊什么的。她说是是是。她根本就不懂。”
那是一种打趣的语气,仿佛聊的是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