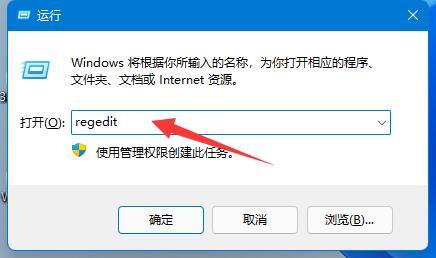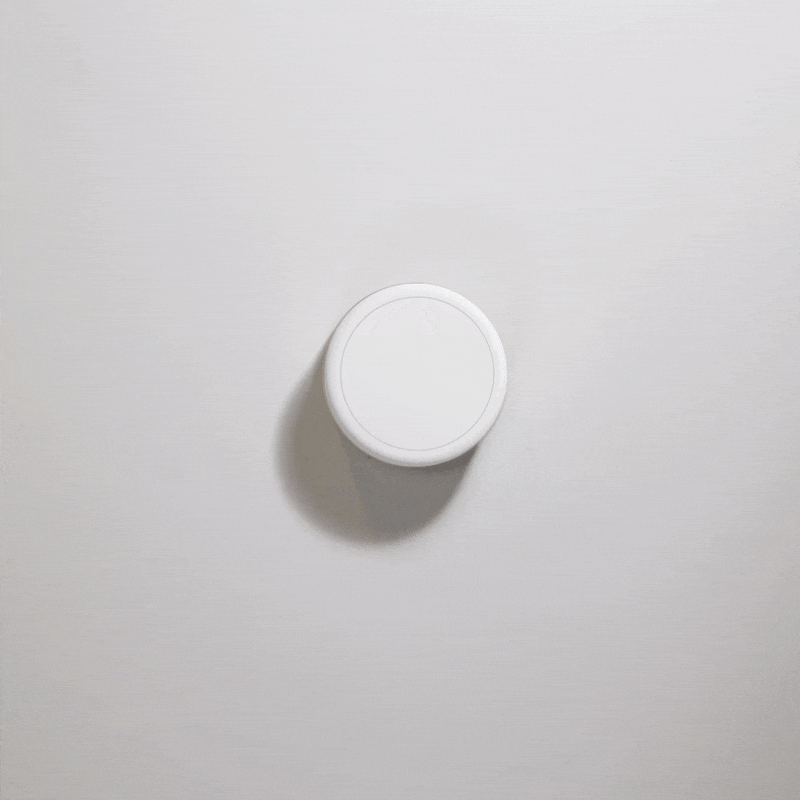作者|刘千荣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我上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冬天,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教我们语文的罗厚平老师,为了扩大我们的课外阅读面,利用中午自习时间每天为我们抄一首古诗词,并像上语文课一样进行解读,现在看来是加量不加价的免费加班。猜测罗老师当时既是“奇文共欣赏”,更是想让我们多学知识,加深文学素养。第一次抄录的就是《诗经》中《采薇》里的这四句名诗,记得教室外面正是雨雪霏霏。罗老师抄完了,给我们逐句讲解,引领我们体味诗句深刻的意境,因为字面的意思不难理解,主要是分析诗歌的情景交融,寓情于景。
那时,风华正茂的罗老师比我们班里绝大多数的同学,只大个五六岁的样子。日久天长和我们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而他放弃午休时间,辛苦给我们加课,为我们的古典诗词功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为我们抄录、讲解的每一首诗至今我都仍有记忆,诸如岑嘉州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白香山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等千古佳句我现在依然能够脱口吟诵。直接影响了我和一部分同学此后的人生选择。
初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末,一个雨雪霏霏的下午。父亲骑车来到学校,喝酒就脸红的父亲,让人一眼看出他喝酒了。有几分酒意的父亲把我喊出教室说是要给我转学。平时也听父母和在县城里读高中的姐姐商讨过。眼见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从常规上来说转学其实对备考不利,但是因为当时的初中升学考试,是复读生们的天下,如我这样的应届新生基本不抱希望。所以转学目的是为明年的复读创造条件,因为我即将转去的镇中学,比我所就读的乡中师资力量要雄厚的多。
父亲领着我先去找校长。校长不置可否让去问罗老师,说是罗老师教了我近三年彼此有感情。在我的引领下,找到了已经荣升为班主任的罗老师。罗老师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父子俩,知晓我父亲的来意后,立即给开了转学证。罗老师非常真诚地说只要对刘千荣的学习和前途有利他都会全力支持。
在那个雨雪霏霏的下午,我离开了学习和生活整整两年半的乡中,也离开了教我两年半语文课的罗老师以及朝夕相处的同学。那一别,我今生就没能再听到罗老师的课。转学后的我有幸考上高中,罗老师则在我本该读高二的那一年,辞去当了一年的教导主任,考入省教育学院进修去了。
罗老师学成归来,被分配到了我曾就读的高中,只是我已经因病辍学两年。和我同届的同学已经高中毕业,而我的学历则被定格在高一未读完。不再读书的我闻讯后,特地去学校看望老师,那次见面也是在冬天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
罗老师为我的前途担忧,认为我不读书可惜了。他建议我把书读下去,把落下的功课捡起来,至于我担心的学籍问题他来想办法。然而,无论我个人精力,还是我家里财力都不容我重返校园读书。罗老师那番劝勉之言,也曾在我内心泛起涟漪,冷静下来细想却不现实。次年正月,我追随兴起的打工潮,辗转于各个城市,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涯。离乡背井二十余载我很少回老家,当然也没能和罗老师见上一面。只隐隐听说他被调往老家一所职业高中任校长,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职高打理得风生水起,其个人也因此获得国家奖项。

五年前的冬天,又是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冥冥之中,上天要安排我和罗老师见上最后一面。我与一位朋友在饭馆吃午饭。随手翻阅手机,见在老家当医生的老班长QQ在线,随口问了一句“吃了吗?”这么一聊我才知道罗老师正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我心里就一沉。看来罗老师病得不轻,否则不会大老远跑上海来看病,即便身为校长的他不差钱,如果不是得了重病,估计也不会这么大老远的折腾。
迎着寒风,冒着霏霏雨雪,我转转到了瑞金医院。当我站在罗老师的病床前,我还是惊讶的半天无言,因为病床上的罗老师骨瘦如柴,让我想起父亲临终前被病魔折磨的样子。还是罗老师先喊出我的名字,我才回过神来马上进行自我否定,不一样的,罗老师比父亲年纪要轻很多。没有可比性,我这样自我安慰。
二十余年未见面的师生说不完的“别来沧海事”病重的罗老师依然在鼓励我说:“听祥荣(我的堂弟兼同学)说你在上海闯出了名堂……”怎奈老师身体太弱,怕影响他休息,我极不情愿地告辞……次年农历二月初六,从老家传来罗老师辞世的噩耗。医院一别,就此成了诀别。
在没和罗老师见最后一面之前,我曾经想着把自己在报刊发表的文章扫描后,刻成的光盘,和自己接受东方卫视专访的视频给老师寄上一份,但光盘放在那里就是没寄,总觉得时间有的是。老师离世了,我不知道该寄往何方?“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从此有问无答。
秋去冬来,冷空气一波接着一波。伴随着寒风呼啸,又见雨雪霏霏,我总会回忆起与罗老师的那份弥足珍贵的师生缘,感恩他在我人生最困难时刻给我的无私鼓励,不求回报的帮助。每当此时,心头便会升起阵阵暖意,冲散冬天暂时的严寒,激励着我走向人生下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