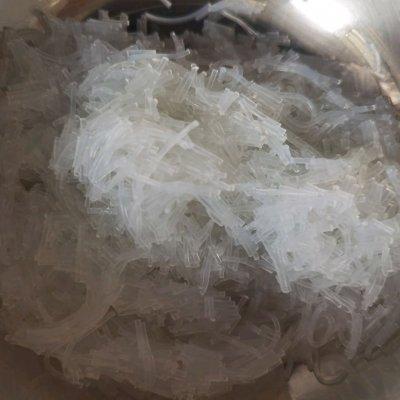娃他姨妈
作者:袁炳纲
农村人说农村话:管妻子不叫爱人,叫娃他妈,自然管妻子的姐姐叫娃他姨妈。
第一次见娃他姨妈是在一九七二年农历七月初九。之所以能记得这么清晰的原因,是我们建陵乡坡北村农历七月初七有七仙女七姑娘的古庙会。那时的古庙会热闹得比如今的工程剪彩、企业开张还要厉害。
方圆几百里的人都要来参加:买卖猪娃,倒换牛羊,交易骡马,购置灶具,添衣扯布,床板棺板,筛子簸箕,木梳篾子……总之,古庙会满足所有农民的所有需求。
前来逛会的人很多很多,摩肩接踵。有我们礼泉县的,还有邻县淳化泾阳兴平乾县永寿的,甚至还有甘肃兰州的人。

不知从何时兴起的习俗,凡是村里订了娃娃亲的家庭,都要在七月七古庙会上,把几乎从未谋面的未婚妻叫到家里来,让她逛会,买点衣物布料,置办点嫁妆什么的。还有男女双方互相见面,相互熟悉了解,增进感情的缘由。
那年,我虚岁十七,刚高中毕业,自然回村随俗,把妻子叫来逛会了。
四天时间,七场秦腔大戏,成千上万的农人,人人乐悠悠美滋滋的,象抽了一口味道极强极醇的老旱烟。
初九午后,戏台拆了,村里临时搭的店铺也被刚兴起的皮轱辘马车转运走了,街道上人们开始打扫西瓜皮,收拾猪羊牛马粪便,该送未婚妻回娘家了。
带上简单的礼物,我推着自行车,一会儿,下了东陈村那个长坡,又下了一个陡胡同,来到了岳丈家,一户门口是沟,家里全是窑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见到了娃她姨妈。
“姐。”我妻叫了一声。“你回来了。”娃他姨妈答道。这个你不是三声,是一声,只有关中人才能明白听懂这个你,这个你包括我和我那个她。
撑好自行车,借从车子上往下取礼物的当儿,我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姐姐来:粉色短袖,蓝色裤子,一双买下的塑料底自己缝制的黑色灯芯绒板鞋,又长又黑的两条辫子一前一后。
那衣服那么合体,颜色搭配又俗雅得当,恰到好处,鞋绱得端端正正,方口上面显露着脚的薄巧和平直以及手工的精美。
特别是她那脸色和眼睛,白里泛红,红里又显白,象一朵刚绽放的莲花。带着湿漉漉的水色,又彰显着纯洁娇美的原生态,不做作,不妖艳,既朴实又靓美。
再看那黑得发亮的大眼睛,在那深而美的双眼皮下,一闪一闪地灵动而传神。
关键是她的气质:既有村姑的淳朴,又有文化人那种深隐的神韵。
我一下子惊呆了,不由得咽了一口涎水。我实在想不到,这么小的山村有这么美的女人,这么让人心旌摇曳、魂难守舍的娃她姨妈。
很快,我从她的表象里读出了她的内涵:一个有文化,心灵手巧,沉着稳重,各方面都很成熟的女人。
也许是娃她姨妈那年刚结婚,刻意打扮了一点,但人的气质不是通过打扮而具备的。气质是一种上天的赐予,是一种一生下来便附着在身上的宝物,装不出来,夺不失去。
说起来有趣,当我反复打量她姨妈几次,心里推测猜算她的一切时,我俩几次目光相遇,终于在又一次相遇时彼此噗哧一声笑了。好在我们都没有失态,分寸拿捏得还算有度。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观察自己的妻子也没有观察她姐这样细致。我甚至后悔爷爷为什么当时没有给我相中姐姐呢。
娃她姨妈非常麻利,很快地给我炒了盘菜,用油炸了馍。待岳父岳母知道我来返回家时,我已经吃完了饭,并端上了娃她姨妈沏来的,放了茶叶又放了白糖的茶糖水。
一切那么有秩序有条理,一切那么自然合谐又恰到好处,娃她姨妈把这一切都操持得既不失体面礼仪又深含温馨情意。
以至于后来我常常想起这次简短的会面。也就是通过这次会面,使我认识了娃她姨妈,一个能说能干甚至能写能画的能行人。
果不其然,一九七七年,我们结婚后,我才真切见识了娃她姨妈这个女人的能干、强悍和精明。
妻子给我说,她家里姊妹多,粮食困难,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在每个儿女的婚事上,父母好象只是走过场,完成便了事。原来本打算把她许配叶家姓刘的人家,可她姐坚决不同意,说:“把我一个嫁到交通不便的高树村了,还要再搭一个妹妹到交通更不方便的叶家去,你们傻了吗!”

我们建陵乡地形特殊,只有中间一条路通南贯北,西边叫西片,一条大梁下去六村,三面环沟;西北方向的西北,米家,南豆芦冯马也一边靠山,一边临沟。到了东北片,地形就更特殊了,宛如一只手伸出四个指头,四条土梁四个村,每村都是三面环沟。
娃他姨妈的婆家,就在叶家那条梁的北边,如果我妻再嫁到叶家,还要下到她婆家这条梁的最南边,也是梁的尽头。娃她姨妈嚎叫,阻拦,终于挡住了我妻她第一次的婚约,从而嫁给了我,嫁给了交通比较方便的坡北村。
我们坡北村,在建陵镇的南北中轴线上,门口便是县级公路,南通县城,北连和建陵接壤的东庄、叱干、相虎、南坊等乡镇。那时,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是一种资本抑或资产,可以轻而易举成就一段婚姻。
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娃他姨妈,那时年纪轻轻的便有这么远的目光和洞察能力,这在当时,一般的农村女孩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何况她当时年龄并不大,只有十五六岁。
我的连襟,也就是现在的娃他姨伯,其实是我的学长,文化革命结束后,我上了初中高中,他去泔河打坝,给民工帮灶做饭,后来被一个好心的领导举荐到西安秦川机械厂,当了消防队员。
工厂消防队,虽说火警不多,但人是不能离开的,他的老家在高树村,一头沉,整个家都得娃他姨妈操持打理。
俗话说:娃娃干活淘死气,婆娘持家驴耕地。
但娃她姨妈不同,担水磨面,烧锅擀面,拉土垫圈,加上还要抚养两个儿子,屋里的,地里的,外头的各种活,她都干得热火朝天,风生水起,真是上炕剪子下炕镰。
家里虽说简陋,但妥妥贴贴,井井有序。那时,谁不夸她,又有几个男的能有她这种超凡的能力呢!
建陵乡所在地在东店头村,农历三、七、十逢集,每次赶集,由于顺路,娃她姨妈都要到我家来,而每次来去,她都急匆匆的。忘不了的是她额头上沁出的细密的汗水。
赶一次集,来回十几里,非上即下,还要考虑下午参加队里的劳动,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的孩子。
为了节省时间,她有时借到北岭顶劳动的机会,让别人把劳动工具捎回去,自己直接从地里去赶集。这样可以减少三四里路程。
娃她姨妈尽管只读了二年书,但识字不少,现在会读简单的文章,还会玩微信,会扫码用微信收付款。
这在于她会淘。她会根据前后认识的字猜测出中间不认识的字。这不是什么神奇,这是她的用心。
其实这个世界上,只要你用了心,就会化无知为有知,变文盲为有文化,甚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苍天有眼,在娃他姨妈的不懈努力,奋勇拼搏下,三五年时间,便给自己奋斗了一院新宅,并盖了三间瓦房,一间小灶房。
尽管椽细檩小,墙是土坯砌成的,但那小小的玻璃窗在当时还是十分让人羡慕嫉妒的。那时,一个村没有几家住房的。
她姨妈的高树村,许多人有大骨节病,走路一瘸一拐的。当地人说得此病有二因:一是水不行,常年四季吃的是雨水(把天上下的雨水积蓄到窖里),二是住的是土窑,阴冷潮湿。所以她刚过门便有盖房的打算。
水改变不了,住窑非改变不可。尽管盖房拉了一些债务,但居住条件改变了,她相信她的儿女不会再得大骨节病了。
这一举动,在这壤穷乡僻的山村,在当时,可能还算得上一壮举吧!
七十年代末期,我有了一双儿女,他姨妈一对小子,比我家的大六七岁。在那个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糖买酒要供应票,买自行缝纫机要分配票的年代,儿子不好养啊!
记得我女儿那时喝羊奶,有时给奶里连白糖也没有,没票更没钱呀。但孩子要穿衣、要穿鞋咋办:自己纺线织布!
娃她姨妈几乎每年都和我妻合在一起织布。四个娃穿的戴的,全凭娃她姨妈裁剪。因为她心灵手巧,不用鞋样衣服样便可以裁剪,并裁剪得大小合适,款式时兴。
那时,上门寻她裁剪衣服的人经常接二连三,络绎不绝。街道上摆摊裁剪的收费,虽说不贵,但有钱的有几家呢!我家连大人穿的衣服几乎还是娃他姨妈裁剪的。
她有时不光是剪裁,还得缝做。我结婚时因手头拮据,没有穿上绸子褂褂,后来手头稍微宽泛了点,妻子执意要给我弄件穿穿,她姊妹俩忙了两天才做成。可惜我没有穿几天,至今还放在柜里。
八十年代初,农村土地到户,责任到人,多年来粮食不充裕甚至不够吃,农民怕了,大家都想多种点麦子,多攒点粮食。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大地,喜气洋洋。刚缓过气来的农民无不全身心投入精耕细作,多施肥料,多打粮食的奋斗中。
可娃他姨妈观念不同:她率先发展果业,在自家的地里一下子栽培了四亩苹果树。

这在当时,没有眼力的人是看不出苹果产业的前景的。没有魄力的人也是不会一下子栽那么大面积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还禁锢在传统农业的模式里,脚步还停留在以粮为纲的老路上。
我当时也算放得开的人,但栽种面积还不大,思想有点保守。不过后来后悔了。
八十年代后期,农村城里所有的人,生活几乎全部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吃饱的问题,而是吃好的问题了。正象我村上说话比较幽默大平所说的:“前几年解决的是米袋子,现在要解决菜篮子,果盘子。
”农民工人手里有钱了,苹果价忽忽往上涨,有时甚至涨到三五块。这时,人们开始又一次眼红娃他姨妈了。因为她一料的苹果收入可以抵其他人三五料的庄稼收入。
她的大儿子这时初中毕业,她用这笔钱给儿子买了四轮拖拉机,后来又换了汽车。她村的第一辆私人拖拉机,第一辆私人汽车就是从她家里开始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殃,九十年代中期,娃他姨妈的事业进入了低谷:由于地理环境制约,她家的责任田向阳不耐旱,苹果严重减产,儿子养车赔钱。
象坐过山车一样,倏地一下,娃他姨妈的收入从高处跌落下来。
她委屈,心酸,熬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她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咋办?咋办?人生还长,生活得继续,生命得延续,出路在何处?
然,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她无路找路了……
建陵乡有一个村叫明桥村,具体位置在她高树村的西北方向。历史上对明桥有记载:金桥银眼石栏杆,涝池岸的杨柳万万千。当然,明桥也是建陵的交通要道了。明桥村南连十几个自然村,北接十多个村。
明桥村又临县级公路,离乡政府所在地东店头村不远,是建陵乡东北片人赴县赶集的必经地,又是临时栖息地,因为明桥有车站,车站上几乎从早到晚都有人。
并且,包括明桥村在内北边的这十几个自然村的土地阴一点,几乎不受干旱的侵扰,每年的苹果几乎全都是丰收丰产。
农民手中有了钱,开始为过世的亲人大操大办埋葬,为娶亲出嫁的儿子女儿也大办婚礼了。抓住这一机遇,娃他姨妈把家搬到了明桥村,搬到了车站旁的别人看苹果园的小房子里了,开始经营纸活店。
心机在某种程度下,等于时机,而时机在特定环境下,又等于商机。娃他姨妈在心机的驱使下,抓住了时机,碰到了多年难遇的商机。
记得当时明桥村的人苹果收入颇高,人说话比较夸张,一次遇见明桥村一熟人,他问:“自家人,你把苹果卖了吗?”我村和明桥村连畔种地,并且都姓袁,所以他这样问。
“没有。”我答。
“我卖了,把钱存到银行了,让他给咱先慢慢滚利着。”自家人的嘴里心里都洋溢着张狂。
当时还有人打趣说,南岭头村的人更为狂妄,一次从口袋掏手帕擦鼻涕时把二元零钱带了出来,他没有拾,反而用脚把钱扫到一边,嘴里说:“你想走了就走吧!我也不拾了,划不着为拾你弯一次腰。”
在这种情况下,开纸活店,那收入会少嘛!
虽然是一间很小的果园房,周围全是田野和果园,但寻娃他姨妈做活的人不少。

好处是这果园房和明桥王姓人的带锯相邻,有电灯可以照明。虽然吃水要到村子里去担,得跑半里地,但做纸活却亮亮堂堂,如同白昼。
那时,娃他姨妈接的活常常由于时间紧迫,赶不出来,我妻常常去给她帮忙。
机不可失固然重要,时不再来更重要,人到了某种特殊环境下,确实要拿人肉换猪肉吃啊!
人啊人,有时候,得把智慧发挥到极致,还得把时间安排到极致,把体力发挥到极限。只有都“极”了,你才会有极丰厚的收入。
两年没出去,虽然说娃他姨妈累得几乎掉了几层皮,但她又一次翻身了,还清了欠款,还有了少量积蓄。
说起来,娃他姨妈实在不简单,二年期间,她不但学做白事的亭子、架蜡、高斗、罐罐纸、摇钱树、九莲灯、金童、玉女等传统产品,还创造发明了紧跟时代脉搏的现代产品:彩电、沙发、席梦思床、手机等五花八门的东西。
确实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她不会做的。
另外,她还发挥她裁剪衣服的特长,给那些过世之人,缝制纸衣服,以备祭祀烧用。



她缝制的衣服除了传统的长袍马褂之外,还有现代人时兴的中山装、夹克、毛衣毛裤、线衣线裤、衬衣衬裤,甚至还有礼帽、热水瓶、手提包等。
她的门类太齐全了,常常使寻来做活的人目瞪口呆、赞口不绝。
建陵乡最早的花圈就是从她的纸活店开始有的。她的每一件纸制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件绝美的工艺品,她做的衣服挂在空中的铁丝上,谁都以为是一件真真正正的布制品,决想不到是纸糊的。
她还专门研制了各种鞋。有小脚女人的尖鞋,有大脚女人的方口鞋,松紧鞋,登山鞋,旅游鞋,还有老年男人穿的圆口鞋,靴子,皮鞋……

总之,只要现时时场上有的品种,包括纸糊的老式烟袋,她都能给你做出来。
红事上,她又会画又会剪,还能挽花,什么窗花拉花,什么喜字红包,什么彩结中国结,她都能变戏法似的给你弄出来,不由你不折服。
爱写作的人讲形象思维,娃他姨妈虽不懂这些,但她可以创新,可以立异,可以让你花较少的钱办较多的实惠事。
你可以想象,她的灵巧,简直就是一个见啥会啥的艺术家……
钱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宝物,没有时,人睡不着,寝食不安想得到它,有了时,人还是睡不着,同样寝食不安想利用它,发挥它。
终于,在这么一天,娃他姨妈又盘下了礼泉县北什字二间门面房。
这两间门面尽管不大,但连人家原来的货盘,八万元。
八万元对有钱的人说,可能如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可对手中仅有一万多元的娃他姨妈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没有那么大的肚子,还要吃那么大的馍,这不光要有识,更重要的是要有胆。胆往往是和钱连在一起的,有钱的人胆大。
赌场上有句话:钱多的赢钱少的,胆大的赢胆小的。但做生意不是赌啊!
对这一决定,娃她姨妈家几乎所有人都不支持,都劝不要盘门店。都说咱目前的状况是挣起赔不起。
可她不行,她说她已经做了调研,经营再不好,充其量弄个娃打娃,不赔不挣。
最后,大家合计了好长时间,才决定盘下来。
那大概是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冬天,娃他姨妈盘下了那两间门店。于是,所有亲戚都帮忙给凑钱。
我那时在建陵教育组工作,由于经常和信用社有业务往来,寻人给贷了二万八千元。
那天,天下着鹅毛大雪,娃他姨伯来建陵取贷款时,我正好去西片检查学校去了。他姨伯是中午从县城坐班车来建陵的,见我不在单位,又撵到西片山王学校,可那时我们检查组从山王走到了宁家。
那时通讯不便,待我知道折回山王时,他蹲在一户人家的门楼下,简直和讨饭的差不多。
后来我二人顶风冒雪步行十多里回到建陵,多亏我人熟,人家下班了还加班给我办了手续,取了款。
象这种顶风冒雪的,苦点累点的事,在那几年,是娃他姨妈的家常便饭。
一个女人家,就这样,在县城的北什字立足了,开张了,营业了,当然,后来也发展了……
一转眼,近二十个年头了,前年娃她姨妈买下了这二间门面,六十万元。
如今她仍然经营这两间门面,生意风生水起,一直不错。
这一路走来,从高树到明桥村,从明桥村到礼泉县城,从盘租门店开始到如今的买下门店,从农民到城市居民,娃他姨妈的致富是一本厚厚的书。
这书里有聪慧,有灵巧,有辛酸,有眼泪,有辛苦,有勤劳,有毅力,有精力,更多的是苦力和耐力。
我之所以把娃他姨妈写出来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好好读读这本书。只有把这本书读懂了,你离致富成功的大门就近了。



作者:袁炳纲,一九五五年生于昭陵镇坡北村,一九七二年参加教育工作,一直执教于坡北初小。一九九六年调原建陵教育组工作。二零一五年退休,小学高级教师。从小热爱文学,曾在陕西日报,咸阳报及秦都文艺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