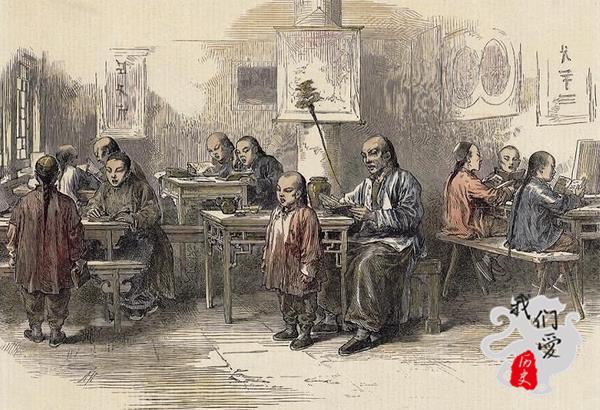文|肖复兴
关于老北京胡同里的吆喝声,张恨水曾经充满感情地这样写过:“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喝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谐和,无论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虽然这里面有部分是极简单的,如‘羊头肉’‘卤肥鸡’之类,可是他们能在声调上,助字句之不足。至于字句多的那一份优美,就举不胜举,有的简直就是一首歌谣。”
张恨水不是北京人,但他说得真好。没错,有的吆喝声真的就是一首好听又上口的歌谣。有了这样的吆喝声,让胡同一下子色彩明亮起来、生动起来,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记得那时候有打糖锣的小贩,打着小铜锣,老远就能够听见,一声声,清脆悦耳,让人心动,紧接着听见的便是他的叫唤声,更像是伸出手,招呼着我们一帮小孩子跑出院子,簇拥到他的担子前,听他接着唱歌一样地吆喝。我记不住他都吆喝什么了,后来看到有北平俗曲《打糖锣》里面这样唱道:“打糖锣的满街的叫唤,卖的东西听我念念:买我的酸枣儿咧、炒豆儿咧、玉米花儿咧、小麻子儿咧、冰糖子儿咧、糖瓜儿咧……”
我见到的打糖锣的,嘴里唱的没有那么复杂,卖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样,不过是一些我们小孩子爱玩的洋画呀玻璃弹球呀之类简单东西。曲子里唱的那些吃的有的倒是有,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酸枣面,一种像黄土的东西,用手一捏就能捏成粉末,吃进嘴里酸酸的感觉,也有人用来冲水喝,是我们那时的饮料。
长大以后,读泰戈尔的小说《喀布尔人》,看里面那个来自喀布尔的小贩,每天摇晃着拨浪鼓,同样吆喝着走街串巷,是那样的辛苦,甚至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那种心酸,和对自己小女儿思念的那种心碎,心里很是感动。想起自己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打糖锣的小贩,其实和这位喀布尔人一样,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人,自有人生的苦涩与艰辛。吆喝声中,含有人世间的心酸,不是小孩子能够懂得的。那些吆喝声中凄凉的声调和无尽的韵味,更是小孩子难以体会得到的。

常听到的还有卖花的吆喝声,格外悠扬好听。不过,我们不会特意跑出院子去凑热闹,一般都是大姑娘小媳妇爱去买点纸花或绒花,插在发髻上;要不就是一些爱侍弄花草的老人,买盆鲜花,放在自家门前或窗台上养。后来读清诗,有这样一首绝句:“颇忆千年上巳时,小椿树巷经旬时。殿春花好压担卖,花光浮动银留犁。”诗里写的是小椿树胡同里挑担卖花的情景。
读柴桑《京师偶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千叶榴花,其大如茶杯,园户人家摘入掷筐中,与玉簪并卖。但听于街头卖花声便耳心醉。”如此大朵的石榴花,我是没有见过的,也没有见过有这样的花卖。不过,他说的听见街头卖花声就耳朵和心一并醉了的情景,还是让人那么向往。
卖花声,大概是所有吆喝声尤其是那些带有凄凉或哀婉调子的吆喝声中一抹难得的亮色。《燕京岁时记》里说:“四月花时,沿街叫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说的真是,确实有味。
吆喝声,尽管里面有不少美好的韵味在,但在时过境迁之后怀旧情绪的泛滥中,很容易被美化。毕竟吆喝声不是音乐,不是诗,是底层人为生活而奔波发出的声音,内含人生况味,和诗人笔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和《天咫偶闻》里记载皇上八月隔墙听到吆喝声而写下的诗句“黄叶满街秋巷静,隔墙声唤卖酸梨”并不一样。

读到的很多关于吆喝声的诗句,其中有这样两首,让我为之心里一动。
一首是夏仁虎《旧京秋词》中的一句“可怜三十六饽饽,霜重风凄唤奈何”,让我感动。下面还有一句注解:“夜闻卖硬面饽饽声最凄婉。”起码这里面触摸到了吆喝声中的人生无奈与心酸的痛点。
一首是金煌《京师新乐府》中的一首《卖饽饽》:“卖饽饽,携柳筐,老翁履弊衣无裳,风霜雪虐冻难耐,穷巷跼立如蚕僵。卖饽饽,深夜唤,二更人家灯火灿,三更四更睡味浓,梦中黄粱熟又半……”写那寒夜里吆喝着卖饽饽的老人的凄凉情景,让我感动。想想那时候的胡同,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数九寒天,哪怕是深更半夜,也是少不了一两声吆喝声的,就像京戏里突然响起的一两声“冷锣”,即使你住在深宅大院里,也能够隐隐约约地传到你的耳朵里,轻轻地却也沉沉地一震在你的心里头。
在那些物质贫寒、天气寒冷的夜晚,那吆喝声,诗意是让位于夏仁虎所说的“凄婉”和金煌所言的“难耐”的。人生中沉重的那一部分,世事苍凉的那一部分,往往弥散在夜半风寒霜重甚至雨雪飘飞时的吆喝声中。
记得张爱玲曾经写过每天天黑时分一位卖豆腐干老人的吆喝声,她是这样说的:“他们在沉默中听着那苍老的呼声渐渐远去。这一天的光阴也跟着那呼声一同消失了。这卖豆腐干的简直就是时间老人。”

张爱玲说的是上海弄堂里的吆喝声,北京胡同里的吆喝声也是一样的,半夜里那一声声吆喝声渐渐消失的时候,一天的光阴也就过去了。那些不管是凄清的还是昂扬的,是低沉的还是婉转的吆喝声,都是胡同里的时间老人。它们的苍老乃至消失,是时间老人对胡同历史沧桑的见证。
还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战争年代被迫流落异乡的北京人,深夜里听见了同样如同时间老人一样的吆喝声,只是和张爱玲说的不同,不是卖豆腐干的吆喝声,而是卖花生的吆喝声:“至于北风怒吼、冻雪打窗的冬夜,你安静地倒在厚轻的被窝里,享受温柔的幸福,似醒似睡中,听到北风里夹来一声颤颤抖抖的声音:‘抓半空儿多给,落花生……’那时你的心头要有一个怎样的感觉呢?”
面对夜里的吆喝声,他的感受,和张爱玲是那样的不同。张的感受更多是客观的、冷静的,而他则是感性的,充满着感情。特别是在远离北京听不到熟悉的吆喝声的时候,这种吆喝声,更加让人怀念,更加撩人乡愁。
无论是夏仁虎笔下卖硬面饽饽的吆喝声,还是张爱玲笔下卖豆腐干的吆喝声,或是最后那位无名者笔下卖半空儿落花生的吆喝声,作为从农耕时代步入城市化初始阶段诞生的吆喝之声,听者和吆喝者的意味是不尽相同的。特别是在寒冷的深夜,在荒寂的胡同,在漂泊的乱世,那些吆喝之声,更多凄清甚至凄凉,含有对人生无尽的感喟,也含有对世事无奈的慨叹。
如今,这样的吆喝声几近于无,让人们在对它连同对胡同不断消失的怀念情感之中,夹带着更多的乡愁。那种声音,只可以模拟,却不可以再生;只徒有其声,却难得其魂。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