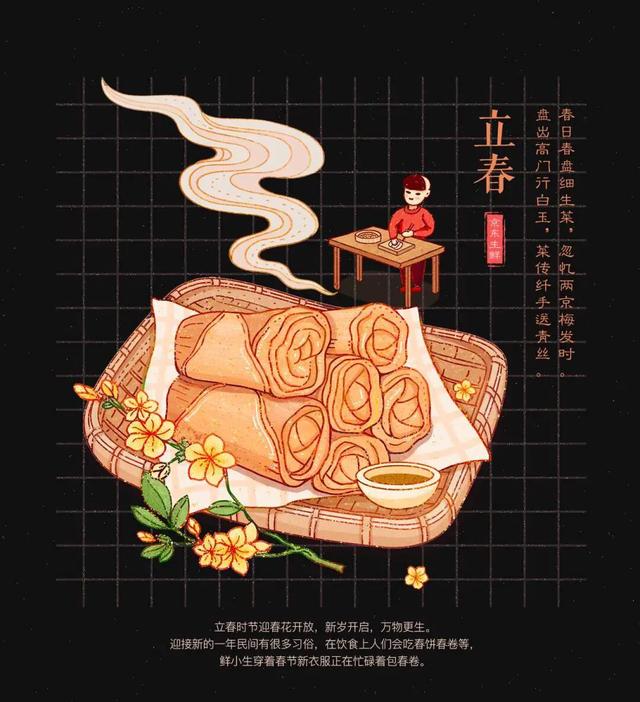本文来源:《中国妇女报》2018年9月25日
转自:社会学吧
作者,肖巍,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以《翻译中的社会性别/超越单语主义》为题做了主题演讲。在巴特勒看来,性别概念实际上需要一种特有的语言指派形式,她试图探索当社会性别概念被翻译成不同语言时,由于语言指派、权力结构及科学解释等差异,人们对它作何理解?这些理解对女性地位、发展条件的影响是什么?她提醒我们不要把社会性别概念预设为“单语主义”的,要意识到其不对等性和不可翻译性。

近日,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以《翻译中的社会性别/超越单语主义》为题做了主题演讲。可以说,自1990年出版《性别麻烦:女性主义和身份的颠覆》一书以来,巴特勒便一直在引领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的发展,她对于性别化身体“祛自然化”的解释,对于异性恋模式的批评,对于性别表演理论的构建,以及近些年来对于政治哲学的探索都在哲学和性别研究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与她的交谈中,她曾爽朗地说:“人们都以为我仅仅研究性别,追求那种随心所欲的性别自由,实际上这只是我的一个小目标,我真正想做的是通过探索性别问题追求一个理想的人人宜居的社会。”
性别必须通过文化和社会得以阐释
在这次演讲中,巴特勒主要讲了社会性别(Gender)在不同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她观察到,女性主义哲学创始人、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未曾使用过“社会性别”概念,因为它在法语中也是一个外来词,不仅如此,“它在许多语言中都是一个外来词”,由此“便会遭遇到抵抗”。波伏娃主张“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这一名言为女性主义理论区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奠定基础,它让人看到即便性别是一个自然范畴,也必须通过文化和社会得以阐释,并不存在一种“自然目的论”指导女性发展成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女人。
巴特勒的这些理解让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当一个男性被视为“娘炮”,一个女性被说成“女汉子”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本质”与“性别本然”,而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性别符号,不论人们怎样强调后者的“自然性”“真理性”“客观实在性”等等都是如此。基于这番认识,那些终日奔波于事业的女性根本无需在意自己是否被议论缺少“女人味儿”,因为这些议论多半来自人们的性别刻板印象。“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男性可以来自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女性,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女性可以出自一个生物学意义的男性,因而社会性别仅仅是一种选择。”
性别是一种“境遇”
巴特勒的这一解释似乎还能打消人们的一种疑虑,根据社会性别理论,“生母”并不等于“慈母”,但还是有人不免要追问:“生母的事实在慈母的社会意义中究竟占有多大成分?”“女性难道不比男性更具有母性吗?”对于这些问题,巴特勒式的回答是:我们并未否认女性作为生母的生物学事实,然而一旦需要解释母亲应当如何时,便进入到社会和哲学概念层面,是否能成为“慈母”,以及相应的比例取决于这位生母的“境遇”。同样,男性在特有的境遇中也会成为慈母,因为这些都不取决于谁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我们之所以有这些疑虑是因为总是把女性生育的“自然事实”与由社会和文化界定的“自然事实”概念混为一谈,而后者在巴特勒看来是“由它们置于其中的境遇组织起来的”。
巴特勒还分析说,如今的波伏娃继承者对于性别大体上持有三种看法:其一,认为生物学性别对于社会性别塑造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后者是一种生成形式;其二,相信性别本身是一个自然事实,但需要质疑建构和描述这些事实的科学,因为它们通常是有偏见的。例如,一些关于女性弱势社会地位和不平等的假设都是建立在“科学”假设基础上的;其三,主张性别是一种“境遇”,意味着它是在一系列社会历史过程和权力形式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指派,尽管女性不是由生物学决定的,但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始终需要在自身的境遇中挣扎,寻求从社会和文化内部作出改变,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平等。每个女性都必须承担这种改变的责任。
性别需要一种特有的语言指派形式
波伏娃理论让人意识到,在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容易填充的鸿沟——如果人们认为性别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会把对于性别特有的版本视为理所当然的,而这种理解却是基于“我们所讲的语言,或者在一系列确定的社会和科学预设之内”。在巴特勒看来,虽然性别概念通过语言被普遍地建立起来,但它实际上却需要一种特有的语言指派形式。
针对巴特勒这次讲演的题目,人们也许还有其他疑问:“难道人们对于性别的理解会有差异吗?”“我们的理解与遥远的古人,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有什么不同吗?”“如果这样,谁应当是性别的最终定义者?”巴特勒似乎窥视到了我们的内心,她以一如既往的直率方式回答说:“没有任何语言有权力,或者权威给予性别确定性的命名。性别总被一种语言占据着,尤其是那种具有科学权威性的语言。我不想为语言相对论辩护,相反我只想知道当我们在多种语言背景下理解社会性别时,将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巴特勒试图探索当社会性别概念被翻译成不同语言时,由于语言指派、权力结构、文化,以及科学解释方面的差异,人们究竟对它作何理解?这些理解对于女性地位,发展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是什么?
巴特勒也敏感地发现,社会性别概念无论被翻译成哪种语言都会遇到困难。这是由于:第一,性别并不能与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塑造的语言构成分开,而就性别作为一种语言构成来说,性别事实上与社会性别并无二致;第二,社会性别是一个外来词,总给翻译者造成困难,它抵达到任何语言中都是这种翻译困难的产物,并在各种语言中从未有过相同的含义。20世纪50年代,这个词在英语中被创造出来,但即便对于英语国家来说,它也是一个外来语,而且一进入语言中便会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对于这个概念本身和女性意味着什么呢?
巴特勒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思考下面一些问题:“当社会性别进入到一种语言,例如英语或者其他语言中时失去和获得了什么?”“作为一种外来语,它带来什么样的困扰?”“为什么在关于社会性别的争论中,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单语主义预设?”因此,“翻译才是使社会性别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用分析范畴的条件”。然而,无论我们怎样翻译,都存在着概念的不对等性和不可翻译性,这些属性会导致一些社会和文化抵抗社会性别概念。在抵抗者看来,社会性别就等同于同性恋、平等、女性主义、变性人、爱、婚姻、生育自由,以及流产权利等。
面对这一局面,巴特勒不断提醒女性主义者注意到不同文化对于“社会性别”概念的翻译和理解,不要把它预设为“单语主义”的,而且也要意识到这一概念的不对等性和不可翻译性,从而也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不同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