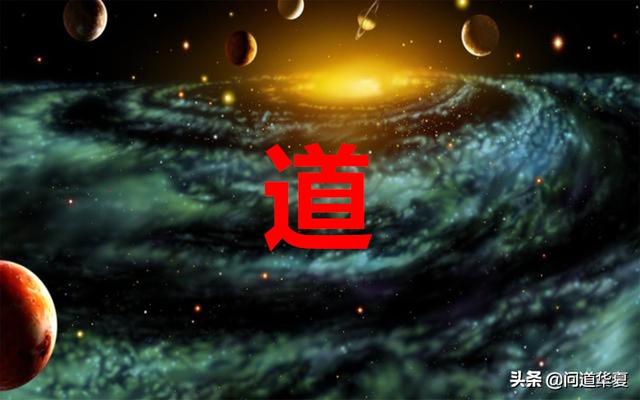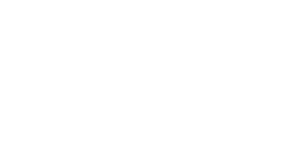我们常常把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中的“昔之得一者”中的“一”理解为“道”,口头表达上说得过去。但是,既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一”就不是“道”,如同“二”不能等于“一”,“ 三”不能等于“二”,“万物”不能等于“三”一样。

那么,这个“一”如果不是“道”,又是什么?
老子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正。亓致之也,胃天毋已清将恐莲,胃地毋已宁将恐发,胃神毋已灵将恐歇,胃浴毋已盈将恐渴,胃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厥。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胃孤寡不谷,此亓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
通常的注解大体都是这样的:往昔曾得到过道的:天得到道而清明;地得到道而宁静;神(人)得到道而能显神通;河谷得道而充盈;万物得到道而生长;侯王得道而成为天下的首领。推而言之,天不得清明,恐怕要崩裂;地不得安宁,恐怕要震溃;人不能保持灵性,恐怕要灭绝;河谷不能保持流水,恐怕要干涸;万物不能保持生长,恐怕要消灭;侯王不能保持天下首领的地位,恐怕要倾覆。所以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因此侯王们自称为“孤”、“寡”、“不谷”,这不就是以贱为根本吗?不是吗?所以最高的荣誉无须赞美称誉。不要求琭琭晶莹像宝玉,而宁愿珞珞坚硬像山石。
上述注解引自“快懂百科”(百度等百科一样),可见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大众化的解读法。
同样,这里的“抱一”“执一”,也是当作“道”来理解的。把“一”提高到“道”的层次来理解,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它会让人产生“一”即是“道”的错觉,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那么,这个“一”跟“道”有何区别呢?
刘笑敢教授认为,这个“一”突出了世界总根源和总根据的统一、惟一的特点,用“一”字有其必要和新义。”但是刘教授并没说明白这个“一”跟“道”的区别。
徐观复教授则直接说:“《老子》上的所谓‘一’,宽泛一点说,是形容道的无分别相,所以‘一’便是道。”也没说清楚。
因此,这个问题得从“形上”“形下”来分析。
“道”是形而上的、超越的、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静态的;而“一”如同一个“混成之物”,如同鸡子,既然它是鸡子,那么它就是形而下的,实存的、相对的、动态的。
因此,可以说:
“一”是由形上向形下转化的“总枢纽”。
我们来看看这个总枢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万物从“无”开始,然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无”,“二”则意味着分化,“三”意味着众多,“万物”是指已经呈现的万象,是“有”,因此,“一”就是从“无”到“有”的媒介,是“无中生有”的“转换器”。
就是说,“一”意味着从绝对性向相对性的转化。虽然“一”依然是无形的,但是它却具备了“初始”的功能,因为“一”是数量的开端,是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集合体,它蕴含万事万物,且贯穿万事万物的生命周期。
宋钘、尹文、王充等黄老道家的“气一元论”是以“气“或“炁”来解释宇宙生成论的,这种观点认为:道生一以后,阴阳二气构成了“一”的全部,阴阳和合又生出“和气”,于是有了万物,有了世界。
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学者们基本采纳了这种观点,严遵、魏源等也把“一”当作“气”来注解。这也是程朱理学的奠基理论。理学家认为,道(理)是超越的,道一气二,道是本,气是构成万物的质料。
理学家的“气”,其作用地位,相当于道家的“一”。但是无论是道家,还是理学家,也无论怎么理解“一二三”的关系,它都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
“一”还是从“静”到“动”的过程。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宇宙万物无一不处在永恒的变化中。老子说: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恒也。”
就是说矛盾着的双方是相反相成的,一方的存在是以对立方的存在为条件的,一方消失,则另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个法则是永恒的。因此“静动”也是阴阳的统一体。
阴阳的静动与和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历来注老者通常的说法是:万物背阴而向阳,并且在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
本人也曾信守这一说法,但是一直很矛盾。因为:既然万物都已经产生,那么这个“万物”还要产生什么新的和谐体呢?
所以,“负阴抱阳”,应该是“营魄抱一”,唐玄宗李隆基解释:“魄则阴虚,魂则阳满”。就是说魄是阴性的,魂是阳性的,负阴抱阳就是静动结合,阴阳和合;所谓“冲气以为和”,就是将元气关注其中,是为“抟气致柔”。冲,灌注,意思是将“元气”注入其中。
总之,“一”作为“道之子”,它的意义在于:将蕴含无限生机与能量的“混成”之物,化生成宇宙万物,因此“一”就就取代了“道”,成为万物生发的动力源,也是万物生发的规则,它决定了一切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规则。
因此这个“一”如同“道”和“无”,它就是“一”,不能将它理解成“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因为,“道”永远是超越的,虚无的;而“一”则处在“形上的道”与“形下的万物”之间,“一”的任务才是化生万物。
有一些老学研究者就从不对“一”就行解读,比如陈鼓应先生,他的前后三次注解里,就直接说“一”。
因此,把握了“一”,也就把握了一切运动变化的规律。所以说“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