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是古代书法最早借用的哲学概念之一,并且与之相伴始终,成为传统书法批评之普遍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在两千年的书论中,无论这一概念出现与否,人们都会自觉地运用其原理,以期实现批评的最佳效果。迄今为止,虽然书法理论、书法美学的研究时有涉及,但多停留在概念之一般意义的阐释上,对其原理与涵义的变迁、在审美与批评中的具体运用等方面,尚无必要的关注和理论分析, 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或借鉴。对此,本文拟做初步的探索,并就正于同道。

一、“法象”与“意象”
采用“法象”的概念来描述书体和书法作品的美感状态,始见于汉代崔瑗的《草势》。该文在概述文字和书体演进之后论及草书书法云:“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法象,谓自然万象,这里指草书的点画形势;俯仰,概言草书丰富多变的动态;仪,仪刑、法式,亦即取法。在崔瑗看来,草书字形的生动之美取法有自,证以后文完全采撷物象喻说的做法,可知包含了取法自然的思想。张怀瓘《六体书论》“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的思想,即承此而来,后人假托于蔡邕的《九势》“书肇于自然”的著名观点,亦权舆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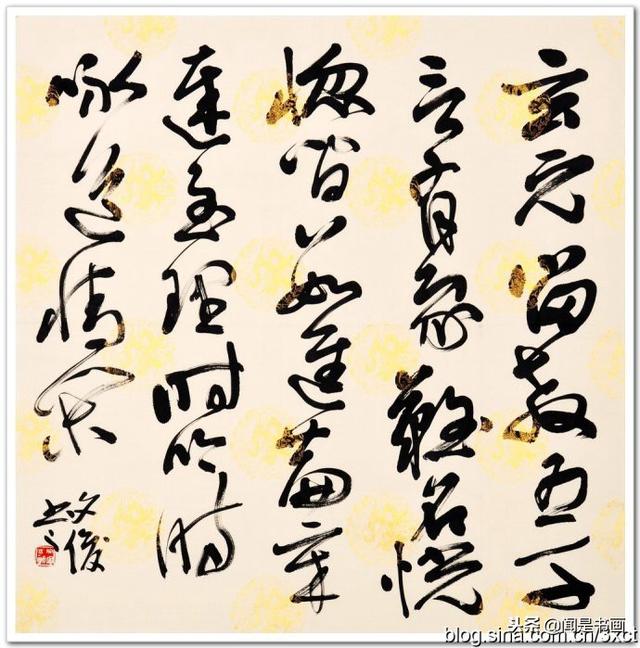
“法象”与自然美是早期书论从文字观到书法观的转化产物,或者说是从文字学理论启蒙而来,有其历史的必然。文字的符号体系成于象形,其基本形体都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有“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特点。 再以基本形体作为偏旁,辗转组合而成“会意”、“形声”的复合字形,所谓“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即其产生与发展历程的生动概括。其后书体样式多变,渐次陵夷,最终脱去象形,演进而成由各种抽象点画结构字形的近世诸体。由于古今书体并行同用,书家例能诸体兼善,遂使古体成为近体书法审美的参照及理论来源。“法象”的适时介入,使自然美成为书体美的本原与基本属性, 书法要有“物象生动可奇” 的见解也随之成为最普遍的艺术认知和量说标准,孙过庭《书谱》“同自然之妙者,非力运之能成”、传李阳冰《论篆》“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等观点,都很有代表性。但是,朴素的“法象”思想不尽适用于抽象的近体书法的发展和理论思考,在其逐渐深入人心的同时,缺憾也开始显现。例如,传蔡邕《笔论》提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的观点,影响到书写的随机性和自由发挥,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和作品之间,很难看到理想的对应。唐太宗《指意》质疑云:虞安吉云: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耶?纵放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

“象本”,指书写应该做到造字之初的自然状态,把象形文字的仿形与近体的抽象审美之两个颇不相同的发展阶段混而为一,故言“未可称解笔意”。换言之,随着草、行、楷诸近体书法的发展,人们已经逐渐地提升了对其抽象美的认知能力,并在书写中日益强化主体精神,于是泛化的自然美与艺术通感的理论适时而生,突出主体体验的“意象”出现即其标志。张怀瓘最先洞知其中的玄机,并从理论上近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六体书论》评张芝草书云:功邻乎篆籀,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

首二句以“篆籀”代表字原,意谓张氏草书能像篆籀一样,去探知万象,还有“法象”的痕迹;“元精”,义犹西方艺术理论讲的“生命形式” ,“取其元精”,亦即取神;“形似”谓不似而似,以其妙和自然,故曰“最为近也”。其《文字论》称“惟张有道创意物象,近于自然”,即其证。又,其《书议》云:“何为取象其势,仿佛其形?”结论是“猛兽鸷鸟,神彩各异,书道法此”,指明了书法之所以要取象万物、法效自然的道理。关于取象之道,他的看法是“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亦即取法万象之“势”及“理”,最终裁成作品的一种面目。张氏在《文字论》中自述写草书能做到“探彼意象,入此规模”,而《书议》论之云“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相”。由此可见,“意象”堪称有物无形之相,是“形而上”的哲理认知,其深奥完备,已远非“法象”可比。“意象”之义有二。一是导源于《周易》的“意”与“象”,在作品中表现为秉承自然之美的书意或笔意与点画形势的生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也就是说,象由意生,意藏于象,所以象能达意;言能释象,只有正确理解论言的涵义,才能准确地说明表象之所以然、再透过表象去寻绎隐含的深意。刘熙载《艺概?书概》云: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先天”,谓未形之前,书意之自然美的法则即已存在;“后天”,谓既形之后,作品之“象”具有自然之美的变化与生动,故可以体现其相应的功用、意义。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属于作者主体精神的人意,包括性情、观念、学养、审美旨趣和寓寄等,使书写在既定的书体、师承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进行个性风格的输入与创造。作品完成,所见现象和经验可以体味的技术运用即为象,象为表现作者主体精神而具有独到的价值。

二、“意象”与“想象”
对书法作品的审美而言,意深隐而象显著。深隐者难以索求,显著者易于粗疏,故尔虽胜流名士,也会有“极难下语”、“言不尽意” 之叹。有鉴于此,古人在用书面语言表达所见所得的时候,往往要通过迁想妙得,借助其他事物来加以说明,由此产生审美之另一种与作品对应的“意象”。这里,良好的感悟能力、想象力和语言文学的修辞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感悟能力表现在解读作品之“象”、再通过象的提示来追微捕虚,寻绎到深藏其后的“意”;想象力表现在解读作品的“意象”之后,如何进行审美联想,找到一种生动易知、概括传神的对应“意象”;语言文学的修辞能力表现在对书面语言的加工、对所得对应“意象”进行提炼、夸张渲染,以期达到喻说的最佳效果。如此,则需要使“想象”在作品“意象”和书面表达“意象”之间构筑起良好的同构和对应的逻辑关系。即使仅仅提示一种审美联想方向的隐喻曲说,或是审美差异所致的歧说殊见,都不能例外。在两种“意象”之间,或形貌动态的类似,或原理精神的相通,只要把书面语言中的“意象”弄懂了,书写技术、作品的美感与风格也会随之了然于心。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语简,行文讲究炼字,审美描述或风格评说时往往采用一二字或数字来做“意象”表达,此即黄庭坚《题绛本法帖》所讲的“语少而意密”的修辞习惯。如果语简,提供的“意象”也随之趋简。意犹未尽,则采取增加字词以多取“意象”进行喻说的表达方式,既可以作为前者的补充说明,也可以省略前者而单独使用。简洁的用语大都是通行无碍的“意象”概括,有“约定俗成”的特点,例如“雄强”、“险劲”之类;或者有历史性的词义变迁,或词义本身即有相对性及经常变易的特点,例如“遒媚”、“雅俗”之类。举凡要做补充说明,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作品美感丰富而多变化,一言难尽所得;二是行、草书天然地具有复杂的内涵及风格表现,需要多角度的观察描述;三是评论者主体感受的微妙难言,简语不能曲尽其意;四是文体的或文学修辞的需求与习惯使然。例如,传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评王羲之书法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其中“雄逸”是经验性词语,从总体上概括王书风格,不别书体。“雄”有动态、静态二指,此为前者,言其笔势的运动状态及其释放出来的力感,可以和知识传习、日常生活体验中任何“雄”的“意象”做泛化的对应;“逸”言笔速,状其笔势飞动,辅助说明其用笔“凌空取势”、“一拓直下”的特点。意有未足,则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两种纯任想象并极度夸饰的“意象”再为补充说明,“如”字表明前后引申、譬喻的次第关系。由此可见,审美想象是自由的,它可以任凭经验所至,务取生动传神。至于米芾抨击其“征引迂远,比况奇巧” ,则受其时历史语言和文风变迁的影响,不为真知。再如,张怀瓘《书断?神品》评王献之书法云:至于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絶,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锺、张之神气。
这是对小王行草书法的整体把握。“兴和”犹言笔势开阖、放收,“孤峰四绝”形容字形体势的险峻特出有如高耸的孤峰,复以“迥出天外”作为补充说明,归结之“峻峭”则再度明其行草书法的势险,以作为美感、风格的总括。“雄武神纵”言其笔势雄强勇武、有如神明助其纵横奔逸,以作为“兴和”的延伸;“灵姿秀出”美其点画字形的变化多姿、灵动挺秀,以弥补“峻峭”的单一。至此,小王行草的审美描述与评说已大体完备,但张氏尚未满足,继续铺陈。“臧武仲之智”,以臧武仲的聪明才智和预见性来说明小王书法的意在笔前、智巧兼优;“卞庄子之勇”,取卞庄之勇来喻说小王笔势的勇武直前、无往不胜。更以“大鹏 风”来夸张用笔的开阖斩斫,以“长鲸喷浪”来形容其气象的恢宏壮观,以“悬崖坠石”通言其笔势的威猛可畏,以“惊电遗光”喻其笔速的飞动奔逸。最后思索诸般美感的所自由来,是作者的意气纵横弥满,笔虽尽而意尚有余,再以“夺龙蛇之飞动”神而明之,以“掩锺、张之神气”誉而尊之,嘎然作结,余音绕梁。比较而言,“峻峭”重在形势,“雄武”偏言气势,为评说小王行草的两个基本“意象”,其余都是从不同角度所做的渲染、充实。从文章来看,既有汉赋的想象铺陈,又有六朝的华丽荣滋,真气鼓荡,文章与书道已经融合如一了。由此可见,张氏不仅善于运用“意象”,也极富于“想象”,所取虽非都是真实的存在,而其深闇书道、善解小王,使批评生动、有效,无人能出其右。

古人在阐述具体的技术问题时,也经常会采用“意象”以明其理,既便于学者感悟,又利于培养“想象”能力。例如人们所熟悉的《笔阵图》,论点法要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意谓作点要像从高峰坠下的石块那样迅疾威猛,亦即打笔而入,重击落笔后旋即弹出,故曰“磕磕然实如崩”;论长横之法要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意谓紧駃战行、一波三折,开阔大气,平实中隐含波澜;论戈法要如“百钧弩发”,意谓曳笔张力强劲,有如强弩之引弓待发;论竖法要如“万岁枯藤”,意谓涩势行笔,曲而能劲,内含无限生机,等等。该文论说点画之法重势轻形,选择“意象”喻说也重在原理,不言法而法自在,不言意而意自明,“想象”生动传神。唐太宗《论书》自述“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就是这个道理。又,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篆书的笔力为何需要掩藏、怎样掩藏?如何感知“气”的存在、以及如何在平稳的“运笔”中保持生机的通贯不息?隶书的笔势为何取“险”、怎样取“险”?节奏的提按抑扬、简洁明快又是如何体现“奋斫”之法的?如果没有“意象”的提示,篆、隶笔法差异很难有如此生动的表达。透过“意象”,我们还可以知道,“力弇气长”出自《书谱》“篆尚婉而通”的基本笔法和美感的概括,从玉箸篆法中总结而来;“势险节短”出自《笔阵图》的“凶险可畏如八分”,“奋笔”出自张怀瓘《玉堂禁经》的“奋斫”,而书体和作品风格样式则基于汉魏梁鵠、毛宏一系之整饬方劲的碑刻隶书,包含了元明清人对汉隶的误解在内,如吾衍《论篆书》称“挑拨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丰坊《童书学程》称“分书以方劲古拙为尚”而以师法于曹魏的文征明隶书为说、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称“隶书当以梁鵠为第一”而以曹魏的《受禅》、《上尊号》等碑当之,均其例。

古人善于在评论中运用“意象”,至此已可窥其全豹,那么,它们是如何通过“想象”而生出的呢?王僧虔《书赋》云: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
意谓书法要能于虚无中“想象”其有,以人的性情去比类万物的性情,使心意顺从自然物理、法则,万物就会成为真实的存在,手随心动,毫从手运,则笔下就会备极生动,妙同自然。传虞世南《笔髓论?契妙》也有类似的见解:
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心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有态度,心之辅之;心悟非心,合于妙也。且如铸铜为镜,明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
“无为”出《老子》,谓书法之迹顺乎自然,因于物理,故须禀承阴阳变易之理而或动或静,运笔拟效万物而成点画形势,“禀阴阳”、“体万物”与“心经于则”是同一事物而从不同角度为说;“神遇”、“心悟”与“测”、“图”相类,都是“想象”,都是指示书法通于自然与如何取效的道理;字形态度为“心之辅”,即宋人视书法为“心画” 、项穆《书法雅言?心相》视作品为“既形之心”和“心相”的认知;“心悟非心”谓心悟于至道与自然物理,笔下则如《书议》的“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假笔转心”和“手以心麾”是一事的不同表达方式,言书法之妙在心而不在笔。又,刘熙载《艺概?书概》亦云:

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也。
“观物”的目的在于以人心去“想象”、比类万物之情,以通达神明之德。如是,则书之前作品已成于“想象”,书之后作品已备具与之同构的“意象”,而作书之时已经天人合一矣。《性理会通?字学》述程子语云:“须是思,方有感悟处,若不思,怎生得此!”所言之“思”与“悟”,也是在讲书法作品成于“想象”而备具“意象”的道理。又,朱长文《墨池编》录雷简夫《江声帖》云:
近刺雅州,昼卧郡阁,因闻平羌江瀑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駃掀搕,髙下蹷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笔下矣。
从听到江水声,到“想象”波涛翻卷、掀搕奔逐的状态,心意因同物情,遽起作书,则波澜壮观尽出笔下。这是从“想象”、“类情”到作品备具“意象”之最为典型的例证。其他如张旭、怀素等许多唐宋名家也都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想象”与感悟,以其为学书者耳熟能详,不赘。
依笔者的体验,“想象”虽不一定尽同于自然物理,而堪与比类的生动乃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想象”可以唤起一种对应的心态,灵感也可能适时而至,对创作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同样,阅读古代书论,通解古人所用之种种“意象”,也需要很好的“想象”,以提升我们的复原能力和学术水平。

三、“想象”与书法创作
应该看到,古今书家最大的差异是知识结构和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等种种不同。古人能把笔法、点画都看成有生命的动态形势,又长于“想象”与文学修辞,所有的技术展示都可以在审美联想中进行。相形之下,今人大都凭藉经验来关注笔法、点画之佳否的自身意义,或是凭藉天资做到生动,而不知如何借助“想象”来锤炼、精纯生动并阐释生动,带有灵感与创作张力的“想象”明显地缺失。风格意识、创作意识的缺失也都与此相关。有一种见解很有意义,《宣和书谱》评李磎书法云:
大抵饱学宗儒,下笔无一点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胸次使然也。

唐人李磎博学洽闻,著述颇富,学者宗之。在古人的体验中,文理与书理相通,李磎虽不专攻书法,而以斯文美盛,能够发其意气,自然地流溢于笔墨之中,且不染尘俗,是其胸罗万有、品次高雅的缘故。又评白居易书法云“盖胸中渊著,流出笔下,便过人数等,观之者亦想见其风概云”,即是此理此证。又评张籍书法称“观夫字画凛然,其典雅斡旋处,当自与文章相表里”、评杜牧书法称“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评薛道衡书法称“文章、字画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异耳”,都是在讲长于文章著述者的书法何以亦能佳妙的道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古代书家“例能诗文” ,而诗文内积乃为学养,外发则离不开审美联想,是则由学养筑基,以“想象”称奇,而“想象”与文学“意象”的表达和书法原理相通,至为明确。也可以说,古人对书法美感的“想象”、阐释评骘和表达中的语言修辞习惯,都是来自文学修养,由艺术通感来衔接诗文与书法。我们指出古代书法批评有较强的可实践性,即包含了以文学为中介这一特点。对今人而言,文学能力的或缺不仅有碍于古代书论的解读与借鉴,也会影响书法创作中的“想象”能力,以及对“想象”之意义的认知和体验。张怀瓘《书断》自叙评论的原理是:“其触类生变,万物为象,庶乎《周易》之体也。”在种种“想象”之后,万物皆可以取之而为书法“意象”,即如《周易》的卦画可以象征、对应世间一切事物的原理一样,使作品获得生动的阐释与评说。可以说,这是古代书论中触目皆是的普遍现象,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怎样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以利于今天的书法创作。

怎样把“想象”运用到书法实践中,古人习惯用一个“悟”字,“悟”之到与不到、转化为技术、美感风格的途径和效果如何,则因人而异,难于用语言表达。例如,张旭以见公主担夫争路、闻鼓吹、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等种种“想象”和感悟而成一代草圣,其原理方法是自秘、还是不自知,他人无从晓得。陆羽《怀素别传》载其自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怀素从夏天的云峰中看到什么、又悟出什么、如何转化到书写实践中去,同样不得而知。到是“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 壁之路,一一自然”的话透出点消息:用笔的“痛快处”劲直如“飞鸟出林”、蜿蜒迅疾如同“惊蛇入草”,“ 壁”的痕迹能启发用笔贵在应势随机、任其自然。其中前者衔上文,应该出自感悟,而非一般的“意象”的表达喻说,后者是从感悟到转化为笔法的描述。又,沈作喆《论书》云:

李阳冰论书曰:“吾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沾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耳目口鼻,得喜怒惨舒之态;于虫鱼鸟兽,得屈伸飞动之理。”阳冰之于书,可谓能远取物情,所养富矣。
物情,神与物游,推扩此心,遂能于天地万象,皆有感悟,或形或理,皆能在书法上有对应的转化,如果加以“想象”,则其转化的原理不难想出一二。至于所“养”之富,既有学养,还要有“想象”和转化的经验,“字外功”才能在字内发挥作用。张怀瓘《文字论》也讲到自己的经验:“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蟉盘旋之势。探彼意象,入此规模。”意谓用笔之法的感悟和实践,劲直如擒虎豹的勇武威猛,婉转如执蛟螭而见其虬曲盘旋的态势,又以“意象”所取,虽不言力,而力尽在其中。按照这个道理探索草书之生动的本原,即能进入其中,再现其美。又,李日华《论屋漏痕》云:
又有闻嘉陵江水声而悟笔法者,悟其起伏激骤也;见舞剑器而知笔意者,得其雄拔顿挫之妙也;见担夫负重络绎而行,虽公主驺从呵禁而不能止者,以其联络成势,不可断也。
李氏的演绎是否合于古人所得,已无从得知,但他能借助艺术通感而进行再度“想象”并转化为具体的笔法,堪称善于感悟和借鉴了。

对书写中具体的技术问题,“想象”的作用也占有重要位置。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云:
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下笔之前先要“静思”,思各种点画形态和笔势,而点睛传神处在“筋脉相连”。什么是“筋脉”?在字里行间如何体现?这就需要对其可见的、不可见的有一个完整的“想象”,再使之转化而为“意”、亦即唐太宗《论书》讲的“皆先作意”,而后动笔,“筋脉”才能把点画字形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充溢着生命光彩的作品整体。《书谱》对书写技术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也有精彩的论说:
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

“凛”为取神,“温”乃妍润,“鼓”则枯劲,“和”备闲雅,这四种笔意通过“想象”,被高度提纯为“意象”和美感,而不限于顿挫方圆之类,既能原则地把握运用,又具体而微妙。其后对应的四种“意象”与美感,是书法达性抒情的四种基本元素,也是作品能够生动变化的成功条件。凡此之类,古代书论中所见甚多,不烦枚举。
今天,如何提高现有的创作水平,是书坛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笔者草成此文,希望能对思考有所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