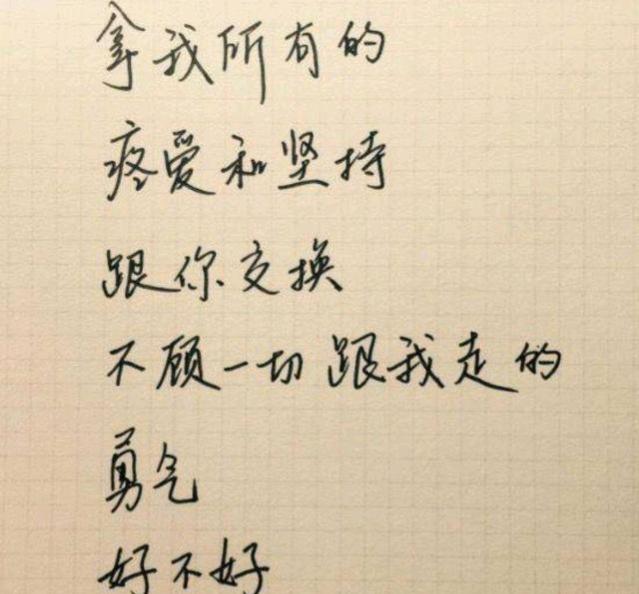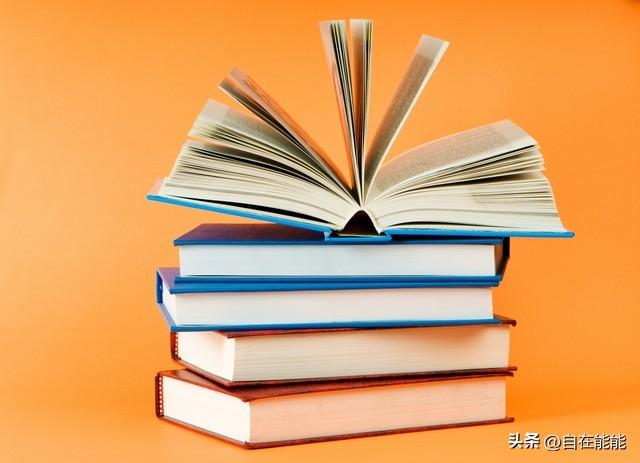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

廪君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地名新解
文/杨光华
[提 要]古代文献记载廪君巴人发源于“武落钟离山”。当代学者对“武落钟离山”这个历史地名的解释差异比较大,有的认为它是“武落山”、“钟离山”二山的合称,有的认为它的本名是“落钟山”,有的认为它在湖北清江流域,有的认为它在重庆大宁河流域。实际上,“武落钟离山”本名“武陵钟离山”,“武落”为“武陵”传写之误,“武陵”即武陵郡。“武陵钟离山”去掉郡名“武陵”,就叫做“钟离山”。这表明廪君巴人的发源地是在清江(夷水)流域而非大宁河流域。
[关键词]廪君巴人 发源地 武落钟离山 武陵钟离山
了解古代巴人历史的人,大都知道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廪君巴人”发源于“武落钟离山”。这里使用的“廪君巴人”名称,系指《后汉书》所载以廪君为首的巴郡南郡蛮。廪君是否为巴人始祖,“廪君巴人”与巴人是什么关系,最初立国于“夷城”的廪君巴人与建都于江州(重庆)的巴国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学术界争论颇大,笔者学识有限,还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想解释的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历史地名——“武落钟离山”。关于“武落钟离山”之地名和地望,当代有多位学者进行过研究,但是他们的解释差异比较大。而正确解释这个历史地名,直接关系到廪君巴人发源地的确认。笔者想谈谈个人的看法,论述中若有不妥,敬请大家指正。
一
“武落钟离山”是一个历史地名,在现存文献中以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为最早:“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代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此已上并见《代本》也)。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按照唐代李贤的注释,《后汉书》的这段文字大部分与《世本》相同,可知在宋代已失传的《世本》又是最早记载该地名的文献。此外,在范晔的《后汉书》以前,记载廪君事迹的还有东汉末应劭的《风俗通》,只是现在已不知其是否有“武落钟离山”之地名,故不赘述。
自范晔以后,在记载廪君巴人传说事迹,今日还能够看到留下“武落钟离山”地名的史籍中,比较早的有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蜀录》和唐初的《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在北宋时已散失,故清代以来学者认定明万历以后忽出之本是“伪本”,系抄录原书佚文和《晋书》等古籍而成。《晋书·载记》无真伪问题,但有学者研究指出,“《晋书·载记》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文字”。现在看来,尽管《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蜀录》未直接说明相关资料的来源,但从其有关记述与《后汉书》大体相同这一点来看,可以确定其资料的最初来源与《后汉书》相同。《后汉书》的记述比较简略,《十六国春秋》、《晋书》的记述比较详细,如《晋书》曰:“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瞫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俱出,皆争为神,于是相与以剑刺穴屋,能著者以为廪君。四姓莫着,而务相之剑悬焉。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为廪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廪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盐阳水神女子止廪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止无行。'廪君曰:`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廪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昼昏。廪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廪君乃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弗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廪君立砀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着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十六国春秋》与《晋书》对照,文字上也有出入,如《晋书》“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之句,在《十六国春秋》则是“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时,廪君死,魂魄化而为白虎,故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为祠。其后种类繁盛”。上述情况表明诸家在采用资料时并不是照搬原文,或者是采用了不同的版本。唐宋时期,不少重要的典籍继续转载了廪君巴人“出于武落钟离山”的记述,如《蛮书》、《通典》、《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古今姓氏书辩证》、《路史》、《文献通考》等。它们或采自《世本》,或采自《后汉书》、《晋书》、《十六国春秋》等,详略不等,大同小异,即便详者也未能超出今日所见之《晋书》、《十六国春秋》辑本。
二
历代史籍记录了“武落钟离山”这个地名,却没有对该地名进行解释。于是,围绕这个地名及其地望,当代学者有了种种猜测。
20世纪80年代初,张希周先生提出,武落钟离山是武落山与钟离山的合称,是今长阳县都镇湾东侧佷山及其附近几个峰峦的总称。“佷山上,有十分明显的峰峦——五落山。所谓`落',是长阳俗语,指一种量词单位,也就是`堆'和`叠'之意。五落山即五座山……佷山原名五落山,可能由此得名。`五'与`武'同音,后来就讹为`武落山'了”。“佷山东隔长杨溪有撞钟垴山,古传有鸣钟悬于其山,因其与清江北岸的州衙坪和佷山分别为江、溪所隔离,疑又称`钟离山'。这样,史家早年可能将佷山一带连同撞钟垴山总称为`武(五)落钟离山'而载于文献”。继张希周之后,张雄先生也认为武落钟离山在长阳都镇湾公社(镇),但未作地名解释。
张希周先生关于“武落钟离山”地名渊源的解释,虽被长阳县本地有关方面采用,但推测的成分比较大,因此其说提出以后不久便被黄道华先生质疑。黄先生认为以佷山作为武落钟离山,缺乏传说和文献的依据。一些文献说龙角山就是武落钟离山,以致人们把龙角山阴阳洞当作巴人发源地,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这种认识也缺乏根据。黄先生没有直接说明武落钟离山的地理位置,但指出清江上游(长阳县境内)的柘洞,有可能是被古代先民利用过的洞穴,柘洞及附近的石器时代遗存,无疑给我们探讨古代巴人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过了10年,张侯先生撰文指出,“佷山”与“武落钟离山”并非一回事。他从上古语言、土家语词的角度,对文献(包括《施南府志》、《恩施县志》)记载的历史中的地名和现实中的地名辗转解释,指出由《世本》所载土家族先祖廪君所居的“武落钟离山”派生出清江流域富有奇特联系的两组地名:一是清江上、中、下游均有的“钟离山”、“钟岭山”(或“钟灵山”);二是清江上游的“马鬃岭”、“都亭山”与清江下游的“马鬃岭”、“武钟山”、“武落中山”等。清江上游的“都亭山”就是“武落山”。“马鬃岭”(武钟山)是“都亭山”与“钟岭山”二山的首字合成,正如长阳的“武钟山”是“武落山”与“钟离山”二山首字合成一样。武落山、钟离山或其合成名称武落钟离山、武钟山,纵贯整个清江流域,是远古清江流域原始氏族活动在地名上的历史印记,是原始先民迁徙活动的地名遗存。张侯先生的观点与张希周先生的看法有相同之处,即认为武落钟离山是武落山与钟离山的合称;有不同之处,即张希周认为武落山、钟离山俱在长阳县内相距不太远的地方,而张侯先生认为武落山、钟离山或武落钟离山遍布清江流域。张侯先生的文章读起来不太好懂,一则古语今言、汉语土家语纠结在一起,叫人头晕;二则历史地名的迁移总有一个渊源,但张侯先生没有讲清楚这一点。
近几年,仍有学者在关注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宫哲兵先生连续撰文对“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进行“新考”。他批驳张希周等人的观点,认为:“将武落山理解成`五座山',又进一步解释成为佷山的五座山峰,很牵强。另外,在
1980-
1981年,长阳县进行了全县地名普查,
1982年编印了《长阳县地名志》。该志记载佷山有三个山峰而不是有五个山峰。这就令人怀疑,是不是有人为了论佷山即武落钟离山,而有意将三个山峰改成了五个山峰。将钟离山解释为`钟'被隔离,更加牵强附会。”然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多方论证了长阳都镇湾的佷山不是武落钟离山,长阳西部的柳山即难留山才是武落钟离山,柳山的榨洞是廪君所出之赤穴,虎洞是其它四姓人所出之黑穴。宫先生的研究为确定“武落钟离山”的地望提供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看法。但是,他在论证过程中使用的一条关键资料,却有错误。他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有“难留城山,县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钟离山,交施南建始界”这样的记载,实际上,这段文字出自同治年间编撰的《长阳县志》。另外,宫先生没有对“武落钟离山”这个地名进行解释,让人遗憾。
最近,周宏伟从董其祥、邓少琴、任乃强等老一代学者的“`巫诞'即`巫臷'说”中受到启示,又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说法,主要观点是:廪君巴人生活过的“夷水”不是后来的“夷水”———清江,而应是今重庆境内的长江支流大宁河;廪君巴人五姓所出的“武落钟离山”,应名“落钟山”,就是今巫溪县咸泉所在的宝山(宝源山);廪君立国的夷城是大宁河入江口的巫县故城。周先生的观点颇有颠覆性,但是存在一些疑点。周先生的论文属于鸿篇巨制,这里仅就笔者认为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希望没有曲解其文其意。
一是关于夷水。《汉书·地理志》南郡巫县下云:“夷水东至夷道入江,过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汉书·地理志》南郡夷道县下颜师古注:“应劭曰:夷水出巫,东入江。”周先生认为,古往今来的学者把这两条资料中的夷水当作清江是完全错误的。“过郡二”,指的是大宁河(古夷水、巫溪水)经过巴郡(鱼复县)、南郡(巫县),而与武陵郡无关。如果夷水是清江,就要经过武陵郡,就应该是“过郡三”。“夷道”应作“夷城”就是巫县故城,“夷水东至夷道入江”应作“夷水东至夷(道)[城]入江”。两汉时鱼复、巫二县的管辖区域不大可能远至属于武陵山区的清江上游流域。夷水又称盐水,大宁河(巫溪)也曾叫盐水,夷水产盐,大宁河(巫溪、盐水)也产盐,但是遍查清江流域诸县民国及其以前的历史文献资料,除了《水经·夷水注》中的“父老传:此泉先出盐,于今有盐气”一句好像与产盐有关,实在再找不到与产盐相关的任何记载。并且,现在的调查也发现所谓“盐泉”不具备产盐条件。因此,夷水不是清江,而是盛产泉盐的大宁河。对于这些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今巫山、巫溪所在的大宁河在汉代属于南郡的巫县,与巴郡鱼复县无关,说“过郡二”有巴郡是不妥的。西汉时,巴郡(鱼复县)、南郡(巫、夷道县)、武陵郡(佷山县)管辖区域涉及清江流域,《汉书·地理志》“过郡二”不存在理解困难的问题,应指夷水(清江)出巴郡鱼复县后,经过南郡、武陵郡。应劭说“夷水出巫”也没有问题,夷水(清江)上源也属于大巫山地区。古籍记载夷水入江,以县级政区名称“夷道”来表示其地,非常清楚。周先生却说“夷道”应作“夷城”即巫县故城(巫城),“夷水东至夷(道)[城]入江”,除了说“道、城二字汉隶形状略近”外,缺乏其他证据。对夷水“东入江”也没有解释。假如夷水是大宁河,就应该书为“南入江”,这点知识古人是应该有的。再者,以大宁河流域产盐、另名盐水从而认定其为夷水,有点牵强,否定清江曾经产盐并进而否定其为夷水,也有点武断。在泉盐分布地区,有盐泉因长期流淌的原因,或因地质构造变化的原因,出现卤水变淡或断流的情况,但是也有盐泉在长期堵塞之后因地质活动的作用而突然涌溢的现象。《宋史》记载,清江流域的长杨县“有汉流、飞鱼二盐井”。在三峡地区,过去被称为“盐井”者,多是泉盐,为储蓄涌流的盐泉,人们刨地为坑或者垒土石为坑,便成大口浅井,往往也叫做“盐井”。宋代长杨县产盐,这证明《水经·夷水注》中的“父老传:此泉先出盐,于今有盐气”之说不假。
二是关于武落钟离山。周先生既认定夷水就是大宁河,就必须要解决“武落钟离山”的问题。宋本《太平寰宇记》载:“《世本》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蜑之先落中山石穴中有二所。”《方舆胜览》载:“《系本》云:廪君之先故出巫峡落钟山石穴中。”周先生据以认为,廪君之先所出地不是叫做“武落钟离山”,而是叫做“落钟山”。武落钟离山一名,很可能是魏晋某人在编写后汉史时,因误读“巫蜑落钟山”五字而调整文字次序并改“巫”为“武”,改“蜑”为“离”所致。落钟山其实就是咸泉所在的宝山(宝源山)。不过,唐以来可能就不叫落钟山了,而被改名叫做“石钟山”。南宋时期石钟山被改名为宝山,明清叫宝源山(今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笔者的看法是,前面二书所引《世本》与《世本》诸辑本相差太大,并且《太平寰宇记》此处所引文字讹不可读,显系刻写错误。《方舆胜览》之文也属于传写错误。同本《太平寰宇记》另一处有这样的记载:“廪君种,不知何代。初有巴、樊、瞫、相、郑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所以不能认定《太平寰宇记》所记就是“落钟山”。再者,根据《后汉书》、《十六国春秋》和其它古籍之引文以及诸种《世本》辑本文字,在“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与“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之间,尚有一段文字相隔,把它们误读连缀在一起的概率应该为零。还有,宝山(宝源山)唐以前叫“落钟山”,唐以后改名叫做“石钟山”,南宋再改名为宝山之说,也仅仅是推断而已,没有提出比较可靠的证据证明“石钟山”在唐以前叫做“落钟山”,宝山(宝源山)在以前叫做“石钟山”。但是,要说“宝山”,也不是没有来历,有学者研究,《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的群巫所登之“葆山”就是后世大宁河流域巫溪县的“宝山”。
根据上述事实,笔者认为,周先生提出的廪君巴人发源地在大宁河(夷水)流域及宝源山(宝山)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看起来,学者们关于“武落钟离山”这个地名及其地望的解释,有点越说越乱的感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正确的解释是什么?
三
众所周知,地名一般由通名和专名构成。回顾汉语地名发展史,可以看到汉语地名的专名从用字构词来看,早期多为单音节地名,后来由于交流的需要和词汇的丰富,多音节的地名也就是二字、三字的地名多起来;也有四字地名,但很少。专名的命名都有所本,因而其意思大都可解。比如历史地名中有“鸟鼠同穴山”,就是四字结构专名,其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以鸟与鼠同处于一穴的自然奇观而名。“武落钟离山”,“钟离”是可以解读的,与古国中的钟离国或姓氏中的钟离氏多少有点关系,但将“武落”与“钟离”放在一起就玄了。
为了求得一个可以理解的解释,有的学者提出“武落钟离山”是“武落山”与“钟离山”二山连名或二山合称。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文献记载的山都是一山,而非二山。《后汉书》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十六国春秋》载:“昔巴郡、南(部)[郡]蛮,本(行)[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时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蛮书》载:“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黑、赤二穴……”《太平寰宇记》载:“武落中山,一名难留山,在县西北七十八里,本廪君所出处也。……盛弘之《荆州记》云:难留北有石室,可容数百人,人常于此室避难,崄不可攻,因名为难留城。”《水经注》载:“夷水自沙渠县入,水流浅狭裁得通船,东径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西面上里余得石穴……东北面又有石室,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从这些古籍中使用的“其山”,“山崩”,“独立峻绝”,“武落中山,一名难留山,在县西北七十八里”等字、词、句来看,古人所述的武落钟离山,怎么看都只是一山,而绝无二山之意。
我们将多种文献记载进行对比,不难看出在后世流传的文献中“武落钟离山”之名在书写上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两方面的:一是用同音字代替;一是省漏某字。
首先,清代以来诸位学者从各种古籍中辑录《世本》,后人收入《世本八种》。多数辑本皆作“武落钟离山”,但是秦嘉谟辑补本中作“五落钟离山”;张澍稡集补注本中有“武落钟离山”、“落中(一作钟)山”、“武罗钟离山”等写法。
其次,《北堂书钞》、《白孔六帖》、《太平广记》中写为“武洛钟离山”。
再次,《白孔六帖》又有“武落钟山”;《路史》、《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也为“武落钟山”。
又次,《方舆胜览》记为“落钟山”。
上述文献中存在的这些差异符合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代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因为音、形相近而在抄写摹刻时出现文字错误。即使在同一本书中,也有这种情况。如《太平寰宇记》一云:“武落中山,一名难留山,在县西北七十八里,本廪君所出处也。《世本》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蜑之先落中山石穴有二所,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状。廪君出于赤色,余姓亦出黑穴。”又云:“廪君种,不知何代。初有巴、樊、瞫、相、郑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两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对于前文“武落中山”、“落中山”之名,后人多能理解它们属于刻写中的错误,故在翻刻或引用该书时,直接根据后文校正为“武落钟离山”。
书籍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上述错误的存在却给我们以启示。笔者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武落钟离山”从山名而言本名“钟离山”,“武落”当为“武陵”传写之误,此“武陵”即武陵郡、武陵地区之武陵。这样说的依据何在呢?
古人著作中记载山水,往往在山水之名前冠以表示其地理归属(地望)的地名,犹如今天我们说“安徽黄山”、“四川峨眉山”之类。从行政区划沿革来看,夷水(清江)流域“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汉代分属于巴郡、南郡、武陵郡。清江中游一带的“佷山”在西汉时属武陵郡,东汉时改属南郡,习惯上清江中游一带仍被视为武陵地区的一部分。文献记述廪君所出之山所居之城,在汉代的武陵范围内,从道理上讲,古人完全有可能用政区或地域名称“武陵”来表示“钟离山”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文献中,我们也找到了直接证据。《太平御览》云:“《后汉书》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瞫音审)、相氏、郑氏。皆出于武陵钟离山。”这条资料显示,后世流传的《后汉书》之“武落钟离山”,原本应作“武陵钟离山”,但是在抄写刻印中,许多版本讹为“武落钟离山”,其它古籍亦以讹传讹。如前所述,既然“武落”在传写过程中曾经被误为“五落”、“武洛”、“武罗”等,那么“武陵”在传写的过程中被“讹读”(音讹)或“误书”(字形相近)为“武落”也是不奇怪的,这尤如《水经注》所载当时发生在清江流域的一件事:夷道县有“望州山”,“上有故城”,“登城望见一州之境,故名。俗语讹,今名武钟山”。
古代文献中,也有去掉前面的限定名称而单称“钟离山”者。《舆地纪胜》既题“武落钟离山”,又注云“按东汉巴郡、南郡蛮,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钟离”。《明一统志》云:“钟离山石穴,在府城西南境。巴蛮五姓皆出钟离。”《湖广通志》曰:“钟离山石穴,在县西南。《后汉书》巴蛮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它们也有把“钟离山”作为一山表示的意思,虽然不知其缘故,但可以说这种写法正与该历史地名的真实相吻合。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武陵钟离山”与汉代的武陵郡有关系,那么,假如《世本》也写作“武陵钟离山”,该如何解释?
如果说《世本》是纯粹的先秦典籍,那么在“钟离山”之前冠以“武陵”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世本》是记录先秦事迹的史籍,其成书时代有战国末年说、秦末汉初说、西汉说等。有学者研究指出,“《世本》乃先秦时各国史官相承所识之记录(也就是出于众人之手),秦汉二代又屡有增益,故有`燕王喜'、`汉高祖'等称谓。是以其书之成书年代,亦不必铁定为赵王迁八年以前,大抵刘向校录以后,《世本》及成专书,而再无增补(增补则以注释之方式出之)”。此说接近真实而有所保留。《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世本》,或题刘向(西汉后期)撰、宋衷(东汉末期)撰,或题宋均(东汉初期)注、王氏注、孙氏注,看起来有点复杂,实则说明《世本》定编以后,还有人进行整理,为之作注。在定编、作注时,甚至在书籍流传过程中,肯定会增补以前不曾采录的资料,难免不会发生以“注”入“本”的现象,诚如史学史专家所说“今本《世本》有后人羼入的成分”;“世本传至六朝,已大非汉时之旧本”。因此,笔者赞同《世本》中有关廪君巴人的传说是后来增补羼入的说法,否则对《世本》多所利用的成书较早的《史记》、《汉书》以及其它史籍不会只字不提。在清江流域,廪君传说产生的时间很早,由于交流的限制而长期不被中原人士了解。东汉以来,随着对武陵地区控制的深入,中原人士才接触到在土著居民中流传的有关廪君的传说,并载入史籍,包括《世本》。据雷翔研究认为,“廪君传说的最早记载,应是《风俗通》,而不是《世本》”,“魏晋时人据以补注《世本》之巴氏或巴子记载”。东晋以降,载录廪君传说的史籍多起来,如《后汉书》、《荆州记》、《荆州图》、《晋中兴书》、《十六国春秋》、《水经注》等。被收入《世本》、《后汉书》等史籍的有关廪君的传说,在民间继续流传。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长阳县西部采集到了三种有关廪君的神话传说,其中《向王天子》流传于长阳县资丘镇,《向王天子翻船》、《向王化白虎》流传于长阳县渔峡口镇。三个民间神话传说,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廪君的记载,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以同为主,它们“都是对巴人关于廪君神话传说的物化”。这个事实除了说明廪君的传说源远流长以外,也昭示了廪君巴人发源的地域。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时间角度,还是从地域角度,《世本》和《后汉书》等书一样,在载录廪君事迹,叙述五姓巴蛮发源地时,一定是以武陵来限定范围的,其最初文字应该是“武陵钟离山”。其实,《世本》和被认为出自《世本》的《后汉书》一开始就将廪君列为“巴郡南郡蛮”,已显示采录该传说资料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清江流域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甚至更晚。但文中的“武陵”与“巴郡南郡”的矛盾,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钟离山所在地区曾经属于武陵郡,习惯上被视为武陵地区的一部分。
总之,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及结论是:
(1)“武落钟离山”原本为“武陵钟离山”,是“武陵”的“钟离山”。
(2)“二山合名说”是错误的,因为“武陵钟离山”是一山而非二山。
(3)“廪君巴人夷水应为今大宁河说”是不对的,因为钟离山在武陵,在清江(夷水)流域。按照《汉书·地理志》、《世本》、《后汉书》、《水经注》等典籍的记述,夷水就是清江,廪君巴人发源地应在清江(夷水、盐水)流域。
至于“钟离山”的地望,笔者倾向于否定今长阳都镇湾的佷山说,认为应该在其西边寻找。廪君出山后先至盐阳后至夷城,其迁移路线,《后汉书》云“从夷水至盐阳”、“君乎夷城”,方向不明,而按照《十六国春秋》、《水经注》、《晋书》、《蛮书》、《通典》、《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等众多古籍所载,廪君先是率众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后复“乘土船下及夷城”,这是由西向东、顺清江而下的。关于夷城,清江中游一处典型的早期巴文化遗址——香炉石遗址发现后,一些学者结合考古资料与史籍记载,结合文献材料和地理条件进行研究,认为长阳县渔峡口镇的香炉石遗址附近是“廪君巴人”所居之夷城;此地有白虎陇,传说为廪君魂魄化为白虎之处。笔者以为此说为目前“夷城”诸说中最为可信者。以夷城为坐标,反而往西,寻找“鱼盐所出”、“盐水神女”所居之地,则渔峡口镇西“盐池温泉”(盐水、盐池河)一带应为“盐阳”所在地。据《长阳县志》记录:“该水水温常年四十二度,含盐比重高,古代一直产盐。`盐水'东下接清江半峡,长十多里,盛产淡水鱼类。”“温泉呈东西向,分别露于清江南北两岸及河中江底。其中以北岸为显,日流量达603.9吨。”按照文献记述,钟离山又在“盐阳”以西,但具体是哪座山,笔者现在还不能断定。宫哲兵的柳山说,也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5卷第4辑
文章作者:杨光华
转化/编辑:黄卿
终校:周辰
审订:伍晨嫣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