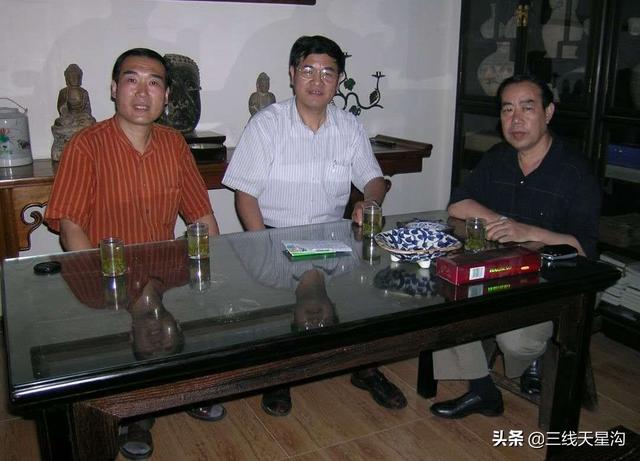陈长吟:198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美文》杂志社副主编、副社长,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陕西省散文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著有散文集《山梦水梦》《文海长吟》《山河长吟》《岁月长吟》《美文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集《风流半边街》,长篇报告文学《水调歌头》,文学理论集《散文之道》等17部。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曾获中国散文30年突出贡献奖、全国冰心散文奖等30余个奖项。
文|黎峰(陕西青年作家)
图|陈长吟
编|郭志梅(陕西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
《陈长吟在陕北采风》
水以长流乃称远,山因直上而成高黎峰:请谈谈你和一些陕西文化名家的情谊。
陈长吟:我与贾平凹交往比较多,因为在一个单位工作了20年,上下级关系,办公室两隔壁,并且一同采风下乡,爬山涉水。我喜欢摄影,光贾平凹各个时期、各种情态的照片,就拍了几百张,不少已经用在书籍插图、展览馆中。我拍照时,他很配合。他比我大几岁,我们都是陕南人,都是农家长大,都是农民进城,都少言寡语,喜欢淳朴日子,关系上也有兄弟般的感觉。就是那种农民本色的,很真诚实在的程度。他比较了解我,给予我很多帮助。我调到西安时,有一次下楼,文联党组正开会,门没关,我刚好路过,只听见平凹在房子里面说的一句话,“长吟是个实在人”。贾平凹不爱花言巧语,他这句话对我就是个肯定。我刚到西安时,一个人搬来,去他家,遇茶就喝,遇饭就吃,很自然,如乡亲,如长兄。在《美文》20年,我编的稿子他一般都认可,信任我。包括当副主编,当副社长,都是他的安排。我在西安市作协当秘书长,他是主席。作协换届时,代表名单、人事安排由我提出来,他都同意。从人格到工作都支持信任我,我们之间其实话也不多,但心意相通。
黎峰:你青年时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梦想?今天来看,你向往的生活实现了吗?
陈长吟:我对我的生活比较满意。很早就向往成为一个作家,一辈子过一种文学的生活。我学的专业都用上了,爱好与工作统一。不像现在很多大学生,工作干的不是学的专业,学的东西可能还用不上。我是散漫了大半辈子,不用天天坐班,上下班打卡,虽然有时也忙,但时间上自己掌握,不受监控,不受约束,不看别人脸色,所以自由幸福多了。我喜欢文学,把我的才华都用在了文学上,跟文学没关系的我不关心它,不在乎它。比如说人家花百十万买豪车,对我就没有诱惑力。因为我都是走路上下班,把身体也锻炼了,根本不要车。别人住高大的别墅,我并不羡慕,我有一间书房就够了。别人喜欢高新区,我嫌那不方便,没有书摊子、没有小吃店,没有老居民可以交流。我觉得财富可以有,但不要唯财是命,不要被财富所迷所困,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那些北京、上海呀豪华大都市有什么活动,我就不想参加。我愿意去边疆和民族地区,喜欢西藏的神秘通透,喜欢云南的丰富多彩,喜欢新疆的博大壮阔,还有昆明的四季如春,成都的安逸闲散。当然西安也不错,这儿的文化积淀,这儿的醇厚气息,这儿的生活习性,这儿的消费水平,让人心里踏实、不急。红柯在新疆呆了十几年,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有没有艳遇。红柯说,我都写小说去了,没那时间谈情说爱。所以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得把它用在重点上。
《陈长吟与贾平凹品茗聊文》中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原院长刘家全。
黎峰:你觉得是什么成就了今天的你?在人的成长道路上,什么是最为重要的?
陈长吟:首先要有理想,理想是动力。人这一辈子,要想做成点事情,要追逐理想,守心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还有天赋,还有勤奋,还有机遇。机遇也是最重要的,能干出大事得有机遇。陕西的作家都是勤奋的作家,但没天赋、没机遇,有的还是出不来。
黎峰:我觉得你是中国作家里一个做人做文做事三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的人。回顾这些年的经历,你有什么感慨?
陈长吟:我以前去讲课,给青年作者们说,“找准自己的路数,攒足劲儿往前走,生活总会打开更多的门”。要有目标,要相信自己,水以长流乃称远,山因直上而成高。
《水调歌头》为汉水立传,汉水文化的散文黎峰:每个作家走上文学之路都有一些偶然和必然,你的偶然和必然是什么?
陈长吟:两个影响。一个是父亲,我们回到安康,冬天晚上很冷,早早地钻进被窝,父亲就给全家人读小说,古典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粉妆楼》那些,主要是听故事,觉得很有吸引力。再一个是我的小叔,他喜欢文学,后来参军了,在部队上得到提高,复员回来后,爱写四言八句的顺口溜,常与我交流。我小学三年级也开始写顺口溜了。我们小学课本学的都是英雄故事,革命化的东西。所以,我说我们这代作家最大的麻烦在于摆脱革命化写作教条,那时提倡的都是“三突出”。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写作。
黎峰:你觉得你的创作之路还顺畅吗?我看到你早年的诗歌,看到你的散文和小说,从中能看到你的阅读量和才情都高于当时很多作家的。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创作感到满意吗?你觉得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陈长吟:还是不太满意吧。自己想写的重量级作品还没有出来。严格地说,是2009年以后才开始真正地转入专业文学。前30年一直在编杂志,做作协的秘书长等,就是具体办事的,投入到这些工作上面的精力最多,创作只是业余。现在出了17本书,长的东西少,主要是散文。散文写起来快,半天一天就能完成。长篇小说几十万字,至少得三五个月,得一气呵成,要整段的时间。虽然也写过长篇报告文学,但还用的是散文的笔法,分节写成。报告文学,写真实的事情,更多的强调社会性与时代感,对我也有好处,可以丰富生活面,认识基层社会,积累更多素材。
黎峰:我在出版部门工作,印象很深的是你的长篇报告文学《水调歌头》,这本书反响很好,当年曾经报去参加全国的“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
陈长吟:报告文学呢,其实与纪实散文是一路,就是用散文的笔法,写真实的事情,更多的强调社会性与时代感。我最早的报告文学,是1980年给一个先进人物韩元中写的,题目叫《吐不尽的银丝》。后来又写过电力、写过油田,写过邮政等。一是有责任写,朋友叫你或者上边布置,写东西是本分,服务一下有何妨。二是写报告文学,对我也有好处。最起码可以丰富生活面,认识基层社会,积累更多素材。
《我家住在汉江边》
写《水调歌头》我是费心用力了。这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写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护建设,最先想叫《一江清水送北京》,后来题目改了。我想把它写成不仅仅是一个工程的纪实。我想完成我的几个心愿。
一是为汉水立传。我是安康人,从小喝着汉江水长大,我感恩山水自然的哺育,既为它的神奇美丽而陶醉,又为它的任性泛滥而痛苦。这本书里,我写了汉江的深远历史及诱人风情,也写了汉江的地理局限及狂暴无常。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个永恒的命题,是历代人民追求的梦想,今天的汉水流域,绿色逐渐增加,碧水晶莹清亮,风景如诗似画,环境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人们热爱家园、抵御破坏的意识在觉醒,在提升,作为一个见证者,我内心充满如莲的喜悦。记录那片狭长河谷变化的过程,是喝着汉江水长大的一个作家的责任。
二是为陕南讨名分。众所周知,秦岭那边的陕南山地,山大沟深条件艰苦,长期以来,群众生活在贫穷落后的乡村。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的经济形势发生了迅猛的变化,陕南的三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市也跃跃欲试,借改革的东风大干一场,但此时,国家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上马,凡是涉及污染的工业都得停止,造纸厂关了,黄姜加工厂封了,矿山缩小了,工人下岗了。据说瀛湖底下有一个大型矿藏,但因为要保护水质不能开采。南水北调是国家决策,陕南人民应该做出奉献。关键是得不到外界的认可,在北京说起一江清水的来源,有人说是长江,有人说是丹江口水库。天津有个著名作家写文章称南水北调是“长江北上接天津”;北京有个文化名人,居然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穿黄工程”是“长江与黄河的亲密接触”,真实情况是,汉江水还没进入长江,在中游就调走了,与长江有什么关系?就是说这一江清水,百分之七十多来自陕南山区的汉江上游。为陕南讨名分,为汉水鸣不平,这也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
三是写一本有历史价值的书。我是一个散文作家,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专集,但大多数是短篇汇编,分量较轻。这一本虽然也是分段写成,但它有一股贯穿始终的内在精神和气韵。一条长长的江水,一位不倦的探行者,一支流畅的笔管,一个明亮的长镜头,本身就是连续不断的风景。但是,我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篇沉重的通讯,一则诉苦的状子,一声震耳的呐喊。我想让它多一些文化成分、多一些可读性,多一些艺术生气,再过几十年,人们读起来仍然亲切,真实可感,有迹可循。虽然是以调水工程为线索,但汉水文化是底色,这个底色是不会因时过境迁而褪色的。所以说,我没有专写工程,而是在里面大量展示了汉水流域历史渊源、地理特征、自然环境、民俗风情。自己费了很多劲。
黎峰:如果不是编辑工作占用了你更多的时间,你的文学创作成就肯定高于今天。你心里有没有感到一些遗憾?
陈长吟: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不由自己决定。每个作家的产量高低和优劣,也不能以一时来评判。创作是长跑,纵贯作家终生。我从不抱怨过去,不想重复自己,现在不会随便写,等机缘到了会潜心用力的。一直有三个长篇的素材积累和构思,等待完成。一个是汉水移民,写明清时期的创业。一个是长安往事,写老文化人品质。还有一个跟山有关,表现山民个性。就是山、水、城三部曲。写作不仅是个人情怀,也应具有深切沉厚的社会意义。
找准自己的路数,枕书待旦
《枕书待旦》
黎峰:2005年你创办全国首个中国散文研究所,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陈长吟:散文是文学一大门类,但不被重视。全国有多个诗歌、小说方面的研究所、研究室,但散文研究比较滞后,我从事散文创作以来,就深有感触。后来我接触到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觉得这所学校依托西北大学百年名校的办学理念,对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比较重视,管理体制朝气十足,就和院长刘家全先生谈了成立散文研究所的事情,很快就达成一致,使想法变成现实了。现在这还是全国唯一的散文研究所。
黎峰:接着你创办了中国散文网,应该算是全国第一大散文专业的门户网站,还成立了散文学会。你个人为什么想到要来做这些算是服务性的工作?
陈长吟:组织者会付出精力和时间,可总要有人干啊。我编散文、读散文、写散文,身在其中,这于我是一项付出了半辈子精力的事业,当然要思考,要继续下去,要做推动工作了。况且我有散文这方面的资源、优势、成果、人脉,也有能力来做这个组织者。当然最初是出于争气,不甘平庸,不受约束,要做点事情看看,后来到了文学研究所,那就是责无旁贷的工作了。
创办中国散文网就是让散文跟上时代,也为散文创作提供更便捷的途径。文学本来就不应是少数人垄断的领域,文学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而网络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廉价而快速的交流平台。2005年10月网站成立揭幕,同时召开全国首届网络散文研讨会,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王宗仁、贾平凹等名家都到会了。林非先生说:“中国散文网的开通,是全国散文领域里的一件大事。它一定会通过与广大散文爱好者互动和交流中,充分展示当前散文创作和理论的面貌,推动21世纪的散文向前迈进。”贾平凹说:“办这个网站,我觉得意义重大。网络解决了传统出版艰难的问题,没有那么多的编辑审查及设计印刷,快捷迅速,方便省力,写作人把作品随时可以发出去。我自己对上网不熟悉,但大家都来与我谈上网,我也就等于上网了。”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宗仁先生说:“我是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作家,深深感到在基层有许多好的散文作品,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中国散文网的开通,对于广大散文作家的发现,以及他们好作品的问世,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国散文网推出后,每天有一万多次的点击量,我们去看那IP地址,世界各地的读者都有。然后我们又举办了很多活动。有李若冰逝世三周年纪念会,还有翠华山笔会、太极城笔会和一些征文大赛,搞这些活动,主要是想真正为散文作家做点事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散文。
黎峰:到省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又是你人生的一个转变。这中间的缘故是什么?
陈长吟:那是2009年,冰心散文奖颁奖典礼在西安举办。很多名家都来参会。我们省社科院的杨尚勤院长去看望王宗仁老师,我也在,杨院长说要重建文学研究所,邀请我担任顾问。当时我也顺口说,那我调过去算了。杨院长说,真的吗,我正找人呢。我说,真的。杨院长说,一言为定。他当场表态,后来就真的过来了。当了几十年编辑,忙忙碌碌,换个环境,也有利于自己的写作。并且从编辑转为研究,也是文化人发展的一个趋势。人生一世,很多巧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爷爷是个风水先生,他给我留了个纸条,四句话:“运有巧拙,时有丰歉,暂守片刻,拨云见月。”他是对我的一种鼓励,还是宿命,不可知。但事实上,想想我的这些人生的转折吧,老是在心情暗淡的时候,有贵人相助。当年从安康调到西安是贾平凹,到社科院当然是杨院长了。
《插秧》
黎峰:你长期从事散文的创作和编辑工作,你怎么理解散文?
陈长吟:散文是国粹,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不管是老子、庄子、孔子,还是《尚书》、《春秋》、《史记》,大多数都是用散文的形式写的。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写作文,作文一般是散文。课本选的文学作品最多的也是散文。因为小说它来自民间故事,包括低俗语言,生活化的口语,它都可能用到。诗歌是宫廷体,适合吟诵,是抽象的,这都不太适合学生语言学习的标准。散文它是规范化的,书面汉语,字词讲究,味道很纯正,是美文,大多数人能接受,能运用。好的散文不光现在看,百十年后还能看。散文也是表达思想最直接、最明了、最真实的文体,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散文来自中国文化的传统。在中国传统中,散文是国体,几乎涵盖了书信、科举考试、便条、笔记、日记等等。如果说现当代小说家都有很多外国老师的话,散文的形态和语言则源自中国历史的根基。
黎峰:可能因为我读得少,印象中好像还没有说得出口的好散文和好作家。你觉得怎么写好散文?
陈长吟:新时期以来,散文真正成为大众文体。写的人多,但千篇一律的东西太多了,在写法上确实没有大的突破。唐宋八大家使散文灿烂起来,明清小品使散文多情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散文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但从“五四”到现在,我们散文变化基本不大。散文作家似乎都穿着老北京布鞋在走路,很少有皮鞋、凉鞋、运动鞋等敲击路面。我做编辑的时候也对山水文章、亲情文章、随笔杂感这几类稿子厌倦极了,深深感受到做编辑的痛苦。我们的背后无非就是许多年前的朱自清、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四大金刚,我们缺乏新的坐标和出轨气象。怎么写好散文,我借古人的话说“无须故作惊人笔,写出性灵品自高”。写作就是在隧道中摸索,只有坚持不懈,找到自己的路子才能重见天日。一篇散文就像一个梨子,由外皮、果肉、内核组成。有个性的语言,优美的语言,是梨子特有的光泽,外皮没有什么斑点才好,语言美,就成功了一半。散文语言要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经验,从生活中吸收营养。果肉是内容,果核是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远,就像果肉一样香甜,果核一样有品质。只有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美的梨子。
(本文为郭志梅策划,作家黎峰几年前面对面采访成文,现在读来仍有新意,受到启发。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