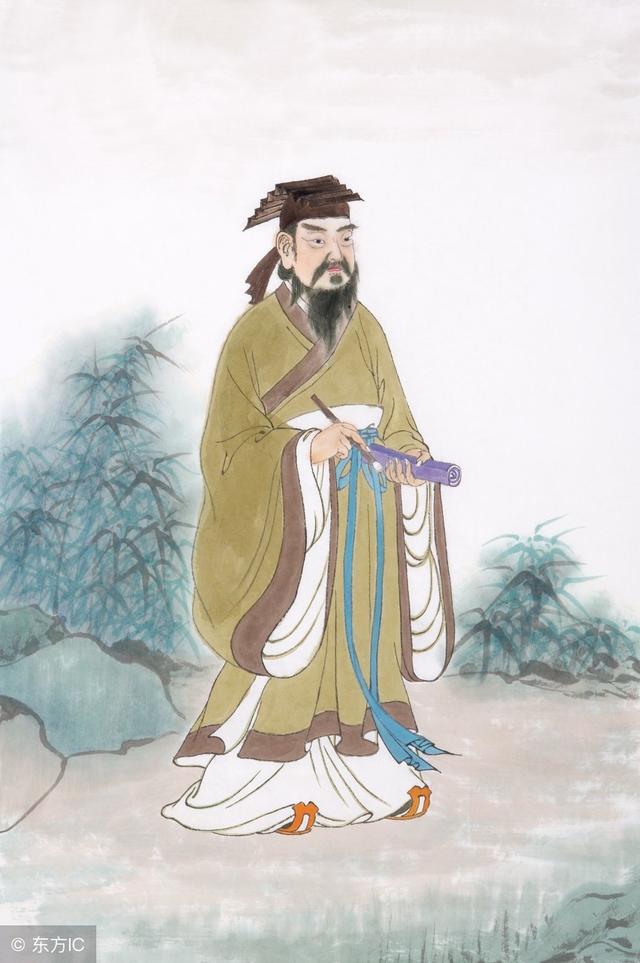北京话是满族口音的汉语?
这样的说法你多多少少会听到过——明粉们每每扼腕叹息,感慨华夏衣冠的丧失,想当然地认为,清朝掌握权力的满洲八旗军事集团,会用权力干涉口音。
满语对汉语普通话有影响吗?这不能否认。
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顺治在北京称帝之后,整个满洲八旗军事集团往南迁移,大量满洲人入关。以满语为主要用语的满洲人,开始深入学习汉语,与汉族人交往愈密,满语影响汉语是必然的。
比如,我们日常说的“挺”好。这个“挺”字,就源自满语词ten(发音)。
再比如,北方汉语常常说的胳肢窝、波棱盖、旮旯,也是来自满语词汇。
但北京话和满族口音汉语,却完全是两码事儿。

细心的朋友会注意到,我在描述八旗的时候,用的词不是满族,是满洲人。
在入关之前,满洲人的认同,就已经通过八旗制度建立起来。但满洲人,不是一个民族认同,而是一个组织认同。
八旗里不止是有女真人,还有汉军八旗、有蒙古八旗,甚至还有锡伯族、俄罗斯族的佐领入旗,我们今天新疆伊犁的俄罗斯族便有不少是俄罗斯族旗人的后裔。
而且,自明初以来,明政府就在东北设立大量卫,管理控制女真诸部,而且还对女真上层人物封官授职,并开展马市贸易。努尔哈赤的父亲和岳父,都是跟着明朝辽东总兵混的,甚至还有汉语名字。先进的汉文化进入女真地区,必然会影响到女真语(即现在的满语)。满语中巨量的汉语借词也由此来。
换句话说,在满语通过权力影响汉语之前,汉语就已经通过权力影响满语了。入关的满洲人,已经接受过汉语的熏陶了。
举个例子,我们看清宫剧都听过“福晋”的称谓,其实福晋是满语中汉语外来词,是“夫人”的音译。读读看,夫人,福晋是不是很像?
再比如,章京,是清朝的武官名,章京的读音听起来像什么?像不像将军?其实章京,就是将军的满语音译。
我们以为那是满语,其实那是汉语。

相比于满语对汉语的影响,汉语对满语对影响才是海了去了。海了去了据称来自满语。
女真人是渔猎民族,民族内还没发展出成熟的手工业和工商业,在哲学、艺术等领域建树贫乏,所以满语中除了渔猎、禽兽等词异常丰富外,其他都没有。比如努尔哈赤,其实意思是野猪皮;巴图鲁,是渔猎好手的意思。
当落后文化在学习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引入巨量的汉语词,从这些被引入的汉语词,其实就能看到满语发音与汉语发音的不同。
我们直观地感受下满语和汉语发音的区别——
顶子,汉语音应为dingzi,满语音jingse;
底子,汉语音应为dizi,满语音是dise;
煎饼,汉语音是jianbing,满语音是jempin
师傅,汉语音是shifu,满语音是sefu
馒头,汉语音是mantou,满语音是mentu
其实,满语和汉语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满语中以d居词首的词少得几乎没有,所以全部用j代替,而且满语固有的音韵中没有汉语的Z,所以全部用s代替。
比如我们刚说的福晋和夫人、章京和将军。而且满语一般是双音节,汉语是单音节,满语中就出现了许多加音节的汉语。再者,满语发音受到蒙语的影响,整个口腔内的开口相对较小,并不是北京话的抑扬顿挫。

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在天聪五年,在六部各设启心郎一员,负责满汉翻译工作。但在入关之后,启心郎满满就废除了。
为什么呢?因为满洲人汉语早已说溜了。
入关之初,满族人使用满语,作为一门外族语而学习汉语。第二代呀呀学语时仍学满语,稍一民后渐习汉语。第三代呀呀学语时已满汉兼学。第四代基本上都是“汉语嘎嘎好,满语不知道”。“嘎嘎”据说也是源自满语。
最早的满语学习书之一《清文启蒙》的问世,说明关内满人已经到了要用教材学母语的程度了。
乾隆皇帝在《满洲祭天祭神典礼》一书中说:原先满人生后儿时学语即习满语,故那时萨满能即景生情口编祷祝唱出,可是现在满人的满语皆后来所学,因而不能根据当时情形口编祷词了。
乾隆对满语很重视,甚至还搞出了一个满语骑射的民族运动,只不过乾隆本人也是靠念书学满语的。
而且这个教材也很有意思,都是用汉字来当发音提示,比如满语里一些汉语没有的音,大概在q和x之间,便用汉字“欺”、“鸡”、“稀”注音时,各加一注“咬字念”。满语里本来有鼻音,但鼻音无合适的汉字可以注音,就用“阿”“额”等代替,比如满洲人名里的索额图、穆彰阿、阿哥等等。

满语对汉语影响最大的时候,是在清朝初年,康熙年间的影响,是真正意义上对语言本身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核心驱动力,便是权力。
我们现在的常用语,比如末末拉拉、敞开、萨其马、混、拉呱、啦啦哈、爽利等等。
东北话里就更多了——哈肋巴说肩胛骨;波棱盖说膝盖;胳肢窝说腋窝;嘎拉哈说膑骨;藏猫儿说捉迷藏;还有马猴儿帽、马虎眼。甚至于我们现在特别熟悉的妞儿、屯儿,也都是满语。
著名作家萧红所写的《呼兰河传》,这个呼兰河的呼兰,也是满语,大意是烟囱,烟囱河就远没有呼兰河有诗意吧。

再就要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了。曹雪芹本人是满洲人,不过呢,他是汉族,是辽东汉人。满汉的融合在他的笔下体现得较为明显。在《红楼梦》中,很明显看出满语语法结构对汉语结构的影响。
“……有吗?”是满语式的结构,按照汉语语法结构应说成“有……吗?”的格式。这个差别来源于满语句子的谓语在后,汉语的在前。还有, “……的上头”结构的句子,即来自满语格式。
最为显著的是 “巴不得……”,比如巴不得您赶紧给我点赞,这就是来自满语的“bahaciuttut……”
其实还有许多语法、语调上的影响,但现在呢,已经不可寻了。为什么呢?被淘汰了。本文着重的参考资料:爱新觉罗·瀛生的论文里,就提出来,曹雪芹所处时代的北京话中满语痕迹还很明显,但到了清代嘉道时代,在作家燕北闲人笔下,这种满语式的汉语被淘汰,便趋近于现在的北京话了。

语言不是单向影响,而是双向影响,满语和汉语是相互影响的,这个权力也不能左右。说到底,语言的生命力,是文化的生命力。
入关前的满洲文化,相较于汉地文化,是弱势文化、落后文化。这样就注定了,满洲文化不会影响到汉地文化的基本逻辑,而只影响表现形式。
具体地说,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器物饮食等物质文化上,但不会影响到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等非物质文化。哪怕是大家都穿上长袍马褂、梳着辫子,也还是得说汉语、学习孔孟之道。
其实,去刻意地追逐语言的纯粹性是很幼稚的,因为语言的意义,是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承载。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静态的,中华文化也在历次大分大合、治乱兴衰中,不断融合,以汉族文化为主题、海纳各族文化,由此焕发出新的活力。
语言本身就是国家叙事的承载,口音的变化背后就是历史的兴衰,为何要刻舟求剑,去追求所谓的纯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