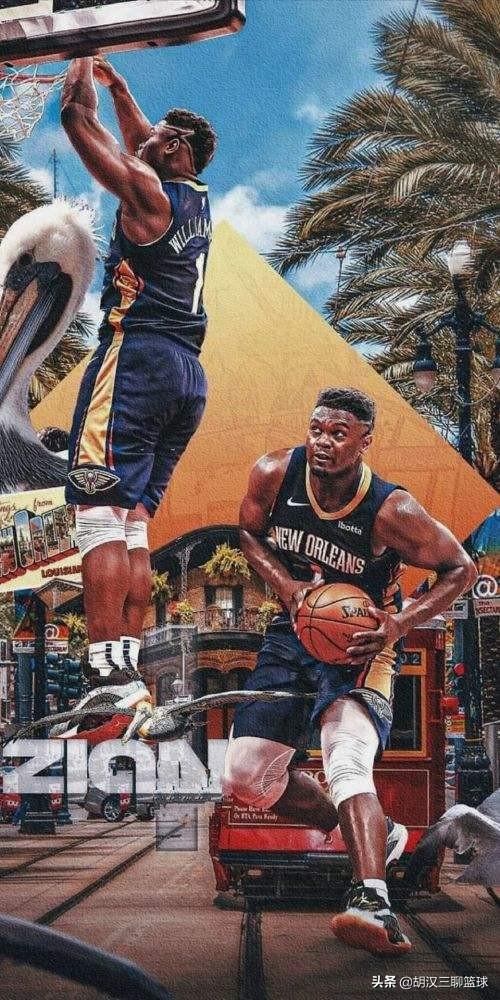上面东北丧葬民俗资料不是很详细,没有我亲身经历的具体情况,和表舅的出黑用的书里,还有父亲留下来的手抄本《黑书》里面那么细致。
我的经历中,认真注意过一些阴阳先生不同的举动。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葬礼极其简单,甚至都不能算是葬礼。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在他跟前,我在隔壁兽医院睡觉了,早晨四点多钟,叔伯三哥喊醒了我,告诉我说爷爷去世了,我马上大哭起来。有人马上警告我不许哭,因为那是封建迷信。从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到出殡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连子孙后代的哭声都没有听见,没有一个人给他磕头。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如果有磕头行为和哭叫声,将被视为搞封建迷信,后人们会受到许多牵连。但是爷爷的去世引起的社会效应,用“兴师动众”来形容一下点儿都不为过,可以说是在他之前是没有过的。那么多的熟人、陌生人,都虎视眈眈地围着院子认真地观察,哪怕有一样不合时宜的举动,就会引起来汹涌的斗争浪潮。
几十年后,我发现那些说得满吓人的规矩和习俗,在爷爷去世那么多年了以后,仿佛都失效了。首先是没有阴阳先生来出黑,没有人给扎过头纸,没有人出去报丧,没有停灵,没有人去报庙,没有人去托魂,没人戴孝,什么压口钱、倒头饭、长明灯、引魂幡、打狗干粮、打狗鞭子、盘缠钱、开光、忌属相、喊躲钉、开路引等等,一概没有,没有人指明路,没有人烧纸,没有人摔丧盆,没有人哭道,没有人打引魂幡,没有人净宅。这些当时都是一律不准许有的,哪怕有人哭一声都是犯忌的。有的只是一口哥哥憋着哭声正在油漆的三七的松木棺材,和院子外面那些“热心的”观众,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热切地关注,爷爷才走得悄无声息地,无阻无拦。
这么多年来,爷爷可能还是在他们的关注下,没有发出来一点点的信息。没有用任何方式通知家人和亲属,他在他们那里过得怎么样?缺不缺衣物和零花钱?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来告诉我们,说他的遗物没有给他火化了。
由此看来,丧葬习俗只不过是给活着的人看的,而故去的先人们根本没人在乎那些复杂的习俗。
和爷爷的葬礼相比之下,奶奶的葬礼就有一点儿模样了。因为奶奶是在农村去世的,这里的人们特别人性化,而且还是要尊重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的。
奶奶从去世到入殓的时候,我又没在身边。是因为家里的新房子的两个大山要抹一下,正好在老屯的叔伯大哥来了,他要去把屋子里的东大山墙抹好喽。父亲让我去西头老胡家取梯子。正赶上老胡家也在抹大山墙,我就在那里等了一会梯子。我拿回来梯子,走到院子大门外的时候,看见挂上了一串过头纸。我马上知道是最疼爱我的奶奶去世了。
我不顾一切地跑进院子,发现奶奶已经入殓了。灵前放着两碗饭扣在一起的倒头饭,上面插着三根短的高粱秆儿,上面缠着棉花球做的祭品。长明灯已经点燃了、摆着一个用谷草拧的小五谷粮囤,还有一个和爷爷下葬时才敢用的,两个一样的下水罐儿。那两个罐儿放到现在都是文物,那是他们老两口子在世的时候就相中的了。父亲和母亲按照他们的遗愿,给他们都放在了灵前,让他们带走了。
我跪在灵前,想起来疼爱我的爷爷悄无声息的走了,如今疼爱我的奶奶也不在了,我心里痛得很。我颤抖着点燃三炷香,痛哭流涕地磕了三个头。有人把我拉起来,去屋子里安慰安慰父亲、母亲。我也想知道奶奶去世前的情况,父亲和母亲都是泪流满面,叔伯大哥恰好来我家,他和哥哥及其他家人,按照一切能办理的习俗,把老人家安置停当了。
我永远也忘不掉,在我两周岁的时候,我天天晚上含着奶奶的奶头入睡,奶奶就那样搂着我,用她的身体暖着我,一直到我十四岁了,才让我自己睡。在我五岁多的时候,一次我让哥哥痛打了一顿,疼得我哇哇大哭,奶奶用她早就没有了奶水的奶子堵住我的嘴,直到把我哄睡着了。冬天的棉衣棉裤,都是奶奶给我捂热才让我穿。棉鞋也是她放在灶坑门口给我烤干。鞋里面的乌拉草,都是奶奶和爷爷亲手掏出来放在炕席下面炕干后,再给我絮上。我还没来得及更多的孝敬她呢,她就病重了。
在她生前,只有两件事我稍微觉得有点安慰,一件事是我刚刚干农活不久,收工回家的时候,刚进院子就听见奶奶在茅道子里呻吟。我急忙进去一看,奶奶在茅道子里弯着腰呻吟着,棉裤退下来在腿弯处,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急忙问她怎么啦?她说不出来话,用手指头指了指屁股后面。我过去一看,是奶奶拉出来一根黄瓜那么粗的、干硬的屎撅子,已经拉出来有半尺多长了,还没有完全拉下来,七十多岁的奶奶已经没有力气了。我马上扶住奶奶,用手攥着那根屎撅子。帮助奶奶排出来了,足足有一尺长,还是硬邦邦的。拉出来以后,奶奶轻松多了。奶奶不用我扶着,自己回屋子里去了。另一件事儿就是给她老人家买来了她最想吃的炉馃,让她在有生之年享用了几天。
我那个可爱的大侄子看见我回来,急忙告诉我说他太奶让人抬进棺材里去了。前院的几个女亲戚,手里拿着大卷黄烧纸,用手蒙着脸“吹着大喇叭”进院子来了。那小子才七岁,还不怎么懂事儿,把来吊丧的人礼节性的哭声说成了“吹着大喇叭”了。也难怪他,他太爷去世的时候,他在我的怀里抱着,他是唯一一个敢哭着闹着喊,让快点儿把他太爷从棺材里拿出来,太爷都冻坏了。不管怎么说,还是骨肉亲情,那么小的孩子就知道惦记老人。
这样的丧葬习俗我也是第一次经过,当时,来吊丧的人手里,一般都是拿着卷在一起的黄烧纸,走到过世老人的院子大门外以后,女性都要用手掩面,不管是真的假的也要哭几声,嘴里还有絮絮叨叨的说着“你怎么走了?”等等的怀念话语。直到灵前,通常都是磕头送行,这时候是过世的人为尊,来吊唁的人无论辈分高低、年龄大小,都要行磕头礼给过世的人送行的。
叔伯大哥告诉我,是请表舅过来给出的黑,他知道具体怎么安排而少留下遗憾。
看见叔伯哥哥,我心存疑虑?怎么那么巧?爷爷去世的时候他从老家来了,而且还是他来的当天晚上爷爷就去世了。现在还是他刚刚来一天,奶奶又去世了。是怎么回事儿?有什么事情在里面吗?但是也没有时间允许我多想啊!直到后来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多月,父亲才告诉我爷爷去世的原委,证明爷爷去世和叔伯大哥没有关系,是我多心了。
奶奶在就要去世前,父亲、母亲、哥哥和嫂子就忙活着,给奶奶穿上了父亲亲手缝制的寿衣。爷爷和奶奶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女,但是他们过继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对待他们,一点儿都不比亲生儿女差!孝敬他们两位老人,甚至都超过许多亲生儿女。
奶奶去世前有一些征兆,因为刚刚搬家到新房子,奶奶在清醒的时候住上了新房子,兴奋了几天。终于因为体力耗尽整天昏迷不醒了,醒过来的时候,总是拉着母亲的手说,她没有和母亲处够,说母亲比亲生闺女还亲。听着奶奶的断断续续的话语,我真正的知道了什么是心如刀绞,和万般无奈。
不得不想起了另一个老人家。那是我九岁那年冬天,和哥哥一起回老屯看见亲奶奶的时候,她老人家也是头朝东横躺在炕上,还不如奶奶这样断断续续地能说清楚话呢。猛然看见我,哆哆嗦嗦地伸出一只手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在我的脸上摸来摸去,又把我的脸往她的脸附近搬,想要贴贴我的脸,再亲亲我。又抬起手来,指着北面,又用手比划成一个那么大的东西,又往嘴里比划,能说出来好…好…吃的话。

图片来源于网络 梨花

图片来源于网络 梨
旁边的大娘,父亲的嫂子,老人家的大儿媳妇高声地对她说:“这回可下子看见你这两个孙子了,亲不过来了。”
又对我说:“她让你吃房后梨树上的梨,看见你们来了,她亲不够了。”
这是我第一次回到老屯,王福祥屯。是用我亲爷爷的名字叫起来的屯子。亲爷爷去世没有人和我说,也可能我还没出生吧?当时我心里想:这些人怎么看着这么不顺眼?一个个都是神叨叨的。叔伯大哥去房后的那棵几十年的老梨树上给我找剩下的梨,因为已经是冬天了,据说那是秋子梨,一年可以结三四百斤梨呢,可以留在树上冻着再摘下来吃。所以,亲奶奶看见我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吃到嘴。尽管她已经不能完整地说话了,但是她还是想看着我吃她推荐的好东西。我在她面前啃了了几口冻着的秋子梨,还行!甜甜的酸酸的。她老人家露出满意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