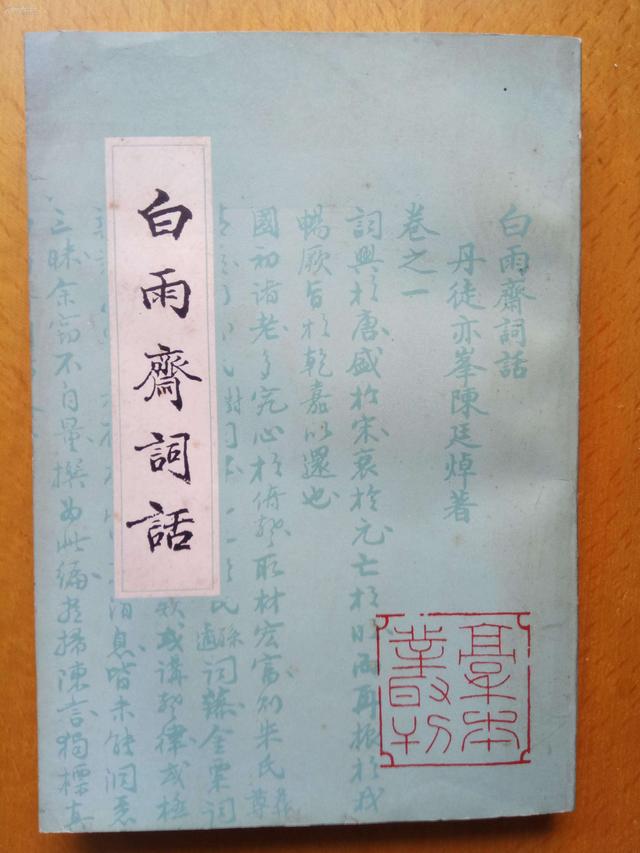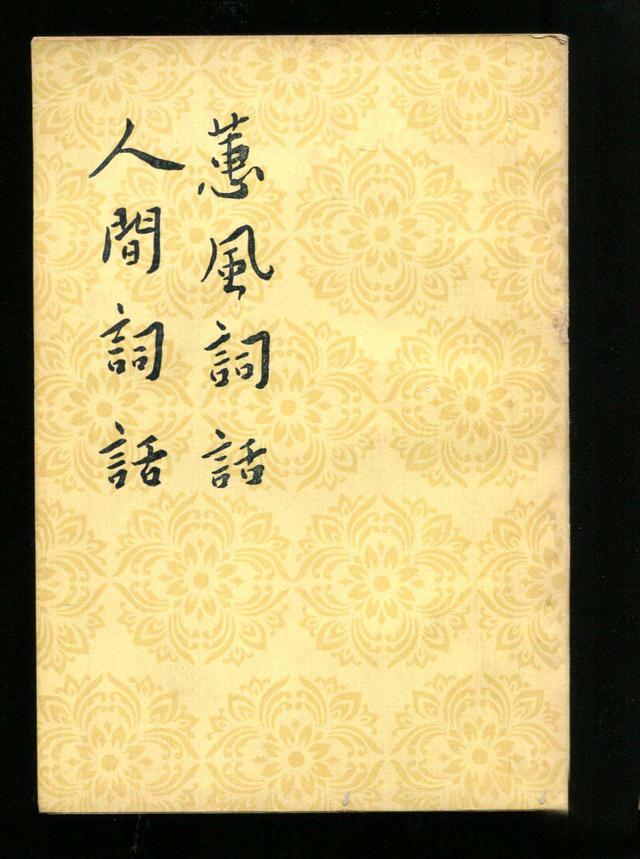《花间集》录唐、五代词500首,题材以女性生活、容貌装饰、思春怀人为主,也有少数咏史怀古、风物人情、边塞旧事的题材。风格绮靡香艳,是文人贵族用来舞筵酒席歌唱助兴之用。《花间集序》对这些风格特点与作用有清晰的描述: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文字精雕细琢,力求精艳工巧。“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这是说《花间集》作品的用处在于歌伎于筵席上按曲演唱。“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是说《花间集》的风格上承南朝靡艳的宫体。
如《花间集》的第一首词,温庭筠的《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描写一个贵族女性的化妆梳洗的日常生活,风格香艳绮靡,字句精艳。
又如《杨柳枝》:
手裹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描写女性对爱情的渴望,极尽温柔之致。“金鹦鹉”、“绣凤凰”也显示着精艳的词风。
然而,这种靡艳而缺乏思想性的的词风,在陈廷焯和况周颐眼中,却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境界。
陈廷焯、况周颐对《花间集》的论述陈廷焯论词重“沉郁,先看一下他在《白雨斋词话》中关于《花间集》的论述: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
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骚,古今之极轨也。
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
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
-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陈廷焯的几个观点:
1. 沉郁须“神余言外”,有言外之意,身世之慨可寄托于草木,而这种寄托是含蓄的,不能一语道破。
2. 他举温庭筠两首菩萨蛮作为“沉郁”的例子,又提出温庭筠《菩萨蛮》从楚骚变化而来。
3. 认为韦端己、冯正中词也是沉郁的,最后总结出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
《白雨斋词话》
再看况周颐关于《花间集》的论述:
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知此,可以读《花间集》。
花间至不易学。其蔽也,袭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谓麒麟楦也。或取前人句 意境而纡折变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为新,以纤为艳,词之风格日靡,真意尽漓,反不如国初名家本色语,或犹近于沉着、深厚也。庸讵知花间高绝,即或词学甚深,颇能闚两宋堂奥,对于花间,犹为望尘却步耶。
况周颐论词推“重、拙、大”,他又提出“穆”之一境,认为静兼厚、重、大谓之“穆”,而《花间集》符合“穆”之一境。
关于况氏“重、拙、大”的理论,可参阅笔者另一篇文章《蕙风词话:词的重、拙、大、直、方、圆》
人民文学出版社《蕙风词话/人间词话》
常州词派思想的影响“沉郁”和“重、拙、大”的共同之处,是比兴寄托:托物寄意,含蓄蕴籍,意余言外,避免直露,这就是陈廷焯所谓“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陈廷焯和况周颐学词均宗尚常州词派,因此他们继承了常州派比兴寄托的词学思想。前引之陈廷焯关于“沉郁”的论述,其实与常州派开山祖师张惠言《词选》序中的论述很相近。张氏云: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张惠言所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和陈廷焯所谓“孽子孤臣之感”是同一意思,陈廷焯称温庭筠《菩萨蛮》“全是变化楚骚”,也就是张惠言“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的意思。张氏论温庭筠《菩萨蛮》云:“此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陈廷焯也认为温庭筠“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句隐藏无限伤心。一首描写女性日常生活的毫无思想意义的靡艳之词,何以被张、况二人引申为感士不遇的伤心,甚至上升到离骚初服如此高尚的政治寄托?
这与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主张和“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有关。
其一,张惠言的词学观,首先是尊体。他的尊体,手段是复古,因此他推重唐五代词。
其二,他为达到“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目的,恪守“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又以比兴寄托作为表意的手段。
其三,张惠言以经学家的眼光来解释温庭筠词的“言外之意”,强加上政治道德的含义,有牵强附会之弊,也反映了儒家诗教对他的词学思想的影响。
图片摘自头条国风图库
“符号学”对于张氏比兴寄托的解释 对于这个问题,叶嘉莹曾以西方“符号学”理论来进行解释。她认为张惠言从“照花前后镜”四句提及的衣饰化妆之事,联想到《离骚》中关于衣饰姿容的描写。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之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等,以衣饰的洁净喻人格的高洁。因此,张惠言以比兴寄托的眼光来解释温庭筠《菩萨蛮》,自然也认为温词有所寄托。当然,这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解释。
陈廷焯又说:“作词之法......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他继承了张惠言的思想,所以自然认为《花间集》这些“变化楚骚”的词是沉郁的了。
陈廷焯还另举冯延巳为例:“冯正中词,极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也。”冯并非花间词人,他的作品表现了对世俗人生的痛苦和烦恼的挣扎和抗争,含蓄蕴藏,感慨很深,所以陈氏认为冯词沉郁顿挫,缠绵忠厚,也是符合常州词派比兴寄托和儒家诗教的思想的。
《花间集》的重与拙再看况周颐的观点。“重”和“沉郁”的意思相近,均与比兴寄托的手法有关,提倡意余言外,欲露不露,得含蓄之致。况氏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 。”这种“不自知”的寄托,正是花间及后来北宋前期词的共同特质。其时的词,作者可能并无寄托,或并非有意寄托,只是于无意中将某种情意流露其中,由于描写的意境容易引发联想,故而被读者进行引申的解释。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种词给读者的感受是细细咀嚼余味不尽,因此意厚。而《花间集》正好有这样的特点。
“拙”是手法上反对纤巧浮滑,拙则格调高古。况氏认为“诗笔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为曲折。”宁直毋曲,盖因直则古拙,曲易浮滑,所以况氏又说“或取前人句意境而纡折变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为新,以纤为艳,词之风格日靡......”他认为有些人学花间,只以刻意雕琢以求纡折变化,徒得花间之貌,其弊在于尖、纤,而全无花间古拙之致。又陆游跋《花间集》云:“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简古可爱和拙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这种简古可爱,体现在词意表达率真自然无雕琢,字句不刻意勾勒。
如《更漏子》:
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
语句自然率真,直有南朝民歌风味。由于文人士大夫对词创作的参与,词逐渐注重词句的锤炼和意境的塑造,北宋前期,这种风格已开始消失,周邦彦之后,词更注重结构章法的铺陈和词句的勾勒,这种简古可爱的特点更是不复可见。
图片摘自头条国风图库
结语陈廷焯和况周颐是常州词派后劲,虽然对于常派词学思想有所创新,但对于“比兴寄托”和“忠爱缠绵、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仍然一脉相承,所以对《花间集》的解读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解读忽视了唐、五代词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比兴寄托强加于《花间集》,实有牵强附会之嫌。然而,二人对于《花间集》靡艳外衣下的厚重与率真自然的解读是精到和有见地的,这种复古的主张,对于纠正浅浮枯陋的词风是有益的,虽然路子窄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