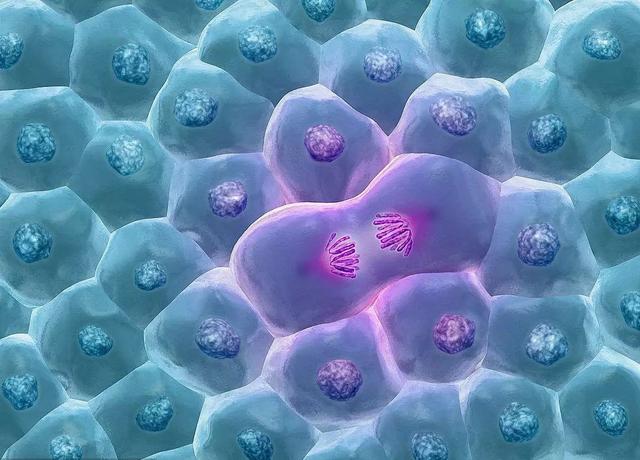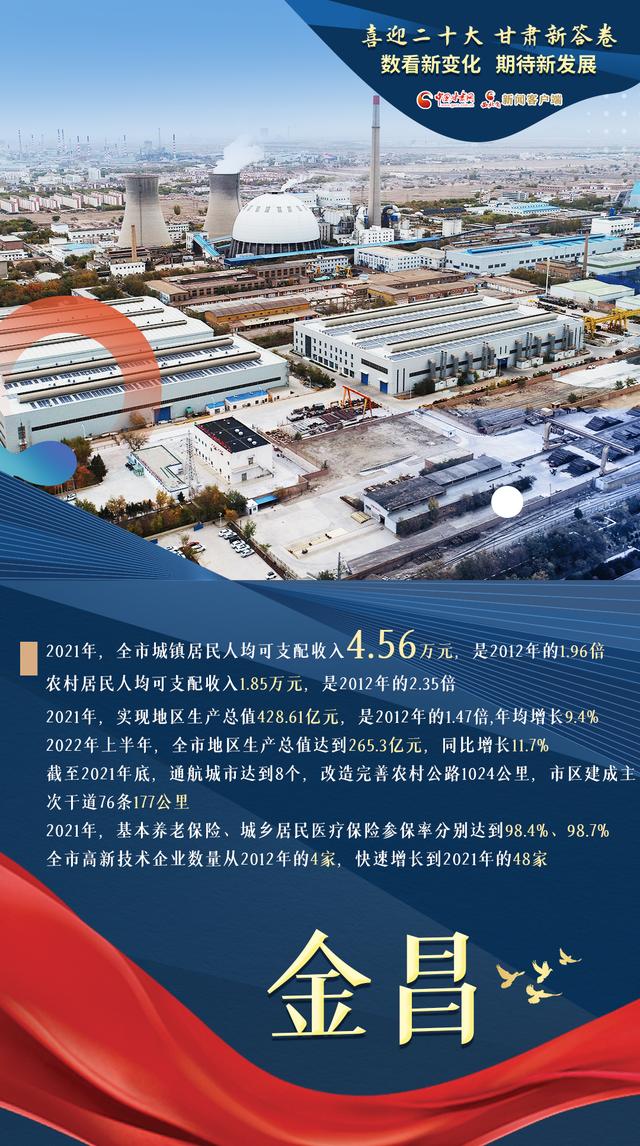每个人对故乡的情感里一定都有对特产美食的怀恋。有时移居千里之外,吃遍全球珍肴,依然会对记忆里的一种味道心心念念。
寻找田野新栏目:乡食记,将跟大家分享那些跟地方特色食物有关的故事。
本期作者简介
萧飞 男 75后 (不说70后是因为正值中年焦虑,少算一点是一点)
上海人 水瓶座 深以以上两点为荣

主业互联网传播,擅长与文字比策略,与策略比创意,与创意比逻辑,与逻辑比文字
见证过身边很多朋友牛逼地崛起,并持续仰望中 。所以他说当他的朋友是一件很有搞头的事情……
说到上海,对上海人来说,什么才是上海?
上海如今更像是一个虚妄的幻影——谈论它的人不是生活在70多年前的霞飞路,就是在近20年才蓦然醒来一般,当中的半个世纪则只有只言片语,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仿佛上海在繁华摩登之外,所有其他的元素都被选择性地遗忘。

上海繁华摩登的幻影
在关于吃这件事上,则更是如此:言必称民国,最少也得是张爱玲写的莴笋圆子;要么说的就是摩登时髦的米其林三星、空运日料和慵懒的Brunch乃至各种网红食品。
是的,上海的四大金刚会不断被提及,不过那也只是因为它们是所谓上海的标签,是上海这道菜里不得不用的吊鲜佐料。也只是佐料,没有成为过主菜,更罔论走进上海人真正的记忆里。
如果你30岁以上或更老些,是不是觉得终归缺了点什么?这个城市伴随你成长起来,那么多真实细碎的片段,却是现在所说的上海所未曾包含的。让国际的上海、风花雪月的上海留给别人去说吧,这次从回忆中挖掘一些上海市井美食,一起回溯一下,那些曾经熟悉的岁月。
夏
夏天,我总是忍不住要絮叨一下上海的夏天。这不仅因为是学生时代最长的假期,也是弄堂文化最为浓郁的时刻。
彼时,上海还没那么热,约莫3、4点左右,就有人家出来在弄堂里泼上几盆水,蒸一蒸地表的热气。不一歇,各种竹凳躺椅和木板,被光着膀子或穿着睡衣的男男女女们搬出来。空气中弥漫的是爽肤粉、花露水和皮肤的味道,弄堂风时不时吹过来一阵,惬意得很。手里的标配是半个西瓜,用一个白瓷调羹一勺勺挖着吃,一边噶三胡,一边吐得满地的籽。

弄堂纳凉
弄口是会架着一桌康乐球的,乒乒乓乓天天很晚。路灯下面围着一群半裸的汉子,哦哟册那地使劲甩牌。当半只西瓜吃完,家里会准备一碗白糖腌番茄,也有的人家端了冰镇绿豆汤出来。
只是这绿豆汤有一个麻烦,因为百合很苦,尤其在绿豆甜水里更显得苦,所以小人们会边吃边偷偷吐掉百合。倘若被大人发现了便是一顿骂,然而骂归骂,该吐的照吐不误。也有讲究的姆妈,会剥去百合上那一层薄衣,虽然绝谈不上好吃,至少也算是不苦了。

绿豆百合汤
最早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娃娃雪糕,小人们最盼望的是卖棒冰那辆28寸脚踏车,以及他啪啪击打木头箱子的声音。这种棒冰并不像如今那种硬得咯牙,也没有冰箱兴起时家制不正宗的碎冰感,它有一种很特别的酥,又不冰得冻牙,兼之有重芝麻和赤豆绿豆多种口味,很受小人的青睐。4分的价格虽然便宜,但大人们多半是不让买,说是嫌脏。

卖棒冰的自行车
不给买棒冰的大人也分,有一小半又算大方的,拿出8分让小人跻着大拖鞋去弄口国营食品店的大雪柜买8分的小雪糕,奶油味十足;若能买1毛3的大雪糕,已经算是“掼浪头”了。这两样都比不上2毛钱的鲜桔水,也就是上海话的“洗脚水”。小人们把麦管咬瘪了磨叽半天,在营业员不耐烦的眼光里还了瓶子,留舌苔上的橘黄色跑去同龄人面前炫耀。
这些年也曾被反复提起的光明冰砖,是童年系列里最贵的,但说冰砖不要忘记说刀,它们基本上算是共生关系——一般都会把冰砖带着包装用刀切了吃的,有些店还有所谓半砖卖。

光明冰砖
那时候有一种神物,叫做“冷饮水”,让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在小孩子的心里无比高大。那往往是从厂里一个带小龙头的保温桶里,用热水瓶“拷”回来的——有橘子味道,也有乌梅味道。
或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饮料的糖精调制味道很浓,然而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珍珠翡翠白玉汤”般的记忆,它代表着少年时那没心没肺的找乐时光,而且这种时光通常远离考试。
最后一个不能不提的是刨冰,某些国营小饭店,在夏天只卖两种:冷面和刨冰。小人们钟情的是后者,有大赤豆或是罐头拆的糖水橘子口味两种(若干年后多了一种菠萝)。店堂里经常拖地,头顶上黝黑的吊扇一吹,环境里就有股子水腥气。
厚扎的啤酒杯里盛着赤豆汤,带袖套的爷叔把冰一扣,嚓一下,刨冰的冰盖头就有了。奇怪的是,尽管从没有约定俗成,但所有的小囡吃刨冰都有统一的标准吃法:咯吱咯吱地先吃掉冰盖子,呼噜呼噜地后喝光那赤豆汤。
冬
和夏天相反,记忆里上海的冬天很冷。这已经不是在讨论是否穿秋裤的问题,而是在绒线裤和棉裤里做一个选择。早上是肯定不肯起床的,所以大人的终极起床技是掀被头。
那时候,脸总是皴的,泛着乡村红,手指脚趾和耳垂终免不了痒而痛的冻疮。最主要的是,太阳落得早,无论打弹子刮香烟牌子还是跳橡皮筋,歇搁的时间也相应早了很多。
然而冬天再怎么不好,过年终归是好的。平时再怎么拮据,年夜饭这一桌一定是少不了。不过那个时候,小人们的心厢总不是在吃上面,要么是想着怎么卡下压岁钱买玩具,要么急着饭后的娱乐节目:烟花炮仗。饭桌上可乐之类是绝对没有的,替代品是一种软包装橙汁,叫红宝。那一天若红宝挺吃,这顿年夜饭小人通常会吃得长久一些。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年夜饭流行起涮羊肉。于是家家户户忽然有了或大或小的铜制小涮锅,那时候乍一看就和高脚痰盂仿佛。
大人都说这是重庆火锅,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与重庆根本没什么关系,而是更接近于日式四喜锅。然而大多小人对现成碗里的并不满意,而是对那个下面加碳上面冒烟的高脚痰盂更为好奇,他们喜欢往滚汤里投料的行径,无疑这又是被禁止的。于是最多也就是夹着一片羊肉贴在锅壁,看着它由红转白,最终老得难以下口的那点乐趣。
小人们好甜食,过年的奶油大蛋糕是一定有的。以至于上海每逢过年公交车上都是晃来晃去的蛋糕,在拥挤著称的上海公交车上,那时过年被挤扁的蛋糕绝不在少。与之后盛行的人造奶油那种油腻不同,那个时候的奶油蛋糕的吃口松软、甜而不腻,记得这种是被叫做“奶白蛋糕”或“鲜奶蛋糕”的,这可能也是很多人至今钟爱红宝石小方的原因。

鲜奶蛋糕的“老式审美”
彼时都穷且省,蛋糕进出如现金流水一般,可能在走了十几家亲戚,拎过好几只奶油蛋糕后,最终只留下一只开开洋荤,吃法和刨冰一样:先奶油,后蛋糕,小人们很乐意地吃成一个丫污脸,大人们则别有心思地边追边搭讪:侬嫑跑,侬嫑跑,哎,王家姆妈,是呀一天到夜喫奶油蛋糕,还像饿死鬼投胎没喫过一样。后者心照不宣地应和,皆大欢喜。
偶尔有家里爽气,或者截留下部分的压岁钱的,就开始跑路边的新鲜玩意:烤羊肉摊。新疆人是一点汉语不会的,嘟着个舌头阿里巴巴地吆喝。羊肉量足,被疑似脚踏车钢丝磨尖的签子穿了在炭火上一烤,羊肉吱吱流油,旁边一圈小人啧啧口水长流。可能是用的煤不好,烟熏得整条街都是味道。
羊肉摊边,是支着大锅的糖炒栗子摊,锅边四喇叭录音机大声放着《一剪梅》,与夸张的锵锵炒锅声此起彼伏,老板是不大会搭理小孩子的,喜欢那油亮酥黄栗子的,多是那些阿姨娘娘。这些和炮仗、火药枪带来的硫磺味在干冷的风里混在一起,是如今依然怀念的上海年味。

糖炒栗子
除了过年,还记得每天清早6点不到天仍黑的时候,拿着牛奶卡去牛奶亭排队领牛奶。冻得搓手跳脚,就等到拿回那瓶光明(没错,又是光明,上海人有光明情节),拆了它的缠头,揭了它一轮圆月般的厚纸盖头,就在反面厚厚的奶冻上用力舔一口,奶香满口。
牛奶亭8点后基本就关张,到了下午放学,亭子边就会有一个老爷叔摆了个摊,一边是爆米花,一边唤作梅花糕。上海人对爆米花是熟悉不过,一声“响囖~”轰的一下,小人们围在旁边捂着耳朵,是又爱又怕又疯;梅花糕若用现在眼光看来,就是一个热蛋筒——在炉火上支上模具,上面一个个深锥坑:以面粉为底,豆沙为馅,上面以面封顶后加以红绿蜜饯果仁。天冷时分捧一个,好吃好拿又好保暖。

梅花糕
春
很多小人最惦记春游,到不是说那些上海市区或近郊的大小公园真有什么好玩,而是在于对于不少人来说,春游是仅有几次的可以拿零用的机会。一只傻大粗黑的面包管了饱,几毛钱的零用,就可以有难得的自主分配机会。
当春游结束,从一路挤得像难民的包车大巴上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烟纸店。老城厢的房子,很多都是那种上宽下窄的砖木老楼,下窄的那个蘑菇柄,烟纸店就开在那里。檀香桃板、拷扁橄榄,无花果……它们满满当当地堆在柜台上的斜口瓶里,隔着玻璃引诱着小孩子们。
待付了钱,店员会打开斜口瓶后面的盖子,用抄子抄出一把来,牛皮纸一兜一旋一转,一个漂亮的三角包就包成了,有嘴巴甜的,街前街后的也都认识,自然包就更大些。小人嘴巴馋,永远也学不会大人要求的慢慢噙吮,而是三口两口吃掉果肉,把个大块头核含个半天舍不得扔掉。
也有省下钱去下馆子的。所谓馆子,只是门面不大的国营点心店。1毛6分一两的生煎,底脆皮嫩,一把葱花洒进锅去,一只只汪汪地泛着油光在炉火上吱吱欢唱。铲了4只盛在破旧斑驳的搪瓷盘里(上面总是有一圈红漆大字印着店名),小心咬破表皮吮热油汤,因为有溅一身油回去挨一顿打的惨剧发生过。讲究点,就点了小笼,那档次似乎是少许高过生煎,而且每次去城隍庙看湖心亭那里永远排不完的长队,也让南翔小笼成为上海的另一个标志,身价陡增。只是小笼和生煎,肯定油腻,所以一碗双档必不可少。

生煎配双档
店里的阿姨总是很老很凶,收银的老是爱理不理,带有你对国营的所有想象。然而他们也偶尔会给你免了粮票,或是缺了几分钱时叹口气说这次算了——在那个时代,这种人情还是很值得感恩戴德一下的。
学校门口一直是个闹猛地方,上海小人在蛋饼、无花果之外,总会惦记一种融合美食与玩具的东西:秦糖。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上海人会把麦芽糖叫这么个名字,但最厉害不过的是秦糖居然是能分男女版的:对男小人,手艺人烧出红红绿绿的糖泥,加上极简单的道具,捏出各种造型——猢狲孙悟空是最常见的,其他还有十二生肖、寿桃茶壶等。
小囡拿了一炫耀二把玩,最后嚼嚼吃掉,如果不考虑手艺人那双手的卫生问题,这可谓用户体验极好的产品;女孩子当然要矜持得多,手艺人便取了两根小竹棍,一并捻了从铁皮盒里挖出一坨秦糖来。小姑娘们就接了,一手一棍顶着糖开始绕,总之每次都绕得翻天覆地绕得海枯石烂,绕到原本麦色半透明的秦糖如白奶油一样的充满质感,才恋恋不舍地吃掉。话说回来,在比较过两者后,女版秦糖的味道比碎糖片一般的男版,实在好吃了太多。

秦糖
倘若多走几步弹轧路,就可以看到街转角的油墩子摊,也是当年心水的大爱之一。那锃亮的捞模像极了一个巨大的调羹,在一口乡音的老太手里,底面、萝卜丝、覆面、入油、起锅,速度飞快而不乱,竟是有一种仪式的美感。油炸最香,风一起更是让整条街的放学孩子心绪不宁。当然最美的是有钱买一个,油纸捧在手里,呼呼吹吹,烫!
秋
把秋放在最后说,是因为小孩子们伤春悲秋这件事自小就学会了一半:伤春是不会的,悲秋是肯定的。因为,经过一个漫长的暑假,秋天开学了,换句话说,搜骨头了!
在这最后部分,说的是上海的早点。这些每天都接触的食物,你在当年说不上喜欢,或许更谈不上美味。小人多爱赖床,就多有上学来不及的苦恼。然而很多大人是不准你在路上吃早点的,因为据说会盲肠炎(其实是阑尾炎)——很多人在鬼哭狼嚎要迟到的悲愤中,被家长逼着坐下把早点吃掉,所以说起早点来多有恨意。
泡饭是最常见的,半籼米半大米的隔夜饭用水煮开,也没什么太多说头。但佐菜的就五花八门精彩得很。酱瓜和腐乳,瓶子里挖出一点异乎寻常地下饭;鸡蛋不常见,作为弥补的是高邮咸蛋和皮蛋,尤其是前者,剥光光了壳筷子挖进去,挖出亮澄澄金黄的油,随之而来的是蛋黄特有的香味——当然极咸的蛋白通常是偷偷扔掉的。肉松一定要是太仓的,在白饭的映衬下肉纤维的丝丝柔柔都在舌尖上绽放,而作为扬州酱菜的宝塔菜则是印象深刻,到不是味道如何,而是在于它的形状像极了当年热播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那架潜水艇。

早饭标配泡饭咸蛋
估计很多人已经完全忘记了与周立波所言的“乐口福”齐名的另一样神物:炒麦粉。从麦乳精罐头里倒上半碗,和上水加上糖,根据需求调整稠度,慢慢调开(易结块)。入口糯甜滑软,属于好喝又管饱的早餐选择。若是加上几块沈大成的绿豆糕、印糕和定胜糕,那更是胜似过节一样了。这种很有上海特色的糕团点心,是绝对的高档货,偶尔打打牙祭可以,平常是不大吃得到的。
四大金刚是应该在这里出现了,上海人把四大金刚的诞生地叫做:大饼摊头,其实也就是国营的糕团店。大饼是用灶烘的,一堵墙那么高,灶口处的铁架像一个简易的水车结构,三块铁板呈120°角穿在轴上,随时保证六个面中的两个对外。师傅面团一揪一揉一按一捻,按咸甜不同加料添油,撒上芝麻,一块块摊在铁板上。正反各转几次,顿时喷香。甜大饼5分,咸大饼4分,算是早点中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油条、粢饭和豆浆,和如今差别并不大,但四大金刚之名,却湮没了不少更好的美食。

早餐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豆浆、粢饭
大饼摊也是买粢饭糕和麻球的,相比大饼粢饭糕可能更合小孩子口味,如果不是很烫的话,它比大饼更容易被消灭,而且粢饭糕好吃不过的是它四个角,酥脆,和油条的蒂蒂头是有的一拼。麻球的受欢迎是因为它是有甜馅的,比起大饼的糖馅,无论黑洋沙(黑芝麻)还是豆沙馅,都要高档很多。老虎脚爪、米莹糕、脆麻花……那时的美食没什么必要上网某宝,更不要开车远行,出门几步路,街角便是。补充一点,那时候很多孩子讨厌的是青团。至于说原因么,你在心急火燎地时候吃一个冷青团试试便晓得了。
絮絮叨叨的这些,正是一个上海土著所经历过,可能很难会再有的上海味道!
真正的味道,未必会留在舌尖,甚至不在影像中。真正的味道,在记忆里,便已经足够。
就这样吧。
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寻找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