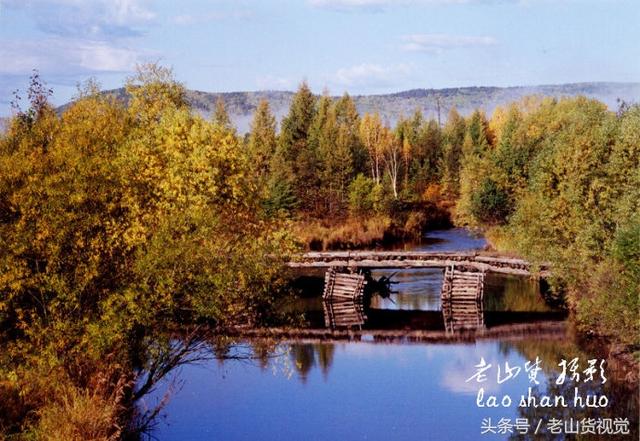一、 遍地荆棘的荒原
大家定睛一看,原来宿舍是挖地近两米深的地窝子,屋顶仅高出地面不到一米的样子,在宿舍的西端有一棵土柱子在冒烟,我和同学嘉声、毓藻、尔愉好奇地走过去,原来是早来兵团的几位天津老乡在为我们做饭。大家按照出发前已经编好的班、排顺序,拎着行李走进了自己的宿舍。地窝子中间是走道,两侧是土炕,上面铺着苇席,厚厚的一层浮土被大家抖净,纷纷铺上了行李。
一路的征尘、颠簸、劳累、终于能有一个伸腿的机会了。刚睡一会儿的工夫,老连长在外边吹起了哨子,开饭啦!第一次过上集体生活的我们,处处感到新奇,一脸盆馍馍半脸盆红烧肉,一个班的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的好香甜。听老职工说,青年们刚来,头一周随便吃,过后就实行定量制了。
从沿海到这里风干物燥,口渴难耐,到食堂打水,一锅浑浊的热水摆在大家的面前。和同班的几位同学各舀了一碗端到宿舍跟前的土台晾着,大约半小时后,再一看已成半缸子水、半缸子泥。强忍着喝去了上面的几口水,倒掉了半缸子泥。
下午时分,我走出地窝子,成片的刺草扎得两脚步履艰难,老同志告诉我们,这叫骆驼刺,那叫芨芨草,前边的一片是红柳。戈壁滩上干旱、风大、靠的是这些草树棵子来防风固沙。
入夜了,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透过屋顶的缝隙望星空,想家的念头像潮水般涌来,恨不得马上天亮,奋笔疾书跟爹妈和亲人们诉说诉说。思来想去还是报个平安吧,让家里人放心,我们来到兵团这个大家庭有领导的关怀和同学们的互助,大家好着呐。
就在这个夜深人静的当口,忽听屋外的哭声,我叫醒班长嘉声,黑灯瞎火跑出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个女生班的学生想家了,老师和连队的领导在劝慰着,几位女生面朝东方声泪俱下,叨念着心中的苦涩。是呀,在父母跟前十五六岁还是孩子,刚刚初中毕业就踏上了远离家乡六千里地的塞外边关,特别是女同学稚嫩的心难以承受哇!我想,此时远在东边的那一颗颗牵挂的心也在滴滴地流着血和思念的泪水。因为彼此地心灵是相通的。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来兵团农场一个多月了,跟来的老师和干部们该打道回府了,嘱咐的话语一茬又一茬地在我们耳边回响,“记住了,放心吧!老师,我们一定要扎根边疆,建设好边疆,为边疆献热血、献青春”。
二、河西走廊的印象
我眼中的河西走廊和理想中的模样有着天壤之别。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白花花的盐碱滩,一年四季从不下雨雪,地表结了一层厚厚的碱钙,脚踩上去嘎吱嗄吱响,东一块西一块的植被大多被沙丘所淹埋。听老同志们说,由于走廊的两侧是高耸的雪山,中间的地带便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风口,大风吹来昏天黑地的,能刮七天七夜,“风刮石头跑,姑娘不洗澡”是这里老乡们的口头禅。每当风头来的时候我们要备足水和干粮,出不去门,既是在地窝子里也要带上口罩蒙上被子,这样还呛得喘不过气来。风过之后被子上能有一公分厚的浮土。
由于这里干旱少雨,水是稀罕物,每到开春的季节,祁连山的雪水开始融化,顺着地势裹着盐碱,向疏勒河流淌,兵团的战士们从上游开始修大渠,把水引到连队,连队里挖几个涝坝池蓄满水,虽然水是苦涩的,但也是我们生存的唯一源泉。上级分配给连队的牛群、羊群也和我们共饮一池水。
因为缺水,平日只能保证饮水和简单的洗漱,洗澡没门。到了冬季用水就更难了,每天一大早上人们拿上麻袋,带上镐头在一冻到底的池子里砸冰,把干净的拣到袋子里,背回来放到桶里融化。
冬天的大西北是凄凉的,零下30多度,冻得手指头像猫咬的一样疼,唯有地窝子里烧上火墙后,才是我们御寒保暖的栖息之地。
三、垦荒的足迹
我们在连队稍做休整之后,正式开始开荒造田了,团里的机耕排开着东方红拖拉机带着四铧犁来了,机子进地之前要求我们必须把东部条田地上的红柳打干净,大家每天扛着铁锨、镐头、挖地三尺,刨出红柳的根,再用镐头把它砍断拉出地面,几天下来战果辉煌,十几马车的柴禾,拉回连队的食堂。成片成片的红柳被我们一扫而光。
拖拉机开始翻地,由于地表太干燥,顿时狼烟四起,一个班次下来,机手除了牙齿和眼晴外,其它地方都被土糊住了,成了一个土人。看上去他们干的很认真、很带劲,一股敬佩之情在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


拖拉机不仅能犁地,还能打埂子、挖渠、每当拖拉机作业完了,我们拿着铁锨在埂子上培土加固,从远处望去地成条田,渠成双。如果要鸟瞰平整后的条田,那就是一幅规范的几何图形。渠埂打好之后,开始平地,技术员拿着水平尺,一块一块地的测量。高低误差在10公分以内算是合格。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急切盼望水的到来,我们要赶在入冬前给地浇上两遍水,一是把地表的盐碱溶在水里并随着水渗到地下层,二是土地保墒,为了来年好播种。
知青来到这儿垦荒,国家是有投入的,据连长说,每开出一亩荒地上级拨给36元,这样我们不仅有了生活来源,每人每月能发29.75元的工资,还为国家扩大了耕地面积,更重要的还解决了知识青年在城里吃闲饭的难题。这在六十年代作为新生事物曾大书特书过,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大好事。知青们应当树为当年的垦荒英雄。
四、老连长
方连长当年三十七八岁,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可谓出生入死,功劳不小,现今他又转入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土战场。他人很善良宽厚,挺喜欢我们青年人的。连长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其实高升的机会很多,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他不识字更不会写字,连自己的名字写起来都困难。说起话来语无伦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有时也挺好笑的。为了鼓励我们,他说,同志们战天斗地的事迹是可歌可拉(泣)的,知识青年哈哈大笑起来,他也不以为然。
自连队每月粮食实行定量制之后,每人发一张饭卡,买一顿饭在卡上划一个勾,主食是半斤一个的馍,菜是白水煮土豆,偶尔改善伙食,做些面汤也是“三白”的,白水、白面、白汤,副食品太少,吃不上油,三五个月不见荤腥,青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上劳动量大,确实吃不饱,有的偷偷地在家里要点全国粮票到司务长那买些补助的饭票以充饥。时间长了老连长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他从附近的公社和老连队弄来一些胡萝卜、土豆、甜菜疙瘩、苤蓝,下班后让食堂蒸熟,晚上分给大家吃。他说,吃饱了不想家。
连队里农活多,特别是麦收农忙季节,就更闲不住了。我们休息大礼拜,就是十天一歇。女孩子们抓紧难得的休息天洗衣服,晾的房前屋后都是衣服、被单。男孩子懒,睡醒了几个人凑在一块打扑克、踢足球、打篮球玩。一次正赶上休息,上边下达接水的紧急任务,连长命令我们班去,军令如山倒,可是小伙子们玩的正兴,三叫两叫不出来,老连长急了上了国语,大伙这才扛起铁掀冲出地窝子,连长跟出来,性子慢腾腾的怡强火了,气势汹汹地耍起了犟脾气。连长扑来,怡强抄起铁锨一挡,锋利的锨头掀掉了连长的半拉耳朵,鲜血哗哗直流,事闹大了。团里保卫股来人,当时要抓怡强。
连长被送到县里的医院医治,他住院后惦记着怡强,直跟团里的领导说情,千万别抓他,这关系着青年人的政治生命啊。最后怡强被罚,脱了一个礼拜的大坯,连长也落下了半拉耳朵的残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