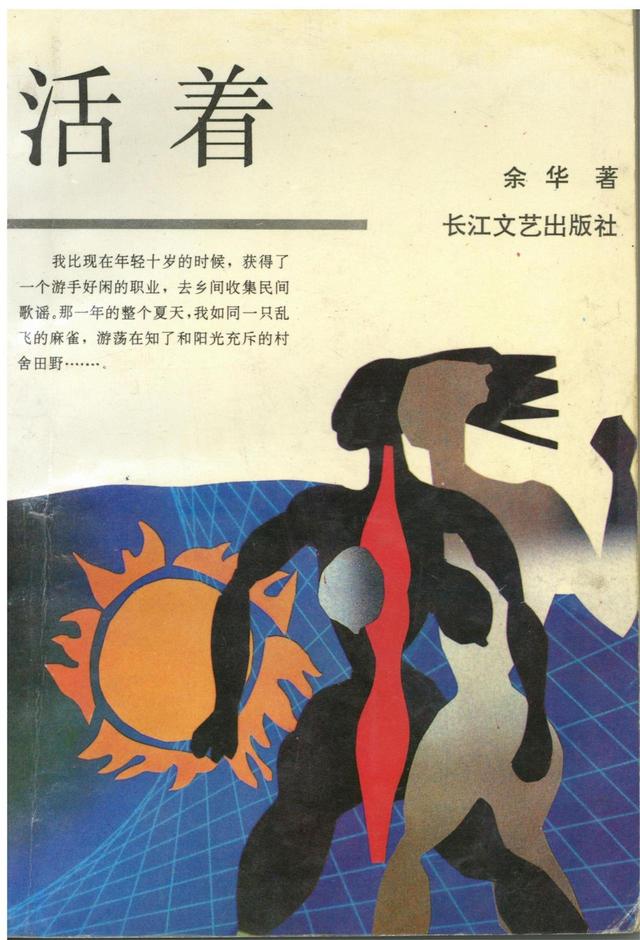蒋玉斌验看他自己缀合的甲骨原片
“屯”的甲骨文

蒋玉斌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蒋玉斌的论文对商代文字两种“屯”形的关系以及对“屯”字构形的阐释

“我的语言可能还是比较晦涩,不适合大众传播。”
接到采访邀请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蒋玉斌对记者这样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和想法。2020年春节前,他频繁接到媒体发来的采访邀请,这是一直潜心钻研的他从来没有料想过的。
这突然而来的关注度,还要从“一字值十万”的事说起。
2016年10月,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了一则“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计划”公告:破译出还没有解读过的甲骨文的,单字奖励10万元;对于尚有争议的甲骨文作出新的释义的,单字奖励5万元。
自公告发布至今的三年多来,仅有一人成功。这个人就是蒋玉斌。
2018年6月21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首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获奖名单,蒋玉斌凭论文《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获一等奖,奖金10万元。
尽管2018年就获得了这项最高奖励,但直到去年底,恰逢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时,蒋玉斌和他的破译故事才开始被大众和媒体所频繁关注。
2019年11月1日,“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不知不觉,甲骨文研究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20个年头。
对于像蒋玉斌这样的专业学者们来说,不管媒体和大众关注与否,他们始终都在自己的领域坚持着该做的事。
严谨如他,对于记者抛出的采访问题,42岁的蒋玉斌坚持用他古文字学者特有的方式来回答。他将问题梳理成书面文字,落在笔尖和纸上,最大限度避免表达上的偏差和误解。
此“蠢”非愚蠢
众所周知,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在具体使用时,又可能有不同的用法、意义。破译古文字,学术界一般称为“考释”或“释读”,就是要把不认识的文字认出来,把读不懂的文句读通。
蒋玉斌举了个例子:“古文字中的‘且’跟后世写法差不多,能辨认出来它就是‘且’,这是认字;但有时看它的上下文,例如‘先且’‘高且黄帝’,字面上完全读不通。如果知道‘且’在这里是表示祖父、祖先的‘祖’,读成‘先祖’‘高祖黄帝’,就都明白了。这就是‘读’。”
那么,他所释读出的这个甲骨文字呢?许多网友看完图片,都调侃说这像一根树枝或者飞翔的鸭子……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联想,都根本想不到这个字会跟“蠢”有什么关系。而蒋玉斌撰写的论文《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则从形、音、义多个角度对这个字第一次做出了完整的解释。
他的论文摘要是这么开头的:“殷墟卜辞数见用在作乱方国名称前的一字,旧无确释。根据细致的字形对比,该字可确认为‘屯’,主要用为蠢动之‘蠢’。”
字形是“屯”字,但释读时却成为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蠢”字。蒋玉斌进一步解释,商周时期有一些动乱、不安分的方国,需要通过征伐加以平定。那么,古书上一般怎么称呼这些方国呢?蒋玉斌说:“比如动乱的夷方,就叫‘蠢夷方’;动乱的盂方,就叫‘蠢盂方’。这样释读了甲骨文‘蠢’,顺势也就解决了西周金文的‘蠢’,像‘蠢淮夷’‘蠢猃狁’,这些都是先动乱、后被征讨的方国部族。”
这种解读一出现,文句一下子读通了,而且与先秦古书中的说法完全对应,例如《墨子》中的“蠢兹有苗”、《尚书》中的“蠢殷”、《诗经》中的“蠢尔蛮荆”、清华简《说命》的“蠢邦”等。另外,西周金文的写法稍一变化,就跟《说文解字》中列出的古文“蠢”相合。
为了让读者看得明白,蒋玉斌也尽可能用更加通俗的说法来解释:“‘蠢’本来就有‘动’的意思,古代把一些动乱、不安分的方国部族称作‘蠢邦’等。‘蠢’带有贬斥的意味,现在大家所常用的‘愚蠢’‘笨拙’等意义其实是后来发展出来的。”
蒋玉斌的论文用这样的解释方法,成功读懂了有关的甲骨文句。同时,还进一步考释了西周金文和传抄古文中的相关形体,打通了之前因为“蠢”字释读受阻而形成的理解障碍,也能解决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高了这些反映王朝与方国部族关系的材料的利用效率。
蒋玉斌这一系列的释读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环环相扣,相互验证。由此还解决了古书中一些问题。研究成果一经推出,有理有据,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认可。
“考释古文字就像捅破窗户纸”
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泰斗于省吾先生曾说,考释古文字就像捅破窗户纸。为什么偏偏是蒋玉斌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蒋玉斌认为:“不是因为我多厉害,而是自己太幸运了。”在蒋玉斌看来,破解瓶颈的关键证据往往就在偶然的一瞬间,而这个瞬间,就正巧让他碰上了。
有段时间,蒋玉斌一直卡在这个字上无法解开。他耗费了大量时间,几乎把所有相关的资料都研究了,也考虑了诸多解读上的可能性,但就是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某天,又完成了一波案头资料工作后,曙光突然出现了,几条关键证据击中了蒋玉斌,这些证据都不约而同地引导他把要考释的字形与“屯”“春”等字联系起来,最终他确认那个不认识的字形就是“屯”!甲骨文中的“蠢”字,就这样被蒋玉斌破译了。
想通了之后,蒋玉斌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大截,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论文初稿写出来了。古文字学者之间有一个惯常操作,就是把自己的文章寄给同行,请他们作评判、提意见。寄出之前,蒋玉斌已经胸有成竹,自己释读的基本观点和结论肯定是对的,因为各种证据已经自相证明。
“只要注意到那几条关键证据,对那几条证据敏感,可以说好多同行都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机会给了我,真是很幸运。古代蠢动的方国部族需要平定,现在我把这个‘蠢’解决了,当然也高兴。”对于蒋玉斌来说,枯燥、漫长并不能真正打击到他,一直没有突破才会令他沮丧。
20年求学“越难越要学”
蒋玉斌本科学的是中文。虽然中文专业学习内容宽泛,还没有细化到古文字研究方向,但对于蒋玉斌来说,这四年恰恰是特别宝贵的,也深刻影响了他在专业上的追求和学习方法。
回想起在曲阜师范大学度过的四年大学时光,蒋玉斌不无感慨:“我想至少有两点让我十分怀念,一是通过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等课程接受了很好的思维训练,锻炼了思辨能力;二是学校学风极好,踏踏实实看了一些书。”
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文字积累,蒋玉斌逐渐在广袤的中文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古汉语、古文献领域,从此与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还是大学生的蒋玉斌就明白了自己今后要走的路,他开始有意识地看古文字学的入门书籍,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占领了他的思想:“特别想知道我们中国汉字的早期面貌,而且当时有个小心思,学甲骨文不是有些难吗?但我偏是越难越要学。”
后来,蒋玉斌考上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顺理成章选择了甲骨金文文献方向,师从古文字专家董莲池教授学习古文字,主要侧重甲骨文。那时,蒋玉斌常到恩师董老师家借书,对哪本书感兴趣了就特意去找,再抱回家来读。
“董老师指导我读甲骨文原始材料,读《甲骨文合集》,大家都觉得《合集》第七册最难,因为难读,就要多方查询资料,就要看更多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既锻炼了自己,同时又意识到,所谓难读的材料,实际上也正是前人关注较少的富矿。”
由于在甲骨缀合、字体分类方面很快就有一些发现,蒋玉斌就更坚定了信心,后来又到吉林大学跟随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林沄先生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这个阶段我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有了一点基础,算是入门了,能全身心地研读古文字原始资料和研究论著。当时我所在的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学术气氛浓厚,能得到名师大咖的指导,并随时受到各种最新观点的刺激。当然其他阶段的经历也各有作用,但都赶不上这三年,时间、精力、环境俱佳。”
回想这一路走来的求学历程,蒋玉斌觉得自己走的每一步都踏实、值得。
仍有3000多已出土甲骨文字待破解
121年前,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这被普遍认为是第一次发现甲骨文。据学者统计,市面上的甲骨文字典收字4300多个,经过120年来几代研究学者不断考证,相对能够确定含义的单字只有1500个左右,有取得共识的破译字仅1300个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在已经发现并出土的甲骨文字中,仍有3000个没有被破解。
“考释甲骨文字的‘难’,根本原因在于已知信息太有限,由已知通向未知的桥梁,还有不少是隐没不明的。”蒋玉斌说,“甲骨文距今时间久远,3000多年来文字的形态和使用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而我们对当时的语言文字状况和历史文化面貌了解还很不充分,现在发现的文字材料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蒋玉斌的研究就像是在不断地打通一个又一个文化时空的桥梁。但伴随而来的,则是严肃、漫长且对于一般人而言相当枯燥的时光。
近代以来,像蒋玉斌一样致力于破译甲骨文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但甲骨文的破译工作也逐渐进入了瓶颈。简单容易的字已经被解读破译了,没能够破译的甲骨文,大多既复杂,又不成文。
蒋玉斌介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曾说,考释古文字时‘机器大量生产’比一个一个考释的‘手工制品’要高超。唐先生考释古文字讲究方法,他是一批一批的,像考释‘彗’‘帚’‘斤’等都是一连解决一大串相关文字的。百余年来,甲骨文字的整理越来越充分,有多位优秀的学者将一些考释条件成熟的文字渐次释出。但时至今日,像唐兰先生那样成批释字的成果已经很少看到了;依靠出土文献与传世古书的对读,发现新的线索,从而新释甲骨文字,这种途径的考释成果偶尔还有,但也比较少了。原因就是前面所说,面对未识字,我们获得的已知信息还不够,由已知通往未知的关系更隐秘了。”
他又举出一个例子:“甲骨文中有一个‘酉’旁加几个斜点的字,出现次数达2000次,虽然学者对它的用法、可能的读音有所了解,但一直未有确释。李学勤先生等曾多次举这个例子,希望学者能早日把它释读出来。”
苦乐全在主观的心
甲骨学需要开拓前路,需要新鲜的材料,更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输入。
除了自己的研究,蒋玉斌还同时从事教学工作,他特别强调“有兴趣”和“勤动手”两点,希望学生们把重点放在培养阅读古书、阅读古文字原始资料的能力上。
“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少不了坐冷板凳、下大功夫。如果缺乏兴趣,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耐力,在这一领域恐怕难以为继。”
蒋玉斌就是这样看待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的,只要真正感兴趣,肯下功夫并且方法得当,研读甲骨文等古文字总会有可观的成果。
“我上甲骨学课,一般会循序渐进,也会尽量调动学生的兴趣。比如我给他们讲甲骨文辞的字体分类,就先拿一些后世或当代不同人写的作品,让大家体会到字迹特征的差异,了解鉴别字迹的方法。然后再切入到甲骨文辞的字迹分析个案。通过具体操作,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观察得也很细致,这样对字体分类理论就感觉很亲近了。”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蒋玉斌非常强调学生在学习中实际动手的频率和大量翻书的习惯。只有真正熟悉原始资料,才能离真相更近一点。对此他特别举了甲骨缀合的例子。
“我自己在学习甲骨学时,需要全面搜集甲骨文资料,曾做过一些甲骨缀合工作,觉得甲骨缀合是培养动手实践能力的手段之一,我认为可把甲骨缀合当作学术训练的一种途径,培养细心、细致的作风和敏锐的感觉。”
甲骨缀合,是整理甲骨的一项重要工作,指根据甲骨图片的色泽、纹理、边缘、字迹等特征,结合骨版部位、时代、卜辞内容等信息进行复原研究的过程。
当前甲骨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黄天树先生也讲过,对于初学甲骨的研究生来说,第一片甲骨缀合很重要。蒋玉斌觉得,“甲骨缀合绝大多数很容易验证,几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旦发现缀合,很快就能知道结论,而不像是需要论证的问题,需要反复思量。这就使人马上获得成就感,欲罢不能,因此就能带着更大的积极性去阅读、研究甲骨材料。黄先生培养的学生有不少是从甲骨缀合入门的。”
他说,在甲骨缀合方面真正有心得的学者,在观察文字特征并考释文字、提炼字体特征并划分类型、注意特殊或同类现象并总结规律方面,往往也会有收获。
在采访的最后,蒋玉斌特意提到,最近国家教育部针对高考改革推出“强基计划”,遴选一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展试点,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结合高校办学特色,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等基础学科专业安排招生。古文字专业作为其中唯一的三级学科,与另外几个学科大类并列。
“这反映了国家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事业的重视和支持,我们应该乘势而上,进一步加强探索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人才的培养模式。”
甲骨学领域的同行之间常开玩笑说,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是苦中作乐,这也是蒋玉斌从业20年以来的深刻体会,他引用了梁启超的话——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在蒋玉斌的世界观里,只要有兴趣,也就没有所谓的“苦”,只有“乐”。甲骨文中待释读的字还有很多,他期待有一天更多学者能释出更多的甲骨文关键字。
文/本报记者 雷若彤
供图/蒋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