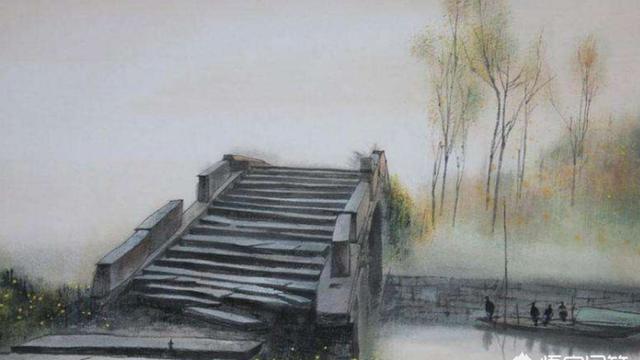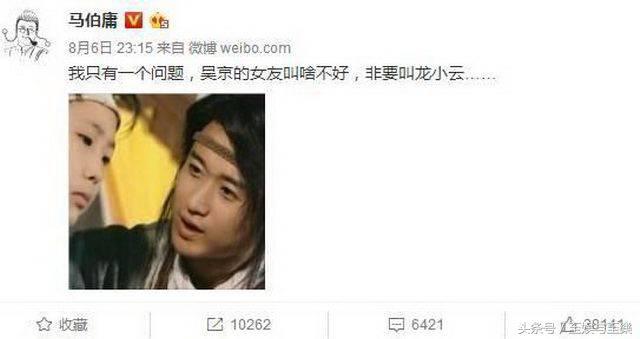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没人知道它对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一段时间里再蓬勃发展的场景,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烟消云散。回忆的重塑不可能完整,但总聊胜于无。通过碎片的拼贴,能让几十年后的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的思考方式中,又有多少来自当年的影响。迈克尔·阿泽拉德的畅销书《我们的乐队也可以成为你的生活》,记录了1981-1991年的美国独立音乐场景。他选取有13支代表性的乐队,从每一支乐队的诞生写到解散。
书很厚,没有一张插图,全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字里行间,多少年轻过的人出没于其中。阿泽拉德明确地指出,此书以故事为重。对音乐的评论穿插其间,有助鉴赏,但他更鼓励读者亲自去听那些提到或未提到的唱片,自己搜寻必要的知识,构建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我们的乐队也可以成为你的生活》
活跃在这十年音乐场景里的,尽是些朋克。蠢的朋克,聪明的朋克,凶暴的朋克,彬彬有礼的朋克,利用人往上爬的朋克,有原则爱助人的朋克,闹内讧的朋克,团结一致的朋克……原来朋克的物种那么丰富,不亚于任何一个群体。大多数朋克都没有通过它捞到个好回报,贫穷、痛苦、死亡总是离他们格外地近。只有极少数好运的朋克,如书的标题、“民兵”(Minutemen)乐队的歌词所指,把朋克变成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穿过枪林弹雨成为受人尊敬又未出卖自己的老朋克。
在这本书里,朋克不是某种音乐流派,甚至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思考和实践的指导思想。用这样高尚而洁净的语言描述这些人,就像试图用冰雕刻出臭气熏天的地下音乐场景般不可思议。读了,才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虽然也有大量场景中感官俱全的描写,但越读,它们越融入了无害的背景。朋克精神确有某种古老而高尚的遗风。它最接近堂吉诃德式的疯狂执迷,脆弱又无比坚强。
只要音乐够快够吵,就是朋克。朋克是一件方便的外衣,毛头小子突击学习一下乐器就能披它上身。它往往脱胎于无聊。人饱食无事便会无聊,一无聊就烦躁不安,想制造出让人听见的声音,最好能震得人目瞪口呆,面露痛苦的神色。
无聊是一种只要吃饱饭,任谁都可能产生的情绪。注入一点信念,无聊便会升华成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书里的众多朋克哪怕捡食物充饥,也愿意以朋克的身份继续游荡(巡演),即出自对所行之事近乎宗教般的信念。大部分穷困潦倒,开着面包车拖着疲惫身躯四处巡演的朋克们,都长期处在信念远在天边无论如何都追赶不上,原地停留又会立即被打回原型的进退两难中。信念成为必需,如同口袋里的最后一张钞票,必须紧紧握在手中。
朋克的初衷都差不多,想引人注目,于是表现得很酷,态度一致地反对主流,表态绝不加入大厂牌成为傀儡和玩偶。由于自我断绝进军主流的路径,拒绝成为摇滚明星,他们往往跌入死循环——出于无聊组建朋克乐队的,最终陷入更绝望的无聊。巡演路上,他们不断面对低智又粗暴的观众,笑面虎般的俱乐部老板,最后落得像动物园里的高等动物,无聊地在后台玩着游戏。留在本地,用心经营本地音乐社群的乐队,也难逃随着演出次数愈多,本地观众在新鲜感耗尽后再也提不起兴趣的结局。
他们到底想要追求什么?决定做个朋克的时候,很少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朋克从来不是问题的答案。它只是一种对现状的自然反应,好像饿了要吃,困了要睡一样自然发生。问题是,快意短暂,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快就会带来更多的困惑。
在1980年代的大多美国人眼里,朋克是破坏力极强,到处散布危险的火种。他们的穿着打扮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好像和光头党也没有什么区别。小孩子们在十多岁时被这种巨响的音乐迷住,在车库和朋友们捣鼓一阵子,取一个自以为很厉害的乐队名字,混到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或社会,朋克生涯便戛然而止。这是大部分人的朋克生涯轨迹。
阿泽拉德选择书写的朋克乐队们,虽然和以上的常规朋克共享一个名字,却并不是一回事。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顶着朋克的名号行事,却行使着光荣的青年使命。
“黑旗”(Black Flag)是最早提出“不喜欢系统,要自己创造系统”的朋克乐队之一。他们来自半人半怪的加州郊区暴徒之列。美国梦最后的天堂加利福尼亚,此时也被经济衰退和阶级、种族对立拉下神坛。“黑旗”亮出态度:反对以貌取人和墨守成规。言下之意是,打扮怪异的叛逆青年也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当然,也可能是狗屎。要确定,你必须亲自投入场景中才会知道。
受人尊敬的“民兵”和“黑旗”关系密切,属于朋克中最具人类美德的乐队之一。他们超级高产,写短约一分钟左右的歌来引起人的警觉。自知商业化无望(亦不想),他们还是拿出仿佛明天就将死去的态度卖力创作。舞台上,他们用行动贯彻理念,在头铁的硬核观众聚集场所演奏轻音乐、民谣、爵士……以此传递他们的信息:朋克不是一种固定的音乐模式或者一种固定的态度,“它同时也意味着自由、疯狂和个性化的艺术。在舞台上,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你的脑海里制造一点危机和喧闹。”
“民兵”的另一个信念对同辈及后世的影响更大。他们在地下音乐网络尚不发达的年代,提出“自己动手”才是朋克音乐的精神本质。口号的实际操作比喊出来困难千百倍。在“雷蒙斯”(Ramones)、“电视”(Television)、“性手枪”(Sex Pistols)、“冲撞”(The Clash)等大牌朋克乐队已经签约大厂牌,除了音乐万事不用操心的时代,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兼顾白天的工作和晚上的演出,自己动手完成一切乐队相关工作。他们的理想主义火焰之炽热,甚至想用自己的经历鼓舞其他工人,告诉他们艺术也可以来自这样的生活,只要一点点天分和很多勤奋……
他们不停歇地演出、争论、帮助别的乐队。在颓势初显之际,创始成员丹尼斯·布恩车祸身亡,“民兵”以“朋克乐队也值得人尊敬”的开创性被人记住。
在很多方面,“缅甸使团”(Mission of Burma)都与“民兵”相似。两支乐队都具有克制、苦修的气质,都出现在地下音乐网络还未建立的八零年代早期。“缅甸使团”崇尚朋克的极简主义,提倡用最少的乐器发挥成员最大的创造力,磁带循环带来现代主义的气息和智性魅力。他们的噪音和艺术气息超前于时代,或至少领先于当时的硬核音乐场景,并以此为光荣。
他们支持本地场景,“我们不是地方主义者,但你得支持在你身边成长的事物。”在波士顿时,“缅甸使团”坚持邀请本地乐队担任暖场嘉宾。他们尽力帮助别人,为培养观众不遗余力,到了一天演两场(下午场针对未成年观众)的程度,最终折损了他们在本地的吸引力。
若以上内容让你产生朋克乐队都很高尚的印象,也是有失偏颇的。有的乐队虽然信奉自己动手的朋克精神,却摇身一变成了投机者。来自化外之地德克萨斯州的Butthole Surfers像一支畸形马戏团,专好在舞台上播放令人闻风丧胆的影像。像“胡斯克·杜”(Hüsker Dü)、“替代品”(The Replacements)这样无比真诚,具有经典摇滚乐倾向的朋克乐队极易遭受厄运。照此标准,Butthole Surfers属于很难被厄运相中的乐队。在外形和自大方面,他们是典型的朋克。开着面包车三餐无着落的巡演生涯,也和当时美国的绝大多数朋克保持同步。但他们时刻准备着签约大厂牌,自己动手并非为了给自己赋权,创造适于生存的环境,而是为了签约大厂牌。他们主动背叛了远离主流、保持独立的朋克精神,不愿永居幽冥的地下。
“面对恐惧,哈哈大笑”,硬核观众很吃这一套。吉布森·海恩斯大闹荷兰音乐节,赤身裸体奔跑、打人、被揍的真人秀加深了他们的传奇。不管在地球的哪个角落,赤身裸体在音乐节、演唱会上奔跑的艺人总会被人传颂。最终冲浪手们利用传奇达到目的——进入大公司,躲过了同行痛苦、贫穷和死亡的命运。



“音速青年”乐队
在纽约和欧洲受到追捧,不仅免于被吞噬,还迫使人们把朋克当作严肃艺术看待的“音速青年”(Sonic Youth)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们始终勤奋努力,从不浪掷生命。这支乐队的成员非常擅长与人打交道,活跃在纽约的各个艺术场景,打通了摇滚和艺术圈,从下流跻身上流。
从上世纪70年代持续至80年代的纽约朋克浪潮人员更迭迅速。乐队们快速走完成立—解散的生命周期循环。如过江之鲫的朋克中,粗鲁狂野的多,时髦又酷的少之又少。“音速青年”有一套自己的做事法则,被视为时髦又酷的典范。他们重视声音和结构,而不是和弦、进程之类的东西。无论如何热衷于用吉他做声音实验,把吉他织体当作雕塑的对象,不改“用一把声音很大的电吉他猛弹的永恒魅力”。他们不仅创造新的声音,还有能力用更成熟、更发人深省的方式表达美国快乐文化下的阴暗面。
“音速青年”诠释了时髦与酷的含义。时髦是始终和新鲜事物保持联系,不断满足纯粹的学习欲望,从不固步自封。酷是职业生涯中从未做过过河拆桥的事(行内奇迹),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其他的乐队和音乐人(包括过去和现在的)。这两点让他们挺过八零和九零年代,成为实际上的社群领袖,却从未老朽。主创瑟斯顿·摩尔和金·戈登由乐队伙伴结成夫妻,为乐队提供长期稳定的成员关系。这支乐队一直到2011年两人离婚后才解散。后来戈登指责摩尔的不成熟导致婚姻失败,“他无法摆脱做明星的梦幻感”,这是后话。
如果要在书里选一支最接近今天我们价值观的乐队,无疑是弗格齐(Fugazi)。在音乐急起急停,自己动手,支持社群,远离主流的方面,弗格齐是八零年代早期“黑旗”“民兵”的继承者。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发展出自己的做事方法。他们从不放弃在音乐场景观察、干预和输出价值观的权利。如果讨厌某些观众跳粗暴的推撞舞,他们会停下音乐制止,或邀请被打扰到的其他观众上台,自己则走下舞台,让跳推撞舞的家伙围着他们跳起和平的圆圈舞。
他们被奉为正直的堡垒,在年轻时就摸索出删繁就简的做事原则。不合意的演出、邀请、合作一律拒绝,接受的才能够全力以赴。他们节约资源,用省下的钱回馈歌迷,尽量回复歌迷的来信。他们不断思考:我继承了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要抛弃什么,想要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思考的结果都会体现在音乐里。
弗格齐的票价十年如一日保持在十美元,乐队精神体现在一句歌词里:“工具,它们会改变。但我们不会被打败。”(《KYEO》)这是一支集高效、自立、善意、自省、坚定为一身的乐队,如果能以这支乐队为生活,一定能生活得更好一些。
虽然这样说很不酷,但这本音乐书真的很治愈。它把硬核音乐里冒犯人的部分用文字去掉火气,将精神的部分凝炼成佳肴供读者享用。它拨开灰堆,把赤红的初衷呈现;那些面孔上沾满灰的朋克们,早已经退场。
这是隔着时间隧道才能看见的景象,是隧道尽头的一洞光明。既然已经不可能穿过隧道看见全景,那么有一星半点的光也是好的。借它想象黑暗时,黑暗亦仿佛被驱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