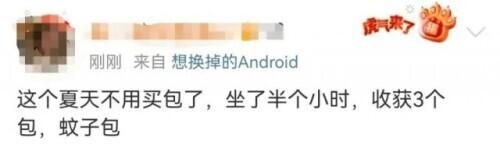作者:黄恩鹏
张敏华与我,都是首届全国散文诗笔会的成员。20世纪90年代,我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刊读到他的作品,语言精致,喻象灵动,思想厚重。在张敏华新近出版的《风从身后抱住我》(漓江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的散文诗集里,完美地体现了他30余年来的写作水准。
纵观张敏华的散文诗文本写作境界,大致应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小见大”的生命精神之氤氲感;二是浑化无迹的隐喻如天籁响彻,闻其声而不见其踪;三是自然生成的审美,物我为一而臻极化境。
“以小见大”的生命精神之氤氲感
《感觉》只有59个字,短而有力。“火车驶入隧道,我走进梦想的场景。车窗外,许多岩石一样坚硬的情节,暗淡地闪过。经历了从黑暗到黎明,谁还会轻易地遗忘漫长?”火车、隧道、岩石、黑暗、黎明,有如特朗斯特罗姆的密集意象,人生的急促感与生命的历史感,诸多“冷的”意象,顿悟了时间之苍远、人世诸事的沧桑与茫然。
《无常》82个字:“晨钟唤醒草木,蟋蟀替代耳鸣,风和叶谈论离别与生死,鸟换取无常的天空。餐风饮露,一个倥偬的身影。回首,山峦浮脉——牛羊放归南山。寥廓夜空,一场雨夹雪融化生与死的界限。”以“自然图景”求证人类的生命图景。无常,是无常世界的无常,是展开了的现实的人类世界图景。
张敏华的文本语言,轻小却是厚重,微小却是宏观。心性虚空,澄怀味象,盛装万象。文本理念透明,即由物变观人变,析出生命存在之理。如《晚年》:
他坐在一把旧藤椅上,翻找着字典中孤僻的生词。冬天的阳光格外温暖,记忆松弛了。”
“时间差点要了我的命。”他喃喃低语:“这里——距离生死还有多远?”他依然恋爱、写作、旅游——回春之力来自自然。
他不停地喝着茶水,渴望在体内有一座茶园,有一个湖泊。但现在他吞下一粒止痛片,咬紧牙疼的腮帮,转过身来。
伍尔夫式的思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主体对于物性的“敞亮”,广远精微,毫无滞碍。运用小说笔法于诗句是一大特点,便有了散文诗文本重要的“叙事性”的存在。有了叙事性,便有文本自由言说的可能。否则,无法厘清文本所要表达的意蕴。
“小中见大”是散文诗文本前瞻而又严苛的创作理念。“小中见大”到底写什么、怎么写?是当下诗坛众家必须思考的。“小中见大”是手段,写什么,则是独立课题。
浑化无迹的隐喻如天籁响彻,闻其声而不见其踪
《废墟中的猫》是寓言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隐喻文本。以荒诞的言说、现代意识的植入,让文本充盈力度。“废墟中的猫,过着隐秘的生活。在白天,它屏住呼吸看着行人,它的毛色黑白相间,它在干涸的下水道里藏身,它对拆迁生活的关注,胜过我。”面具、钟表、错乱了的时间,“日子像数字一样,被搬走了梯子。”猫跟在“一群聋人”的后面,听“一位患了绝症的人的忠告”黑与白的辩证、文明的悖论、无处藏身的生活。
存在主义认为,荒诞是“人”的基本处境和悖谬的存在,既有个体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人根据自己的利益,界定精神处境。动物也一样,现实受挫、生存无意义、西绪弗斯的悲怆、无法言说的苦难。历史本位与变化,进一步将之推回到“原罪”,从而使之感觉没有出路,陷入了茫然的无聊与虚幻。猫,是一个隐喻,荒诞现实中的孤独的流放者。诗人努力创造一种精神图像:西绪弗斯式的悲剧。诗人喻说的是灵魂皈依的存在却又无处皈依。因为到处是废墟。“清静之梦”终将受到冷落和拒绝。这是宿命。自我拯救,是否拯救无望?文本的喻象是猫,但无异“人”的变形,卡夫卡式的甲虫变形。
《雪》喻示生命,墓地与雪,生命的联类,人生的经历如同雪泥鸿爪的茫然。“高贵或低贱,富有或贫穷,被同一场雪所爱,雪成为某种化身。”“雪”是事物消逝、肉体死亡、灵魂超生的喻象。雪变成水,形骸消亡,灵魂却在。这里所说的“雪”,是指过往了的或正在进行的时间形骸。感伤情绪突兀,带着疑问,对自己,更是对别人。诗人为何如此这般?原来是看见了自己的时光,有如雪。反向喻指,转瞬之间,离开大地。死亡之姿,都将呈现,酷烈、促急。雪最终会被风吹走被太阳晒干,最终回归大地。暗喻了生命终将衰亡,灵魂却是不朽。
人类寻找灵魂家园的过程,其实也是人文精神回归的过程。那种沃尔科特似的把“精神意蕴”放在历史的沧桑中来认识。或者说,从时光的流逝中,追寻到什么,才会让诗性放射出光亮的诗人是痛楚的。文本中的悲痛与玄思、愤怒与讽刺,妙想与感受联类,很大程度,是由诗人确立的历史感决定的。个人的心灵史决定历史感的深浅,历史感是诗人对于时代整体的把握和考量。历史感为诗的个体经验提供了可以精神依附的力量。历史感就是一种沧桑感。但需要写的巧妙、灵动、风趣和厚重。如《端午》:
一条大江的孤独,屈原知道;一方水土的忧郁,伍子胥知道。人生不过百年,但他俩已活了千年。
两只粽子,放在两只瓷碗里,碗与碗之间的距离,就是伍子胥到屈原的距离。
昨夜两次醒来:一次惊梦,为伍子胥;一次惊魂,为屈原。
不写泗泪滂沱,不写青铜悲鸣,不写魂洒江海,而是不露声色地,将不同历史时空的人物,相互联类,相互走近又相互剥离。灵魂之思与时间之维绾结一处。“剧场”效应明显,而叙事性与诗性的巧妙结合,则让作品立体而有强劲力量。
再如《堆积》中的世相本态、《匮乏》中的虚实之辨,都是造化相通,托诸本体意义指向走向哲学辩证,从而揭示内心:为道出思想,需要怎样的努力过程,喻示人生艰难的抵进。卡夫卡式的人之异化为“甲虫”,在“被时代”里,是怎样的生命存在?
“风”系列灵动巧思。“风从背后抱住我,我仿佛披上了卑微的袈裟”。他把“风”运用到了极致。风,或是清风,或是大风。是《列子》背负青天而飞之风。是《庄子》大块噫气万窍怒号之风。是宋玉“不择高低贵贱高下而加焉”之风。风,不单单是自然之象,它吹起的是寒潭的翅影、斑驳的征袍和沧桑的旗旌。风吹在了诗人身上,便是一种随形化迹的生命精神。
张敏华还有许多“边地地理”的文本作品:《昆仑山口:风从身后抱住我》《德令哈:太多的传说让人怀想》《雅丹:风蚀的倒影沉入云端》《克鲁克湖:鱼与人性呼应》《茶卡盐湖:一面返照的镜子》《夜晚登望海楼,想起唐朝诗人张又新》等,这些独特的边地地理,最是让诗家兴奋,因为会决然有别于一些同质化的作品。
从诸多文本的总体策略来说,张敏华走的一直是“小中见大”的路子,语言干净,意蕴深刻,不拖泥带水,设置语言张力和弹性以给读者思考的空间。他的文本多样,手法多样,思想立体。他以陌生化的语言隐喻,将主客融为一体,从而让他的散文诗文本独特又有厚重感。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