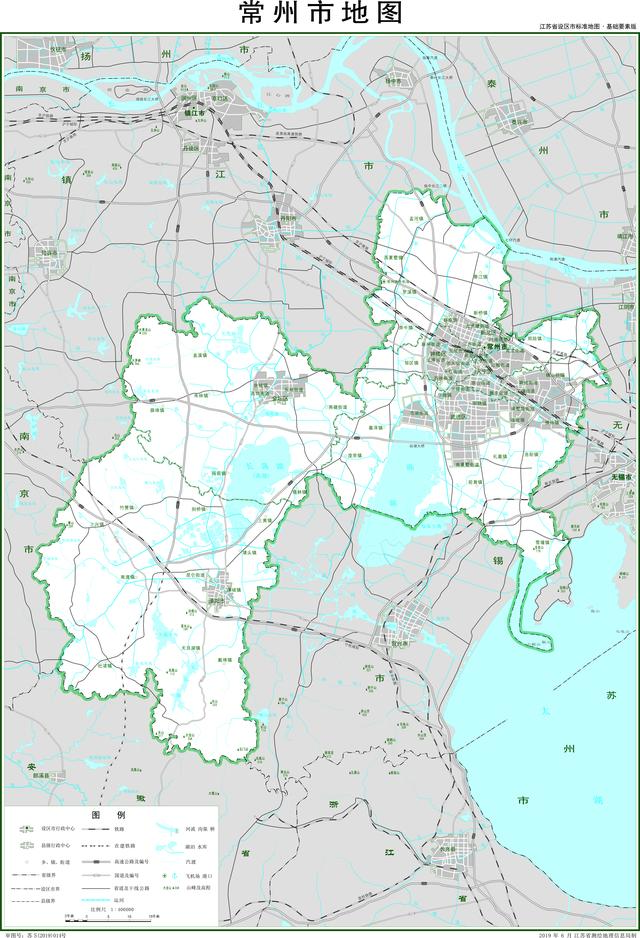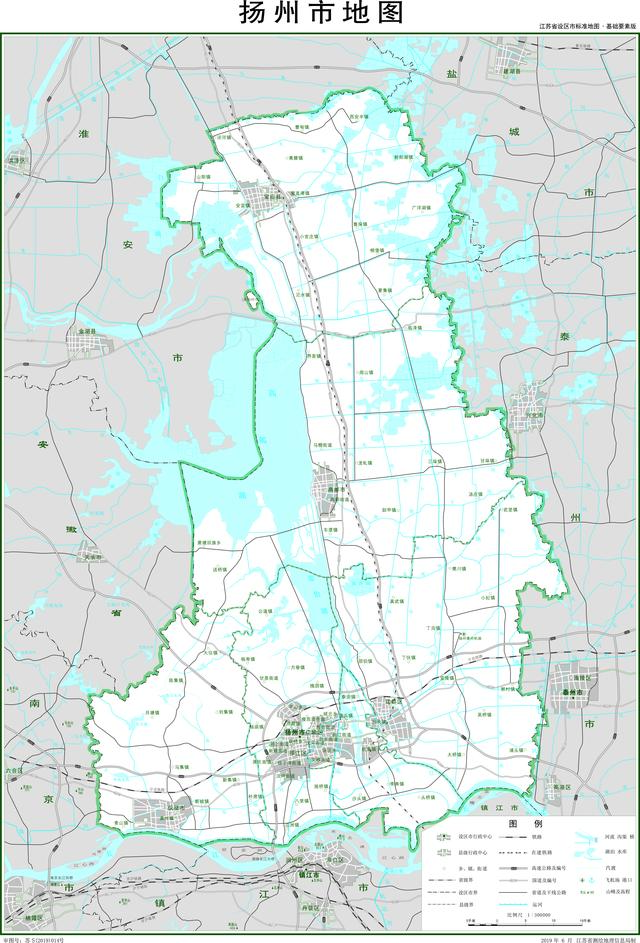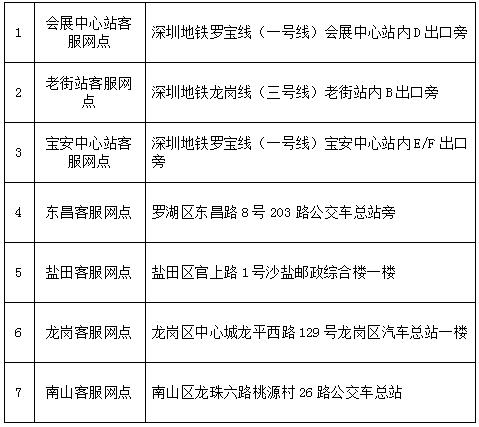今天,阴历4月29日,是父亲离开我们12周年的日子。不知何故,这几天夜里经常梦见父亲,梦见他坐在那张矮桌上首,一言不发地吃饭;梦见他骑着那辆长征牌自行车,穿着那件破旧的白色褂子,到学校给我送饭;梦见他赤脚挑水浇灌自留地里的西红柿,梦见他在诊所里给病人号脉听诊。梦境里的父亲还是那么的健壮,那么的亲切,那么的自然。我是多么的盼望着这梦永远的继续下去,让我再感受父亲的疼爱,父亲的呵护,父亲的温暖;但往往梦到半截就会醒来,醒来后再回放梦境,眼里就会不争气地噙满泪水,然后再保持原睡姿小心翼翼的入睡---据说这样可以使梦延续,但延续梦境的片段几乎为零。我知道,父亲走远了,越走越远了,他带着对亲人的不舍,带着对人间的眷恋,带着对子孙的美好愿望,恋恋不舍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父亲出生于1934年正月十三。坊间云正月十三为杨公忌,爷爷叹道:怕是这孩子多灾多难啊!爷爷是一个憨厚壮实的庄稼人,人生念条就是开荒种地,多打粮食,遇到灾荒贱年别把孩子们饿死,他心里带着这一原始简单的逻辑思维,凭着一身力气和简单的农具,挖石填壑,开岭造田,加上用结余兑地置业,至解放时家里已经达到100多亩土地的规模,日子殷实富足,解放后爷爷被顺理成章的划为地主成分;父亲6岁那年,尽管当时兵荒马乱,人心不宁,爷爷还是请了本族的识字先生,连同别姓的几户人家办了私塾,让我的父亲走进学堂念书。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8岁那年,经历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劫难。那是1942年的中秋节,秋粮入仓的节骨眼上,当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过完节呼呼大睡的时候,子夜时分,忽听村里鸡飞狗叫,人声噪杂,远处还有零零落落的枪声。原来,是盘踞在泗水县张庄一带的土匪头子张显荣,带领匪徒到村里抢劫绑票。据史料记载:张显荣半道落草为匪,为人奸诈,图财劫舍,绑票勒索,时有“东有刘黑七,西有张显荣,老百姓活都活不成”之说。正在睡梦中的父亲,硬生生地被破门而入的3个土匪从被窝里拖走,爷爷奶奶追到门外,凶恶的土匪用枪托朝爷爷打去,爷爷应声倒地;奶奶哭喊着奔向土匪,拽住父亲的小手,又惊又怕地想夺回自己的孩子,土匪飞起一脚,把奶奶踢倒在地。就这样,可怜的父亲被土匪拽着,一溜小跑来到村外的土岭上,那里聚集了很多土匪和马匹,田野里月光惨白而耀眼,马背上刺刀的寒光借着十五的月亮发出瘆人的杀气;父亲浑身没穿半点衣服,脚丫被岭上的蒺藜扎得流出血,疼得父亲大哭起来,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土匪拽着父亲的胳膊把父亲拖上马,“再哭就砸死你!”,土匪恶狠狠地吼着“拽住马鬃,摔死不问!”,父亲再也不敢哭、不敢叫,自己忍着剧痛把脚底的蒺藜摸索着拔掉。随着一声口哨,这伙土匪集合,带着抢来的财物以及21个儿童,堂而皇之地消失在夜色中。


父亲被劫走后,爷爷奶奶心急如焚,老人家顾不上满身的伤痛,四处打听营救消息。3天后,土匪那边通过中间人(实际就是所说的“钩子”)捎来口信,每个孩子须100块大洋赎回!爷爷卖地、卖牛、卖粮食,又从亲戚家借款,折腾了10多天才筹够大洋。父亲被中间人领回后,骨瘦如柴,目光呆滞,身上只披了一件覆盖到脚的成人破褂子,仍然赤着脚。由于受惊吓、寒冷,父亲大病一场,昏昏迷迷一个多月,自此父亲再没有进入学堂,不久因时局动荡学堂也关门停办。
父亲18岁那年,祖国已经解放。由于父亲多少识得几个字,爷爷便托亲戚介绍跟随外村的季老先生习医;这季老先生便是我后来的外公。父亲聪慧好学,手勤心灵,早起晚睡,很是用功,深得外公的喜欢;三年后,父亲便与母亲喜结连理。
1955年,上级号召成立联合诊所,个体游医编入联合诊所统一管理,父亲进入联合诊所继续从医,成为共和国第一批赤脚医生,后来那批人全部转到各大医院工作。当时西医引入国内逐渐普及,父亲头脑灵活,专攻西医,利用药片针剂治病效果既快又好,特别是父亲用“西林油”给病人治疗恶疮,外敷加注射,治愈众多患者,一时名声鹊起,引得外乡外地的患者奔着父亲来治病。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然界的法则套用在人间市井也是惊人的妥帖。父亲的小有名气非但没有带来福音,相反却带来了厄运。当时诊所的负责人眼看父亲从医之路风生水起,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便心生妒忌。加上父亲年轻气盛,常与负责人拌嘴摩擦,又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负责人自导自演了一起“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下放回家。搁现在有监控探头,这起错案根本就不可能得逞。1960年12月31日,所长安排诊所的3名员工晚上加班盘点清资,把当月的现金收入由会计锁在三拉桌中间的抽屉里;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加班餐。席间,所长故意劝父亲喝酒,致使父亲大醉,只好睡在诊所里;翌日,会计交账时发现少了18.5元现金,所长便把这事报告给上级,就这样父亲不清不白被冠以“监守自盗”的罪名下放回家。原来,那个三拉抽屉桌子只要把左侧抽屉取下,可以从夹缝伸到中间抽屉两个手指把钱夹出来,是有人趁父亲沉睡做了手脚。


我含冤受屈的父亲、我有口莫辩的父亲、我耿直任性的父亲、我多灾多难可怜的父亲,就这样由一个医生下放回家务农!
随着哥哥姐姐的出生,家里日子过得拮据而凄惨,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为了撑起这个家,父亲吃遍了人间的千辛万苦,受尽了生活的苦辣风霜!“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30出头的父亲经常用那个挂在山墙上的镜子端详被岁月过早染白的双鬓,嘴里自言自语的自我安慰、一声叹息。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父亲没有倒下?我想:除了父亲对爷爷奶奶的孝敬、对母亲的终身承诺,就是对我们子女的舐犊之情、慈爱之心。父亲啊,您用瘦弱的肩膀,为我们擎起大伞遮风挡雨,用干涸的汗水,为我们滴聚起一泓清泉,用永不停留的双脚为我们的成长铺路护航!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妹7人。我记事起,家里依然一贫如洗;“别把孩子饿死”,是当时父亲的最大愿望。父亲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作,开始利用早晚两头时间,几乎是披着夜幕与月色,用生产队分给的3分半自留地“搞经济”;春天,他在那片地里种上西红柿;夏末,拔掉西红柿再种上大葱;秋后,拔掉大葱又种上了芹菜,利用竹条架起简易棚子,为的是入冬后芹菜卖个好价钱,当时这是搞单干、被批斗的行为。为了防止被“割尾巴”,父亲说尽好话请假卖菜,有时就让母亲和姐姐去卖菜;为了便于管理菜园,父亲在地下挖一米,地面以上夯起1米多高的土墙,再配以木棒、柴草,搭建了一个简易的茅草屋,屋内打起了地铺,屋前架起葫芦棚,棚下摆上石块做茶几,幼小的我就在葫芦棚下看护菜园子。那简直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乐园,我们在地铺上睡觉、玩耍,在菜园里捉蚂蚱、抓虫子,可以吃上新鲜的西红柿、大葱;“人勤地不懒”,这是经常挂在父亲嘴边的话。清晨,每当我醒来,总会看到菜园子里的水还没有完全渗下,我知道那是父亲从半里远的坑里,用双肩挑来的水浇完了地,而父亲已经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了。记忆中的菜园子欢乐而又苦涩,我们家也算是靠着菜园子,勉强吃上咸盐、勉强生存下来;已经忘了经历了多少个春夏秋冬,那个破草屋一直蹲守在菜地一角,以至于唐山地震后,成了现成的防震工程。
葫芦棚下,地铺之上,父亲总是怀抱着我,给我们弟兄讲故事,记得他讲得最多的就是“孔融让梨”、“凿壁偷光”的典故;现在想来,父亲是在激励我们要发奋学习、弟兄团结啊!因为我们弟兄多,父亲就用历史事例教化我们,千万不要上演“煮豆燃豆萁”的悲剧。即使在外边,我们弟兄姊妹惹了事、与人产生了矛盾,父亲从没有给我们争理的先例,总是先把我们呵斥一顿,让我们反思过错;假若惹了祸,父亲有时会举起耳光拳头,咬着牙向我们挥来,但我清楚地记得:咬牙切齿的父亲举的拳头再高,落在身上总有一种温柔的感觉,其实父亲是舍不得用力的。父亲最崇尚的职业就是“教书行医泥瓦匠”,父亲说:教书让人识字,行医帮人治病,泥瓦匠可以给人打墙盖屋。父亲的意识里,始终潜伏着积德行善、助人解难的基因。即使父亲被下放后,仍然为街坊邻居义务看病处方,特别是给幼儿看病,父亲非常拿手,“孩子小,不会说不会道,但仔细检查总会找出病根”,这是父亲总结的经验。记得有年春天中午,村里一个婆婆与儿媳吵架,婆婆一怒之下跳进水井,“救命啊,救命啊”,大街上传来呼救声,父亲赶忙放下手里的饭碗,一溜烟跑到井边,那个婆婆正被众人捞起,但因呛水停止了呼吸。父亲拨开众人,一会按压心脏一会嘴对嘴吹气,最终挽回了婆婆的性命,那吓傻的儿子儿媳在父亲跟前长跪不起。
改革开放后,父亲始终惦念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总想着圆自己积德行善的夙愿。父亲辗转奔波,去有关部门批办了手续,在村里开起了个体诊所,一边种地一边行医,起早贪黑两不误。大哥、两个姐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和二哥,四弟五弟4个人都在学校读书,所以父亲仍然没有歇脚喘息的空档,“砸锅卖铁也让孩子读书”,这是父亲一贯的治学态度。之前,由于当时升学实行推荐,大哥大姐和二姐没有机会读书,这成了父亲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遗憾。二哥升初中那年,同样没有推荐上,11岁的二哥就开始参加劳动。在我家胡同口,二哥经常和同龄伙伴们聚在一起说话嬉闹,但一到时间那些孩子们就急匆匆地向学校走去,二哥只好扛起农具走向田野。看着这般情景,父亲心里定然是五味杂陈。终于有一天,父亲晚上步行10多里路,找到一个教书的远房亲戚,托人脸托脸的让二哥异地上了初中。后来二哥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随着我们兄妹7人成家立业,随着孙子辈的出生,父亲的脸上总算有了笑容。年近七旬的父亲不再下田种地了,但依然在诊所里坐诊。此时,父亲的最大愿望就是看着孙子们能有出息,能亲眼目睹子孙们有什么发展。“忠厚传家远、耕读继世长”,这是我家每年必贴的对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父亲教育我们最爱讲的一句话。
上了年纪的父亲腰身不再挺拔,满脸的皱纹刻录着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头上的白发映衬出父亲走过的坎坷光阴和沧桑岁月。
我不懂《周易》,也不迷信,但是当生活中出现什么大事,总在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一种科学无法解释的暗示。2010年“5.1”假期第一天,午睡中的我忽然被妻子叫醒,“快开门,咱爸爸来了”,等我打开门时却没有发现父亲的影子,妻子揉着惺忪的眼睛说道:“可能是我做的梦吧”,当时我心里陡生一种忐忑和担忧。我和妻子急忙从县城赶回老家,却发现父亲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父亲有点懒得起床,我问父亲怎么了?“感觉浑身没劲,肚子难受,别和西门外你堂哥样,得了不治的病”,父亲慢悠悠地说。我知道,住在村西头的堂哥因胃癌去世,“别乱怀疑,咱去市医院查查吧”,我对父亲说。
阳历5月4日,我和两个哥哥带父亲去了市人民医院。待各种检查完毕,我和哥哥们简直就像遭受了晴天霹雳!无法相信父亲会患上“胆管细胞癌”,并且已经到了晚期,心一下子降临到冰窟,一时难以接受诊断结果,眼里无法控制的渗出泪水。我们隐瞒着病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抓紧安排住院。翌日,四弟五弟以及叔叔家的弟弟赶到医院,商量下一步方案。四弟略懂中医,他拿起父亲的右手,仔细看了一下手上的表象,我分明看到四弟脸色一下子凝重,把脸扭过去,眼泪顺着脸颊哗哗流下。父亲并没有发现这一微妙的变化,“你们都放心吧,医生说我不是胃癌;你爷爷奶奶都活到90多岁,我不会有事的”,父亲对我们说。
第三天,我们经与父亲商量,从市医院转院到省城济南,住进了省中医医院。因为父亲相信祖国医学,认为中药能治标治本。看到病友的情况,再看看专家多次来会诊,父亲大概或许应该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只是他不愿意捅破窗户纸,自觉地配合治疗。我知道父亲爱吃鱼,就打听着到附件饭店买了几次“酱焖偏口鱼”,“这么贵,买鱼干嘛,吃着一点不香”,一向省吃俭用的父亲不停的责怪着,我明白是父亲肝胆胃发生病变,已经吃不出味道。父亲啊!以往您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如今您已命在旦夕,您倒是使劲的吃啊!怎么就吃不下呢!
服药、输液。一周后,医院给父亲采取了靶向注射治疗,我们也盼望着出现奇迹,出现救星。但事与愿违,父亲病情每况愈下,身体日渐消瘦。一天夜里,陪床的二哥被父亲的抽泣声惊醒,忙问怎么了?“我梦见你奶奶了,你奶奶踮着脚来到了济南,要带我回家。我看到你奶奶忍不住哭了”,二哥听着听着已经憋不住了,赶忙给父亲擦干泪水,自己谎称如厕,跑到楼下抱头痛哭。
在省中医医院治疗16天后,我们带着医生的“病危通知书”,带着“逐客令”,无奈的返回老家。阴历4月24日,我们把父亲又送到县医院做了最后的救治;此时父亲已经几度昏迷,无法进食;26日,我四叔,父亲的一母同胞,颤抖着双手捧着父亲的脸庞,“哥,咱回家吧,不能再待在医院里了”,四叔哽咽着说;父亲睁开眼看了看,微微的点了点头。回家后,我们一边准备后事,一边给至亲及在外地读书的孩子们打电话;阴历4月29日下午4时05分,当亲戚和孩子们都到齐后,父亲慢慢闭上了眼睛,望着气若游丝的父亲,我赶忙趴在父亲的耳边,用嘶哑的声音告诉父亲:“大大(方言,父亲之意),孩子无能,孩子不孝!您得的是胆管细胞癌啊!大大,您不用再受罪了!”,只见已经闭上眼的父亲,眼角里艰难的滴出两滴泪水。
在那些艰苦岁月里,父亲为我们弟兄5人成了家,建造了5座房子,而他与母亲一直居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给父亲做一口好棺材吧”,我的提议得到弟兄们的支持,也算是对父亲最后的报答。“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啊!您怎么就这么没有福气,在毫无保留地耗尽心血后,早早地撒手人寰!父亲啊!您不牵挂您的孩子了吗?您不是说要看看孙子们的成长吗?父亲啊!您把人间的苦尝遍吞下,没有享受一天啊!
父亲去世后,逢年过节是我最难过的日子;很多人将亲人的遗像悬挂起来,以示纪念。但在我是万万做不到的,莫说是父亲的照片,即便看到父亲的遗物、父亲用过的任何东西,都会触景生情、睹物思亲,我那可亲可敬的父亲的身影就会浮现在眼前。我常想,父亲并没有去世,父亲只是用另一种坚强的存在,在时时刻刻的关爱着我们。假若有天堂,我惟愿天堂里的父亲不再操心受累,不再忍辱负重;假若有来世,我惟愿还做父亲的儿子,尽一个儿子的微薄孝心。假若有另一个世界,父亲一定会为自己的辛劳和善良感到自豪和欣慰,因为父亲一生的付出操劳已经有了回报:父亲的6个孙子已经考出了两个高职、两个硕士、两个博士,95岁高龄的母亲和我们弟兄的生活,正向着父亲所未享受过的理想的日子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