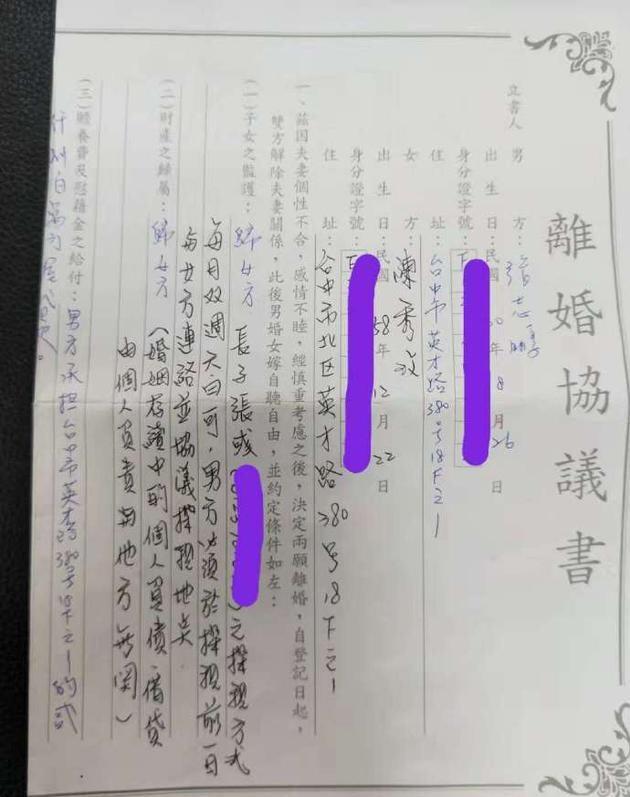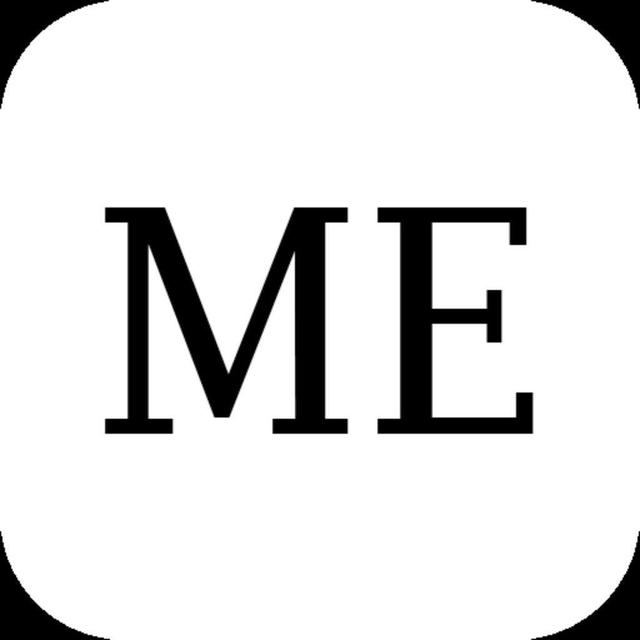一
项斯微说:有一种烦恼是莫名其妙的。
这句话在我身上不准。因为我有成千上万的烦恼都是莫名其妙的。比如我常常担心下辈子我要是变成一条金鱼那我的尾巴是很长很漂亮还是很短很难看;比如我还会担心高考的时候我会不会突然把背得滚瓜烂熟的公式给忘了;比如我还担心要是明天没有太阳,那么面对悠长悠长而又寂寞的黑夜,我应该去逢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郁的姑娘,还是应该好好睡觉。
我可以像滔滔黄河水一样连绵不绝地“比如”下去,可是席慕容告诉我不能浪费青春,所以我适可而止。
黄河也有断流的日子。
二
嗯成都的夜/黑不黑/有没有青城的寺庙黑/有没有青石板路黑/嗯我问你嗯/是我的长发黑/还是我的思念黑
我在榕树下看小引的诗,结果看到了这样一首山歌一样的“黑”诗,我想告诉小引:成都的夜,非常黑。
我从成都飞来上海,飞机离地升空,整个城市在我脚下星星点点闪烁不已,每盏灯火就是一个家,里面有我们追求的小幸福。
我头顶的是星空,脚下也是星空。美丽的是幻觉。
安妮宝贝说:夜幕降临,我的指尖开始蠢蠢欲动。我是个很爱崇拜别人的人,所以我也试着在晚上写文章,结果我也养成了一个不怎么好的习惯,凌晨时分在电脑键盘上不断key in, key in.
假如明天没有太阳,我想我就可以写很长一篇文章,可以赚很大一笔稿费了。那我看中很久的那支羽毛球拍就可以买了。
我是个很爱假如的人,我最常做的一个“假如”就是:假如时光倒流三年。
假如时光倒流三年我想我不会上这个应该被诅咒的高中。我会随便挑所中专然后随便挑个专业然后轰轰烈烈地生活,并且义无反顾。我会像北大那个特疯狂的学生一样做好“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的准备。我会写很多的稿子,然后交给我所熟悉的编辑。我会学会弹钢琴,让自己的十指变得无比灵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角度扭曲自己的双手来使用左手定则,右手定则。
可爱因斯坦告诉我:你的假设失败。
假如明天没有太阳,这好像也不太可能。
三
假如明天没有太阳,那明天的黑夜会有多么庞大?
安静的夜里我习惯一个人躺在床上,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我可以看到城市间隐隐浮动的霓虹,可以看到大朵大朵的云散发着清凉的气息飘过黑蓝的天壁。
所有的声音都退得很远,只剩下无边无际膨胀的漆黑。而这种漆黑要么让我疼痛,要么让我热血沸腾。而这种状态很是歇斯底里我是知道的。
在让我疼痛的夜晚,已经沉淀的往事又会被搅动起来,一个一个排成队从我心里爬过,所过之处一片喧嚣。而当一切骤然退去的时候,心上搁浅下来的东西会让我唏嘘。
而在让我热血沸腾的晚上,我总是在电脑上疯狂地打字,一直打到黑了,然后倒在床上筋疲力尽,然后幸福地抽筋。
我想我是个疯狂的人。
四
上帝要把一个人毁掉必先令其疯狂,可我疯狂了这么久上帝为什么还不把我毁掉?
还有还有,世界末日的前一天太阳不会升起,可后天又不是世界末日,那么为什么明天的太阳还没有升起?
我想上帝他老人家一定在专心致志地修他的手指甲。
五
有个笨蛋曾煽情地说:“噢,朋友,假如明天没有太阳,请别忧愁,因为你还有月亮。”
说什么屁话!太阳都没了哪儿来的月亮啊?
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喜欢阳光的,只是偶尔依赖于黑夜的保护色。就正如我曾经以为自己骨子里是个聒噪的人只是偶尔莫名其妙地安静,后来朋友告诉我,其实你骨子里是个安静的人只是偶尔莫名其妙地聒噪。
我想我是喜欢阳光的。我总是在有空的时候就搬把沙滩椅坐到阳台上,在如水一样流淌的阳光里翻我的牛津英文词典,看那些一条一条很长的词条。对面阳台上的那个梳着细长辫子的女生也总是在阳光里努力地背单词。她背单词的时候很认真,像我初中的同桌小溪,小溪也是梳两条细长的辫子,但她的样子我却记不起来了。况且我手边也没有一块橡皮什么的供我回忆起同桌的她。
我的初中时光被遗忘在某年某月的某个黄昏。
某个一去不再回来的暖色夕阳。
是悲哀啊是悲哀,不管我把拳头握得再紧,闪亮的时光照样从指缝中流走,不费吹灰之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你走你的独木桥,我唱我的夕阳调。谁的孤独,像一把刀,杀了我的外婆桥,杀了我的念奴娇。
杜拉斯说,人一开始回忆,就已经开始变老了。
我在努力地回忆,或者说,我在努力地变老。
六
我有个朋友叫前世,网络上的,我们最开始认识是因为他想把我的几篇文章弄到他的网站去,他很负责地发E-MAIL过来给我说一声。
前世是个诗人,他说他就是不希望有阳光的,他说,他前世就是黑夜里开在黑色沼泽里的黑色曼陀罗,暗香涌动。
我问他我前世是什么,他说你是钟上面的一枚针,一边孤独地原地转圈,一边看时光一去不返,而你无能为力。
前世总是这么一针见血地刺伤我,很多时候我都是马上关掉电脑,然后喝上一大杯开水,告诉自己别怕别怕,今晚好好睡,今晚好好睡,可大脑总是坚持苏醒。
诗人说:在黑夜中坚持苏醒的人代表着人类最后的坚守,可这种人往往容易最先死掉。
黑夜有时令我恐慌,我希望明天还是阳光普照。
七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说的这句很像病句一样的话其实很有道理。
我在故乡以外的城市看着街上灯笼越来越多,我真的很想回家。
太阳的光芒一天淡似一天,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哪一天它就转身消失不见了。
日历越撕越薄,而我文档里存的文字却越来越多。文档里有我各种各样美丽的幻觉,像是个美丽的垃圾场。当我飞来上海的前一天,当我整理我的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小乞丐。
八
我写了八个小节,这是个吉祥的数字。
我知道明天没有太阳那是假的。
可是我看到头顶脚下的星空,我写的文章,我的羽毛球拍,我的牛津字典,我的同桌小溪,对面阳台的女生,越来越薄的日历,这些统统都是真的。
而现在我想回家过年,我想快点快点,回家。
这也是真的。

我喜欢的音乐是两个极端——摇滚和校园民谣。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的确有人伸手过来摸我的额头看我是不是发烧。
我有六盘心爱的CD,《校园民谣1》,《校园民谣2》,《高晓松作品集》,以及麦田公司的红白蓝系列。朴树的白色孤独,叶蓓的蓝色忧伤和筠子的红色激情。
我总是觉得中国五四时期和90年代初的大学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五四时期有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到了90年代,还有大学生为了海子的死亡而焚烧诗集以悼念。于是海子极其惨烈的死亡也随之有了光环。90年代还有高晓松。只是我们喜欢称他为搞笑松而已。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界定高晓松的音乐。我也不知道听惯了重金属的自己为什么突然对那么柔软的音乐着迷。我记得我最初把高晓松的作品集借给我的朋友听的时候,他回答我,好是好,不够味儿,没摇滚带劲。朋友的回答让我跌破眼镜。可我却是真正感受到那些哀伤清淡的旋律里面所蕴藏的激情,如同夜晚大海的黑色波浪,一波一波朝我内心深处打来,雷霆万钧。就像杜拉斯曾说过的“潮水匆匆退去又急急卷回”。给我更多冲击的还有他的歌词。我喜欢的作词人有三个,高晓松,何训田,林夕。有乐评人曾经说过,有了这三个作词的人,所有的诗人都该感到惭愧。何训田的歌词需要欣赏的人有强烈的西藏氛围来支撑,而林夕的词太偏重于城市里精致的爱情。而高晓松的词可以在晚上听,可以在白天听,可以夜色阑珊时听,可以在阳光明媚时听。小A曾经笑着说高晓松的歌像是万金油,百病皆治。我说不对,他的歌太老的人不能听,太小的孩子不能听。因为高晓松的歌词里总是会流淌着一条青春的河,时光蔓延,哀伤弥漫,轻而易举地就能将人覆盖。拿给小孩子听他还不知道是青春,拿给老人听他们想起了青春应该是民国时的水深火热,至于什么青春的忧伤之类的我想和他们八竿子也打不上。我总是喜欢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已经大学毕业,每个人都在生活的夹缝里谋取营生,每天穿着整齐的西服穿行于石头森林的时候,突然听到诸如笔记本,考试,英语语法,寝室窗前的美丽香樟,同桌的漂亮女生,食堂门口常看见的帅气男生,心爱的书包,不及格的成绩单,毕业纪念册,足球场等这些词语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停下脚步,有多少人会涌出泪水。
然后是老狼。老狼身上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流浪歌手的气质。我一直都记得老狼在《流浪歌手情人》里哼唱“你只能一再的一再的一再的相信我”时,表情与声线是如何的哀伤与清澈。老狼的歌声像是一本日记,他就一页一页地将他的和我们的成长撕给我们看,于是相同的年轻和忧伤浸染了当时大部分的大学生。比如他唱的给女生写的情书,好兄弟彼此猜硬币,午夜哀伤的电影,弹吉他的流浪歌手。当初最早听他唱歌的人已经长大了,还没长大的我们继续听他的歌。“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里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恋恋风尘,恋恋风尘。
一直以来我偏爱叶蓓,那个迎风吟唱的蓝色歌手。说是“偏爱”是因为从对校园民谣的贡献来讲叶蓓的确比不上高晓松和沈庆。但是我喜欢。我最早接触校园民谣就是听的叶蓓,比老狼都还早。我记得第一次听到叶蓓唱歌是在一条喧嚣的大马路上。我经过一家叫“麦田风暴”的音像店,里面在放叶蓓的《B小调雨后》。一瞬间我停留下来,身边所有的喧嚣都立刻退得很远,包括那辆嚣张叫嚷了很久的洒水车,空气里只有她空灵的声音辗转回旋。旋律以血液的形式汩汩地流进我的身体。我觉得自己的身子像是夸父,一瞬间身体有变成山脉变成大海的冲动,皮肤上有开满离离的野花的激情。身体消失,灵魂飞升。就是这样,有点像佛经中的顿悟或者立地成佛。
叶蓓是个朴实无华且低调的歌手,我不知道这种性格在一个歌手身上究竟是一种优点还是一种缺点。叶蓓是声乐专业的本科学生,可是她很少炫耀这些的确值得她炫耀的东西,她也很少卖弄她轻而易举就达到的高音C,她就是那么安静而忧伤地唱,没有喧嚣和做作,如同月光下的湖泊,平静,但有着令人眩晕的银色涟漪。
之后我开始生活在白衣飘飘的年代。我穿越整个城市找遍了所有的校园民谣,然后就疯了一样地听。可是看看那些CD的出版日期,背后总是写着1995。这代表着什么轮不到我说,我只能说我以后很难买到新的校园民谣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有唯美而忧伤的旋律来当做日记本,记录所有高昂或者哀伤的青春。
说到青春我想起沈庆,他的那首《青春》总是让我念念不忘。有些时候生活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碎却不堪憔悴。淡淡的云淡淡的梦,淡淡的晨晨昏昏,淡淡的雨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我想我到了很老很老的时候,老得几乎可以隐入落日的余辉的时候,我也会记得,年轻的自己曾经很喜欢过一首叫《青春》的歌。因为这首歌就是我的青春凝聚成的油画,我的整幅青春光彩夺目。我曾经在一个谈话节目上听到沈庆这么评价自己:青春的记录者。不管他记录的是谁的青春,总之我很喜欢并且很赞赏这种定位。他用音乐当做纸笔,写下大学时代的忧伤。就像他唱的那样:“我要埋下所有的歌,等它们被世间传说。”
另外一首《青春》是筠子唱的。我只记得那里面的吉他声有着让人落泪的破碎,恍惚的旋律,下雨的黄昏时分的冷清街道,路人空洞的眼神,一切都贯穿着旧电影昏黄的色调。筠子的声音高昂嘹亮,可是却有着忧伤的嘶哑,如同水晶杯子上的裂痕,听着筠子的声音我总会想到石康的话:“我看见一阵一阵尖锐的忧伤划过我的心脏”。《青春》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当我听到筠子用梦呓一样的声音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我听到了青春在天花板上扇动翅膀的声音,像是蓝天上嘹亮宣言。这让我想起我看到过的一篇乐评《十三楼的折翼天使》。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浸染着一种情绪——孤独。筠子就给我这样的感觉,不,应该说所有的校园民谣歌手都给我这样的感觉。那些书写青春歌唱青春的人都离开学校了,他们意识到自己远离了自己清澈的柏拉图,于是他们拒绝离开,于是社会的喧嚣抛弃了他们或者说他们抛弃了社会的喧嚣。于是他们就孤独了。这就有点像不想长大的彼得·潘,他不想离开童年,于是他的伙伴长大了,他一个人留在了永无岛,于是他成了一个最孤独的孩子。高晓松他们的孤独是一种城市里的孤独。就像莫文蔚在《十二楼的莫文蔚》里宣扬的寂寞一样。
莫文蔚是商业流行歌手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她在《十二楼》里准确地演绎出这个飞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给人们投下了怎样孤独的暗影。我想高晓松他们的孤独也一样。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远离他们依恋的纯真年代。我想起一个我记不起名字的爱尔兰歌手的歌:整个城市在旋转,可是我转来转去总是孤独;喧闹的灯火照亮了一切甚至夜幕,可照不亮我手心的孤独;我们的青春无情地飞逝,年老的我啊依然孤独;最后我进了天堂,可天堂里孤独的我依然跳着孤独的舞步。
我想把孤独的内容演绎得最生动的还要数朴树了,那个白色的寂寞歌手。《那些花儿》里清晰的流水声音让我想起时光的荏苒,一起长大的朋友分散到天涯,距离的隔断真的让大家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青春不再,光阴不再,麻木铺天盖地,涌入血液心脏骨髓。大多数人习惯了,接受了,屈服了,只有朴树不,于是他用带着哭声的歌问道:“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然后有人听见,然后更多的人听见了,于是大家一起重新痛。“新的人间,化装舞会,早已经开演,好了再见”。朴树说他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因为他心爱的气球丢掉了。我知道那个孩子就是那些校园里孤独行走的歌手,高晓松,沈庆,叶蓓以及他们和她们,但我不知道那个丢失的气球代表着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气球最终飘到了什么地方。
高晓松们的低调已经是对社会的一种退让,可是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似乎还不满意,于是校园民谣被逼到了死角。以前校园民谣有商业价值,于是唱片公司也乐得赚钱,当校园民谣不再有号召力的时候,于是就有了“1995”的大裂谷。断裂,挣扎,消失。沈庆现在是一家音乐网站的总裁,西装革履地出入任何场合。当我看到沈庆在一个谈话节目上穿着西装唱《青春》的时候,想想那个毛衣牛仔裤的沈庆真的是恍如隔世。高晓松写书拍电影去了。老狼没有了消息,偶尔会在某某大学的校庆上看见他,可是脸上早已没有了年轻的飞扬,眼角的沧桑让人唏嘘。那天在一个采访中老狼说自己对未来还没有方向,于是我想起了他当初唱《月亮》时迷茫的样子:“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唱起了歌”。而叶蓓则在华纳公司唱情歌,听着她唱什么“你的怀抱”“回忆忘不掉”之类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再想起她唱“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不过叶蓓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她还会唱“很旧很旧的风在天上”。而庾庚戌呢?我只记得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没唱校园民谣了,我在做设计,因为我要吃饭。“因为我要吃饭”,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鼻子酸酸的。排山倒海,物是人非啊!也许就像李碧华说的那样:“很多隐退的演员重新复出,不要以为是割舍不下艺术,皆因付不起醉生梦死的代价。”对校园歌手来说,很多人隐退不是不喜欢校园民谣,而是付不起理想至上的代价。
听到庾庚戌采访的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高晓松叶蓓他们一起唱《孩子》:“我想跑跑得很快,心在不安里飘荡,但看一看四周,想到你已白发苍苍。春天的花朵,开在冬天的雪上,风吹过的过去,我们从未曾忘记,想和你分享,可是你已经老了。孩子孩子我还是孩子,孩子孩子我不是孩子,你原谅我吧,别对我说吧,我原谅你了,可我终于哭了。”
我一直不愿意接受某些媒体所宣称的“校园民谣时代的结束”。我在等待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纯真年代能够重新降临。会有忧伤的歌手会在校园里弹吉他,会有为海子焚烧诗集的悼念仪式。可是按照眼前的情况来看好像希望很渺茫。也许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会对着我即将离开的校门说:校园民谣的时代真的过去了。我想那一刻我会听见黑色的劲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如同午夜最后一班飞驰而过的地铁。但是我想我会深刻地记得,那些歌手曾经是我生命花园里的灼灼桃花,我旅途驿站的阳春白雪,我青春的夜空里瞬间绽放而又转瞬即逝的美丽焰火。就像叶蓓的《蒲公英》:“一开始/我就站在这里/在风里面长大/没人路过身旁/为了你一句叮嘱/你留下的旧地图/我穿着这件衣裳/守着这片山岗/天黑了/没有星星的夜/没有雨的春天/没有你的流年/我不怕迢迢路远/我不怕浩浩人烟/我要随着风飘落在你的脚边”。那些寂寞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一样,站在山岗上,守候我们心里的纯真年代,守候一份希望渺茫的希望,守候一份我们曾经的坚持。
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

我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开始于17+N年前,其中N大于等于零。
我现在17岁,数学老师说那个N的取值范围实在是不可理喻。
其实没什么不可理喻的,用一句大家都明白的话来说就是:上辈子我爱王家卫的电影爱得要死,然后喝孟婆汤的时候我少喝了一口或者吐掉了一点,而那一点恰恰是用来消除我脑中关于王家卫的东西的,所以上辈子的喜好这辈子再接再厉。
提到孟婆汤我想这又可以拍出一段类似王家卫风格的电影了。画面开始的时候一片漆黑,然后头顶一束光打下来,照着一个很沧桑的男人,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或者说是麻木,然后低沉的画外音开始浮出来:我上辈子少喝了一口孟婆汤,所以这辈子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忆,它们令我的生活恍惚……
很好很好,我想也许将来我可以做个大导演,像家卫一样。或者当个写剧本的,像李碧华一样的也不错。记得我刚看王家卫的电影的时候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将来我要去为王家卫写剧本。后来知道原来王家卫拍电影是从来不用剧本的。笑。
河的左岸
有个男人叫左岸。他出现在我的潜意识里浮现在我的剧本上。
左岸是个摇滚乐手也是个很有灵性的诗人。他有一头很有光泽的长发,明亮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
左岸之所以叫左岸而不叫右岸是因为他偏激、愤怒、冲动、自负。左得很。
就像曾经的我。
很难想象十六七岁的孩子会符合上面四个词语。但有时候是会有奇迹或意外的。
在《重庆森林》里王家卫就让金城武不停地吃凤梨罐头,不停地等待奇迹。
十五岁的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打断老师的讲课,然后对他说这里的to不是不定式结构而是介词所以它后面不应该用动词原型。然后我骄傲地等待老师对我的表扬。结果我等来了一个奇迹,我比金城武幸运。我等来的是英语老师的一刹那尴尬至极和随后的不可压抑的愤怒。他一边在空气中漫无目的地挥动着手臂一边冲我吼:你给我坐下。我说:错的是你我为什么要坐下?然后一切变得不可收拾。
最后他对我说:以后你别上我的课了。
然后我对他说:我现在就可以不上你的课了。
我记得我冲出教室的时候把门摔得震天响。
然后我以外语满分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走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终于还是赢了。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疲惫,就像油灯熄灭前奋力地一晃。所谓的瞬间衰老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转身的时候听见他在背后小声地说:原来你一直没有明白,我以为你明白的……现在我十七岁了,站在成人世界的大门前向里面张望。我觉得当初的自己实在是太过年轻太过冲动太过骄傲太过盲目了。其实一切都不必要的,为了一个动词。
美丽的错误。
回望中的道路总是惊心动魄。我记得白岩松曾经这么说过。好了让我们回到左岸身上。
他住在几平米的阁楼上,每个夜晚光着脚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晃。木质地板吱吱地响。
“寂静的夜里并不黑/趁着首都光辉/开着窗缓慢地来回/忽然亮起的红灯/淹没我窥视/开着窗真理在徘徊。”
他会站在窗前盯着外面阑珊的灯火呢喃:如果我可以飞翔可以不再忧伤……想到这儿就会戛然而止。如果……那么……的结构没有完整。因为左岸从来就没想过“那么”之后的事。那么我会怎么样那么我能怎么样?
左岸的生活是一种单调的重复,有着王家卫的空虚和张爱玲的琐碎,像是翻来覆去的沙漏或者不断回放的电影。左岸对现实的生活采取的是一种回避的态度,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然后大声唱歌: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左岸会想他的女朋友——曾经的女朋友。每天每时每分每秒想。
他总是想她和他分手的时候说的话。很多很多的话。她说:你太漂泊而我不习惯流浪,你太叛逆而我却很宿命。你是个天生寂寞可是才华横溢的孩子。谁做你的女朋友谁就是最快乐的人但同时也是最痛苦的人。我很普通我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落差。我所想要的只是平凡——一盏灯亮到天明的那种。我只是想有个人可以和我说话可以给我你认为很俗气的玫瑰可以把我的手放到他的口袋里然后问我暖不暖和。我很平凡所以你放过我。
而左岸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后没人唱歌给你听了怎么办。当左岸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泪纷乱地下坠。他的还有她的。
又是一个夜晚。左岸照常想他的女朋友。但今天他的思念极度放肆,犹如洪水猛兽席卷所有理性的坚持。于是深夜一点或是两点或者三点,随便导演怎么安排,总之是深夜。左岸跑到街上的电话亭里打电话。
他握着话筒说:我想你了,你想听我唱歌吗?我唱给你听好吗?你让我唱吗?好吗?成吗?
然后他蹲下来哭了,头埋在两个膝盖间。而这时导演可以考虑不时地让车灯打入电话亭。一明一暗。
然后左岸站起来往回走。
然后左岸听到一阵很尖锐的刹车声,他回过头去看到刺眼的车灯和司机惊慌失措的眼睛。
画外音:我发现自己的眼泪原来是这么烫的。我想我该回家了。起雾了,街上影影绰绰。前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排队?他们等着干什么?我挤到了前面,发现队伍前面有个慈祥的老妈妈,她正在给排队的人喝一碗又一碗的汤。
THE END
我的朋友看完问我:你在写恐怖片?我说是啊是啊写得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真是好啊。
想不到把我这样一个好学生生活中被掩盖的东西写出来竟会是恐怖片。想想真是惊世骇俗。
河的右岸
右岸是个老实的男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按照最让人放心最不会让人害怕的条件打造出来的男人,那么右岸就是这样的人。右岸之所以叫右岸而不叫左岸是因为他的温文尔雅他的逆来顺受。右得很。
右岸留一头简单纯色的头发,穿合乎场合的服装,有恰如其分的微笑,用平和清淡的古龙水。
就像现在的我。
以前我七七八八棱角很多,连走路都是张扬的。我斜挎着背包双手插在口袋里晃——注意,是晃,不是走——看见漂亮的女生就对她们笑。
而现在我背着双肩包贴着墙根快快地走,双眼盯着脚尖像在找东西一样快快地走。同学说我捡到钱包的概率会比别人高很多。
现在不要说让我把门摔得震天响,我连同老师讲话的时候也在考虑应该用怎样一个无法申诉的眼神怎样吐出优雅得体的措辞。因为老师的评价是高三保送成功的重要筹码。
小时候我想当一个伟大的作家,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大一点我想当个畅销小说家,有很多很多人来买我的书,那我就会有很多的钱;而现在我想我可以为那些钱多得没地方花而且又想出名的人写传记。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把祖国建设得很富强;再后来一点我的理想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钱;而现在我的理想是能上复旦。好听一点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难听一点说是我越来越世俗。
我是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孩子,我有单纯的眼神和漂亮的成绩单,安分的性格和其他长辈们视作珍宝的东西。我妈的同事常对她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你的儿子真是争气,你活这一辈子算是值了。
好了回到右岸。
右岸每天早上坐同一时间的地铁坐同一个座位去上班。从地铁站口走出地面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同时看看被高楼切成几何图形的蓝天。
右岸的生活也很简单。
白天在电脑前喝纯净水,晚上在电脑前喝咖啡。
简单的重复。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重复是永恒的主题。无常的宿命一次又一次直到N次地呈现在你眼前,就像是一个人在你面前不断地撕开伤口来向你证明“我在流血”一样,最终逼迫你恐慌逼迫你心疼逼迫你流下眼泪。
又是一天,重复的一天,右岸像往常一样坐地铁上班一样抬起手遮住眼睛一样仰望蓝天。不一样的是他今天要交一份计划书。
和他一样,另一个人,暂时叫他小B好了,反正是个小人物,也要交份计划书。在主任的办公室里,主任微笑着说:好的,基本可以,不恰当的地方我再改改。
然后计划被公司采用了,但策划人却变成了主任,右岸和小B的名字出现在助手栏里。
不同的是小B向上级报告说要讨个说法,而右岸则平静地坐在电脑前一如既往地喝纯净水。
后来主任升职了。主任走的那天右岸就搬进了主任的办公室。而小B被调到了资料室。
再后来右岸成了四个部门经理中最年轻的一个。
再后来右岸结婚有了个女儿女儿嫁人孙子出世。
孙子出世之后右岸就躺在了病房里。但他依然很胖,右岸从三十多岁就开始胖了。右岸躺在医院就会想到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是怎么也长不胖的。
右岸习惯在医院洒满阳光的午后开始回忆,然而回忆总是进行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就中断了。
后来终于有一天右岸想起了大学毕业后的生活,电脑与纯净水、电脑与咖啡。
右岸想自己好像过了很多个那样的日子,应该很多吧?应该有一两年吧?
然后右岸就想睡觉了。在眼皮快要合拢的时候右岸看到一个慈祥的老护士走到他的床前对他说:右岸起来,该喝汤了。
右岸想:现在的医院真是好,还有汤可以喝……
THE END
朋友看完说:那个右岸的生活真是无聊,不痛不痒像温吞水一样,与其活得那么沉闷还不如去跳天安门城楼来个举世瞩目。
其实右岸的生活就是按照长辈给我设定的当前的状态发展将来一定会出现的生活,不想却被朋友骂得那么惨。暗自心惊。
河的第三条岸
河的第三条岸到底在哪里,连舒婷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是河床嘛!只不过是另一种说法而已。就像我在网上的名字第四维一样,其实第四维就是时间而已。简单复杂化!
河的第三条岸不属于右岸也不属于左岸(那属于我好了),它就是第三条岸,属于过渡区的。
过渡区的东西是最复杂难懂的,比如化学的过渡型元素就令我相当头痛。但复杂有复杂的美,总比处在两个极端要好。珠穆朗玛峰太冷,吐鲁番盆地太热,中原多好。
就像现在的我。
我上高二了,轰轰烈烈的生活,寻找每一个理由善待自己。我不是全年级的前三名,但我总是在前二十名内徘徊以便不使我的父母过分操心。我爱看严肃的电影也爱看日本的偶像剧。我看卡夫卡、大江健三郎也看古龙、卫慧。我在传统的杂志上发文章也在榕树下说些疯话。
我常常思考自己的生活,自觉是个比较有深度的人。
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在自己的眼泪中开始在别人的眼泪中结束。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很聪明但未免太宿命。两次眼泪之间的几十年是光芒万丈还是晦涩暗淡完全由你自己做主。
所以说我既不是右岸也不是左岸,我是第三条岸,所以我写的剧本缺乏真实的体验难以操作。我很想写写自己的生活我想那一定是几万字的巨著,但韩寒说了:给自己写自传的人都很恶心。他的风头正健所以我只好放弃。我说了,我不是个出挑的人。
还是那句话,我希望能给王家卫写剧本。虽然这句话也很不可理喻。但请注意我用的动词是“希望”。同类型的句子还有:“我希望我能飞翔。”
这样想就没什么不可理喻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