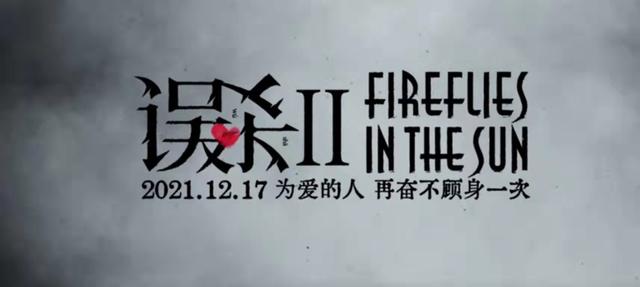提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估计所有人首先想到都会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而如果提到《史记》这部书,那么人们脑海中首先会浮现出鲁迅先生那句经典的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虽然该书有大量光怪陆离事件的描述,比如黄帝战蚩尤,汉高帝斩白蛇等等。但是,由于《史记》拥有大量详尽的史料,所以谁也无法否认它是一部令人信服的“信史”。同样,作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它的文字和语言华丽且优美,会让人在得到史学知识的同时,在文学上也能获得陶冶和升华。但是,这些是史记的优点,但并非独一无二的特点。那么《史记》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

在笔者看来,《史记》与其他史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个注重对悲情英雄的描述。而且,那些战争或者宫廷斗争中的失败者,司马迁都给予了非常正面的描述。甚至不惜为他们献上最为华丽的辞藻,让读者在阅读时,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同情。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对悲情英雄予以正面夸赞的同时,还在对他的对手进行了“反讽”和“挖苦”,进一步突出了悲情英雄的光辉形象。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项羽和刘邦二人在《史记》中的形象。在历史行的项羽,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他为人暴躁、嗜杀,不仅屠戮数十万秦军战俘,还为了让齐国屈服在齐地大肆杀戮。但是,就这样一个人,司马迁还是将其列入了“本纪”。要知道“本纪”属于皇帝的专属特权,虽然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但只是一方诸侯而已,最多可以列入“世家”。但是,司马迁不仅将其列入了“本纪”,更是对他不吝优美的词语进行夸赞。甚至在垓下之战时,面对汉军的“十面埋伏”,项羽已经是“四面楚歌”的末路。但是,司马迁依然不忘强调项羽是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他之所以走上穷途末路,只不过是“天不与我,而非战之过”。所以,当项羽乌江自刎千年之后,李清照还写下了“今日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但是,作为项羽的对手刘邦,则完全以另一幅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位泗水亭长一出场,就被其父刘太公给定性为“无赖”。所以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战场上,刘邦将这种混不吝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当单父县的门阀吕公移居沛县之后,刘邦敢到门上吃“霸王餐”;在彭城之战时,为了自己逃脱性命,不惜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扔下马车;到了成皋荥阳之战时,面对被俘的刘太公,居然对项羽说出“我父即为汝父”的话……可以说,简单的几个故事,就让一个“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的汉高帝跃然纸上,而且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让很多人感慨“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但实际上刘邦真的如此不堪吗?这个先入关中,能够约法三章,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朝开国皇帝,如果真只是一个“无赖”,怎么会让韩信说出“大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的话语呢?

由此可见,司马迁为了凸显项羽悲情英雄的形象,不惜对刘邦进行了一定的抹黑。而且,司马迁的《史记》中不仅用语言文字戏谑了一番西汉开国皇帝,同样没有放过为汉朝江山建功立业的汉朝名将们。纵观西汉200余年的历史,北边的匈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敌人。但是这个巅峰时期控弦40万的强大游牧民族,在遇到西汉两大名将卫青和霍去病之后,只能哀叹“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但是,就是这样两位让西汉北部边陲安定,同时又为汉朝开疆拓土的大将,他们的名字居然会出现在《佞幸列传》之中。虽然,他们也各自有单独列传,但是司马迁这种态度,似乎就是在表明自己对他们二人的不满和嘲讽。或许在司马迁看来,他们虽然建立的前无来者的功勋,但都是靠着裙带关系才获得这样的成就。
反观号称“飞将军”的李广,由于生不逢时,生活在讲究无为而治的文帝景帝时代,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封为侯爵。但问题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到了,李广一生大小经历70余战,那么他无法封侯或许不是因为缺乏立功的机会,而是缺乏立功的能力。纵观李广一生,作战很多,但是败多胜少,甚至自己都曾被匈奴生擒活捉,这足以说明李广的军事指挥能力欠佳。尤其是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身为先锋的李广,居然会中途迷失道路,无法及时赶到战场,反而遭遇匈奴伏击而损兵折将。司马迁虽然将这些也记录在了史记上,但是往往会笔锋一转,用更为华丽的词语来为李广的种种表现进行辩护,最终让人们对这位屡战屡败的将军产生深深的同情。

而且,《史记》中不仅有这种出人意料的巨大的反差对比,还有对悲情英雄的正面描写,比如先秦“五大刺客”。这些自认为得到“知遇之恩”的游侠,为了报答自己的恩主,凭借一己之力,靠一支匕首,就敢深入虎穴,对王公贵族或朝廷要员进行刺杀。完全不顾他们刺杀的结果,会对天下局势或黎民百姓造成何种结果。同样,被司马迁笔下的田横五百壮士,他们集体自刎的故事确实能让“闻着伤心,听者流泪”。他们毫无疑义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何不能选择留下有用之躯为江山社稷做一番贡献呢?但是,司马迁还是将他们都写入了“列传”。
当然,这些都属于以今人之眼光揣测当年人的心思,似乎有些“后世诸葛亮”的意思。但问题是,为什么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会有如此的表现呢?很多人都觉得是司马迁因为自己为李陵进行辩护,遭遇汉武帝处以刑罚之后,对汉朝的刘氏皇族心存不满。所以才会对汉朝的天子和大臣用文字进行挖苦和嘲讽。而且,由于司马迁本人身体遭受刑罚之后,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反而对那些没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产生了同情,所以才会更加偏爱那些悲情英雄。这些原因是否有道理呢?或许有一些,但是在我看来,更为关键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

首先,就是司马迁也好,以及当时的汉朝人,并没有形成服从权威的思想。虽然,秦代就开始推行法家学说,汉武帝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从汉初推行道家的“黄老之学”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依然是“百家争鸣”。既然是百家争鸣,那么看似高高在上的皇帝,他的权威性并无法让人屈服。而这就导致,当时的人们不会有“成王败寇”的认识和概念。所以,司马迁完全可以完全不顾及皇帝的权威,而是根据自己喜好,书写自己内心所想。
当然,皇帝的权威性不仅在汉朝没有很多好的解决,甚至到了唐初都没能得以解决。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门阀的权势远超当时的皇帝,以至于出现“王马并天下”的局面。到了隋唐时代,皇帝的姓氏在《氏族志》中仅仅只能位列三等姓氏。虽然,这些并非汉代所发生,但在中央集权和皇权都没有得到加强的汉代,这些事情并非不可想象。而长期世袭“太史令”的司马迁家族,对于刘汉皇室同样也有制约的方式和力量,所以皇权根本不能让司马迁屈服。
其次,太史令的权力。司马迁一家长期世袭“太史令”一职。作为史官的太史令,在编撰和记录历史时,可以完全摒弃皇帝的干扰。皇帝根本没有权力去逼迫史官,按照自己的意思记述某个历史事件。所以,司马迁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收集的史料,书写自己想要表达的历史观点。

当然,除了史官本身的权力之外,还有这所谓的“神权”!“太史”一职最早出现在殷商时代,在先秦时代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倾向于神权,主掌天事”。虽然此后,其职责不断丰富,但是到了汉代它的主要职责还是“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记之”。由此可见,太史令“神权”确立的时间,以及大众认可的程度,都比号称“天之骄子”的皇帝要更令人信服。毕竟,到了汉武帝时期,君权神授的思想才开始逐渐确立。也正是因为有“神权”的护体和加持,才让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能排除包括皇帝在内的各种干扰项。
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在《史记》中对悲情英雄展现非同一般的偏好,除了与自身的命运相关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史官的相对独立的环境,以及太史令“神权”的加持下,可以不惧皇权的权威,不怕皇帝的干扰和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