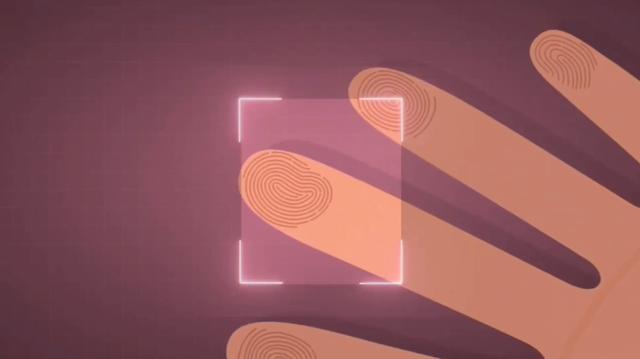作者:刘河廷

邻居对门家爷爷,按辈分应叫老爷爷,打我五六岁记事时,就是下巴一缕山羊须似的白胡子,又高又瘦的样子,略微地弓着腰。那时感觉就像七、八十岁的“老人”,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爷爷还是那个样子,只是略微又老了一点儿。
爷爷经常在家,不怎么上地,不时会看一些小说之类的书,或者看些我那时不知从哪里借来的报纸,年纪那么大了,视力却非常好,竟不用戴老花镜。我那时还怀疑爷爷是否真的能看清书上或报纸上那么小的字,甚或真的是装样子在闲度时光呢。但我儿时学习的起步倒确是从爷爷的手里开始的:从认识算盘到常用的计算口诀及应用,以及好多小学低年级的生字都是老爷爷教会我的。不记得爷爷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教我,又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教我,教我那么多语文、数学的基础知识。
那时我也有稍微的好奇和疑心,以为爷爷不是老师,未必懂得许多老师才会的东西;及至后来,也不知怎么竟和爷爷无端地默契融合,竟就自然地把爷爷当成了我的课外老师,无事时就常常在一起坐会儿。等我上四、五年级以及再到离家十多里的地方上了初中后,星期天回家早晚空闲时,也总无由地找爷爷在一起坐会儿。他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的时候多。
每当我在他身边坐下,挨着头一起看不多时,他就自然停下自己的阅读,轻轻地把书伸给我,说:“嗯,你拿去看吧!”开始我还觉得不好意思,一是打断了他的阅读,二是怎么能再拿去看;于是说:“你看吧——”他就又说道:“没事,我看不看都没什么,看也是掩心焦呗!”或者说“你拿去看吧,你看完了我再看。”我那时还只以为爷爷看书真的是“掩心焦”呢,就自然地经常拿回去赏读几天,或者开学了就及时还他,或者就连着几个星期天看完了再还他。现在,我懂了,他那时是把我当做一个热爱学习并喜欢上进的自家小孙孙看的。等还书时见他手边不是放着报纸,就是已经换了其他的书。我只是一边奇怪爷爷从哪来这么多的书可看,一边经常地从爷爷这儿“借”书看,——说得不客气点儿,简直就是拿书看。
初中三年级时,我十五岁,一个星期天,我从学校回来,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说:“西院你老爷爷去世了,前天埋地。”我顿时愣住了,好大一会儿竟不知所措。然后,眼泪汪汪地问母亲,爷爷怎么好好地就去世了呢?——爷爷一向身子骨很好,从来没生过什么病。母亲说:“也没生什么病,只是在床上躺了两三天,不吃不喝,临终时是因为一口痰噎着了!——也就是老病吧。”我那时只觉得爷爷的死像个梦似的,恍惚间还是好好的样子。家里放着前段时间拿的《欧阳海之歌》这本书还没有还,——当时爷爷也只是看了少半就给我看了。整个星期天,我懵懵懂懂地,只感觉爷爷还活着,似乎和往常一样。好长一段时间,我经常猛然间想起爷爷时,心头总是“咚”地跳动一下,爷爷的样子就在我眼前或心里闪现一下的感觉。我也总希望能在梦中再见到爷爷,但不知怎么梦见的时候却不多。
爷爷的脾气并不好,但我却很少见到他生气的样子,多是后来有时听母亲说起的。爷爷在家里为些小事不时会生气或拌几句嘴,我也只是偶尔遇到过一两次。听母亲说,爷爷一辈子脾气着实不好,特别是年轻时,最常见的是和老奶奶拌嘴生气,而且一生气就乱摔东西。母亲说,老奶奶总是让着爷爷。——这倒使我诧异了!爷爷说话结巴,这我知道,但爷爷和我说话总是很慢,话也不多说,我也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异样。母亲说一次老奶奶和邻居婶娘们坐着做针线活聊天时,有人问起了老奶奶:“奶奶,你怎么老是让着爷爷呢?”老奶奶笑了笑,慢慢地说:“孩子们,我能不让着吗!他说话慢,又脾气不好,一生气,更是说了上句接不上下句。
我如果不等他把话说完,他满脸通红地更说不上话来,那不急得要了他的命吗?——一个家的人,能把拌嘴生气当真吗?”母亲说,从那以后,邻居的婶娘们对老奶奶格外尊敬了,各自家里的闲气竟也渐渐自觉地少了许多。老奶奶一辈子身子骨也很硬朗,听母亲说老奶奶活了七十八岁,根本不知道“感冒头疼是怎么回事”。爷爷活了八十六岁,最后也是所谓“无疾而终”。这得多大的福气和造化!
爷爷的家族在村里是过去的“土财主”,大家族,家底殷实,父辈兄弟八九个,满家族大几十口的人。爷爷的父母去世早,因而颇受爷爷奶奶及叔伯婶娘们的溺爱,且颇上了几天学(应该是私塾之类)。常听母亲说“爷爷满肚子文才。”——想来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六、七十岁的人有几个会读书看报的呢?又因了溺爱及上学的缘故,爷爷小时候甚至成家后从来很少上地干过活。等年纪大了,时代变了,再后来土地下放后,需要上地干活了,儿孙辈都已成了劳力,因此一辈子几乎没上过地。
爷爷一辈子清闲,爱看书,甚至好生气,但在我看来都没什么好与不好,只觉得爷爷是我记忆中尤为亲切又很有“知识气”的长者;而且,对我特别地好,是爷孙,但更像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