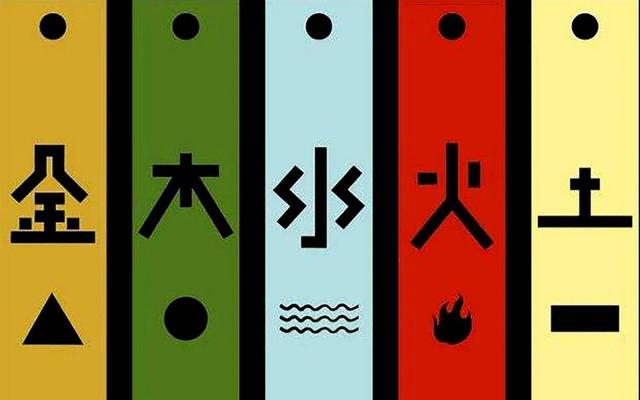读着爽爽,是我们选择长篇小说连载的重要原则...这就是了。

写小说最重要的技巧就是不要给读者耍花腔欺骗读者......
长篇历史小说
《大河之城》
-蔡磊-
第五章 民以食为天
三
关于明仁的买卖,吴冲也有主意:贩茶叶。
理由首先还不在钱多钱少,而是说甘肃茶叶市场目下以湖南人为多,其优势在于,一则有湘军之势可以借助;二来湖南也是产茶区,采购便利。此前很早不是就有了南柜湖南帮的说法吗?吴冲表示,要是明仁有意于此,他可以帮着想想办法。毕竟,江西靠近湖南,说是半个老乡并不为过;再加上自己大小不说,总还是穿着官衣干着官差的官员,还怕愿意巴结的商贩少了?
明仁不无心动。毕竟在商行混过,加之连日来四处留心多方打探,他对兰州商行贸易之事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啦。
本地为商者多在烟行;外省人除山西票号四家外,钱庄、布庄、杂货、木行差不多都是陕西人的天下。至于京货,则是直隶和陕西人平分秋色。绸缎以河南人为多。说到茶叶,又分东西南三柜,南柜为湖南帮,东、西两柜为陕帮。
林林总总算下来,商家商行总有几十近百家,大体上本地人占一半,山西、陕西人占了另一半。茶行湖南帮的异军突起,也是随着左大人到来之后才开始的。这无疑是个机会。明仁细细琢磨着,有买有卖方为买卖,有进有出才成市场。
兰州市场上的输入品为大布、茶叶、洋货、海菜、杂货等等,所输出者却只有水烟、土药(也即鸦片)和羊毛牛皮。皮毛不懂,大烟当然碰不得,剩下的似乎也只有水烟或是茶叶了。

清末抽水烟的女人
甘肃历来就是朝廷养马之地,茶马互市也是古已有之。
见明仁一副难下决断的样子,吴冲开始给他掰开揉碎地讲解起来:大清立国之初,朝廷就在这一带设过五个茶马司,其中一个就在兰州。直到乾隆年间才撤销茶马司,不再以茶易马,允许商人贸易,缴纳税银。也就是从那以后,兰州才一跃成为茶商麇集之地。
那时贩茶,须先纳银请“引”,也就是销售茶叶的凭据,所谓的引有定额,销有定量。“引”有长短之分,也就是销售区域大小不同。后来内乱迭起,兵祸连接,百战余生,城乡残破,官茶片“引”不行,官家少了税银不说,百姓连茶也喝不上了。
左大人现在的办法是,免除以前茶商因为战乱所欠税银不说,还以督印官茶票取代旧“引”,意思就是不论何省商贩,都可以自行领票运销,无须假手总商。而且呢,领票时要是没有筹措到应缴的正课税银,也可请人作保,事后补缴。
知道不,为了鼓励茶商运茶,左大人还和他湖南家乡有协商,凡领有甘肃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由甘肃省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的协饷内抵划。此举可谓一举两得,茶叶商少缴税就能多挣钱,自然高兴;湘、甘两省官府也少了好些扯皮推诿。如此好事,湖南人能不蜂拥而上,成帮成派?
对呀,明仁反诘道:如此好事人家能容得下我横插一脚?火中取栗与虎谋皮,真要有个啥争执,血本无归只怕都是轻的呢……
吴冲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不是说了,有我吗?
你我信。可生意总是我来做,你还能陪着我西北江南来回跑?
吴冲先泄了气:兴致勃勃地半天,全是白说,那你自己拿章程吧。
明仁下了决断:我还做水烟。那行我做过,心里多少有些底……
吴冲略一思忖:真要这样也好。对了,我劝你别走什么北线了,黄河里的皮筏子,我看着就眼晕。那条大河胃口也大,哪年不吞下十几口子去?要我说,你就改走西线如何?
明仁琢磨着:你是说,跑新疆?
对喽,就是新疆。吴冲重又来了兴致:你不是说过,兰州水烟有青、黄之分,黄烟行销西北各省,那为何不把目光转向新疆?两地隔绝已久,内地货品能不大受欢迎?用久旱之盼云霓说话,不为过吧?要知道,不管是朝廷还是左大帅,早都憋足劲要收复被洋鬼子假手他人占领的失地。据我所知,肃州克复之后,打前站的队伍早就开拔啦。你想想,你的货要是能跟官军一起到新疆,能不是头一份、独一份?!
明仁兴奋地双手一拍:好,就是新疆!就是水烟!
越说越近,也越说越热乎,俩人甚至还商定,由吴冲设法通过私人关系在运送军粮辎重的驼队中夹带水烟,这样明仁就可以省去人吃马喂脚夫工钱等一大笔成本费用。这当然是假公济私,说是贪墨也并无不可。所以俩人又击掌为誓——

事出有因,仅此一次;贪得无厌,天打雷劈!
俩人你来我往,总在一起盘算谋划,又因为明仁还是单身,赶上饭点儿,吴冲少不了要留明仁吃饭。有时俩人在明仁屋里说着话,还会让淑惠或是淑秀把饭送来。
淑惠有些纳闷:人家的事你咋那么上心?你过的是啥瘾?
淑秀也有话:就是的,姐夫,衙门那么多公事,你不累呀?每天回来不好好歇着,还不是新疆就是水烟的,那个姓高的真给你喝了鹿血?
吴冲自己也奇怪:说的是呢。我咋就爱和明仁说话聊天,心里畅快,还真不觉得累。
淑秀之所以跑来常住姐姐家,主要是要避开家里那个得意忘形嚣张跋扈的春花。姐姐的家事,她自然只能是点到为止,就是人家不听,她也不宜多说什么。
但淑惠还要冲着吴冲使点小性子:都是你,好好的一个家,看闹成啥了,活活就是个杂耍班子!整天价嘴上说一入官场,折节下腰,斯品下矣,可又跟一个买卖家打得火热……
吴冲却只笑不说话,还是我行我素的样子。
终于,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两口子躺在炕上,吴冲说出了心中真正的盘算——
淑秀是你妹,我这个当姐夫的能不替她想想?看你爹那样,显然是让昔日的丫头春花给拿捏死了。那个春花呢,按你们兰州话说,那就是洋芋开花赛牡丹,张狂得不行。河口那个家淑秀也真是没法待了,要不这回非要跟着咱们,不管你爹咋说都不行?
淑惠一声轻叹:淑秀心里苦,她说过。她说她要是个男人……
吴冲一只手在淑惠胸间游动着,抚摸着,嘴里还在说:这话白说。她当然不是男人,这辈子也变不成男人,但女人可以嫁男人,对吧,嗯?
淑惠先是一声娇嗔:轻点儿,你弄疼我啦。然后又赌气一个翻身,甩开了吴冲的手:你的意思,是说淑秀该嫁人了,是吧?我妹子才跟了咱们几天,你就嫌她吃了你的啊?
吴冲并不气恼,扳着淑惠的肩膀让她躺平了,那只手又上上下下地游走起来:自家妹子,计较那些,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想,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是不是入错行了还真说不好,可那明仁真能是个好买卖人,真的。淑秀要是嫁给他,好事呢……
淑惠动心了,幽幽问道:这是你们谁的意思?明仁提说过?
吴冲笑了:这事还用提说,你没见他看淑秀的眼神呀?
淑惠未及答话,吴冲已经翻爬起身,胸有成竹地开始在淑惠身上动作起来。刚开始淑惠还是不迎不拒,只在心里思谋该怎样和淑秀提说。渐渐地,俩人的喘息声都越来越急越来越重,最终纠缠一处难分彼此……

第二天,吴冲去了衙门,明仁也为筹措买卖之事出门而去,姐儿俩配合默契,将屋里屋外都收拾清爽,小院也洒扫干净后,各搬出个小板凳坐在天井中,家长里短地唠了起来。天空瓦蓝,阳光灿烂,无云无风,在冬春季节动辄风沙弥漫的兰州,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春天早晨的阳光洒在身上,不仅身上暖暖的,心里竟也是柔柔软软,说不出的舒坦。平常日子给娃娃喂奶,不管有人无人,淑惠都是尽量遮遮掩掩的,那天却敞开衣襟,那对饱满的圆润立刻无拘无束弹跳而出,一旁做针线的淑秀先就红了脸——
姐呀,你看你,啥样子嘛!
淑惠不以为然:院门关着,就你我姐妹两个,你就让我放肆一回呗。没听人说呀,姑娘为金,媳妇成铜,一旦有了娃,胸前这对肉疙瘩,就成了猪奶子。除了没长牙的娃娃稀罕,谁还拿它当宝贝?
好像是知道大人们正在说自己,也或许是淑惠怀里正在吃奶的娃娃敏感到少了束缚,只见他伸手蹬脚,嘴里叼一个、手里还霸着另一个,一副憨态可掬的无赖之相。
淑秀摇头,嘴里还啧啧有声:啧啧啧,姐呀,你看你,当妈的一放肆,当儿子立马就成了个不讲理的小霸王。姐夫也不管管你们呀?
管,咋不管,说起来还是当爹的,自己儿子的醋他就没少吃……话一出口,立马知道失言,淑惠脸红了,飞快地瞥一眼淑秀,语不成句地支吾几句,话题也随之一变:我说,你姐夫的意思,想给你提亲呢……
淑秀快人快语:就是那个高明仁吧?我早看出来了……
妹子脸上实在看不出名堂,淑惠不得不问:那你是愿意不愿意?
淑秀停了手里的针线,脸上依然波澜不惊的样子:只要能离了河口那个家,我有啥不愿意的?再说了,那人不聋不瞎又不瘸,对了,还不是个麻子,挺好的。
不管是神情态度还是言辞语句,淑秀的反应都让淑惠有些始料不及,也就不能确定妹子是不是在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家境殷实吃穿无忧,打小爹娘没少在她们身上操心,姐妹俩也都识文断字粗通文墨。
从戏台上看来的大戏折子戏就不用说了,私下里《石头记》《西厢记》也敢看了一遍又一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欢女爱才子佳人看得多了,又是思春怀春的大好年华,难免不对自己的那个人有所憧憬……
如今,妹子对此事答应得如此爽快,急于摆脱那个春花算是个原因,一见钟情还可以是个原因。可她到底是咋想的?万一遇人不淑或者所嫁非人,自己牵线保媒罪过不小且先不说,关键是妹子的一辈子可就真叫毁啦……
见姐姐半天不吭声,只顾盯着自己发愣,淑秀又笑一笑,神情竟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姐呀,你也别七想八想了,我愿意,真的愿意。是女人就总有一嫁,嫁好嫁不好的,不是也得嫁了才知道?不听人家说吗,女人出嫁就是转世投胎!真的,我也想早点转世哩。
淑惠不知道该跟妹子再说点啥,半天终于憋出一句:那我就跟你姐夫说了,啊?
说呗。淑秀轻声一句,依然飞针走线,一副风平浪静神情自如的样子。但右手的针几次扎在左手上……

应时应景蝶恋花
接下来的事情就亦步亦趋全是按规矩来的。
为了婚事早点落实,不管内心多么不情愿,淑秀也不得不捏着鼻子硬起头皮回到河口娘家,以待字闺中的小姐身份,听凭张五爷开始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等相关程序,坐等花轿最后来接人的日子。
这一切也都是张五爷坚持的。祖上传下的老礼,自然是不容马虎。张五爷就是这么说的。
当然,还有好多想法,张五爷并没有说,也没法儿说。比如吧,内心深处,讲究门当户对的张五爷对即将成为自己女婿的那个高明仁其实并不满意——那样的家境也太差太穷了吧!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老祖宗早就讲过的啊。
尽管那明仁现在可以说是个买卖人了,但买卖行里波诡云谲,许多时候翻云覆雨天上地下也只在须臾之间,他是担心闺女日后的日子不踏实不牢靠。正是因为明白闺女的心思,所以他才从心里觉得对不起闺女。
但闺女就是闺女,闺女就是比不得儿子。
这样的,尽管心怀歉疚,觉得闺女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自己逼出门的,但张五爷并不打算改弦易辙,只是在陪嫁上无所不包大包大揽颇显慷慨。
可这又惹恼了春花,从冷言冷语到指东骂西再到公然撒泼,见张五爷不为所动,干脆玩起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忍无可忍,张五爷先指使奶妈抱走儿子,然后指着春花鼻子发了威——
上吊有绳,割腕有刀,要跳黄河,都由你!你看有谁拦挡着你!
春花哪里见过这个?自从跟老爷滚到一铺炕上,尤其是有了身子、果真生下个大胖儿子之后,老爷从来对她都是百依百顺,而且还吩咐家里所有下人都要听她的,所以她也真拿自己当了明媒正娶的当家奶奶啦。
如今看老爷变脸发威,她也就明白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天还是天,地还是地,老爷还是那个老爷,也就依然还是老爷脾气。
作为主要当事人,明仁少不了要一趟趟往河口跑。而且总是乐颠颠喜滋滋乐此不疲的样子。这没办法,此前就是做梦,他也梦不到能娶上淑秀这样可心可意的老婆。
所以呢,他就要竭尽所能倾其所有,只为能顺顺当当,早日抱得美人归。

清朝时花轿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在兰州城还是在河口镇,几次无意间转脸扭头,明仁似乎都能在人群中看到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要说呢,那张脸也没什么特殊,但就是那双藏在草帽下的阴森凛然的眼睛让人不寒而栗,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可那张脸总是神出鬼没飘忽不定的,让明仁总也抓不住。
无论怎样苦思冥想,明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认错了人,更不明白那个人为什么既躲躲闪闪又死缠烂打地跟自己没完没了?
那个人究竟是不是康家湾失踪了的羊倌——也就是那个在械斗失手杀人,然后就踪影难觅不知死活的高明礼?
到底是不是?究竟是不是呢?

明天继续>>>
俗话说,是福不用忙,是祸躲不过。高明仁这心里一犯咯噔,这牵肠挂肚的事就多了。他会做什么呢?如果真是高明礼,当年他爹没有为高明礼娘失踪的事做主,这可就是埋下的“祸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