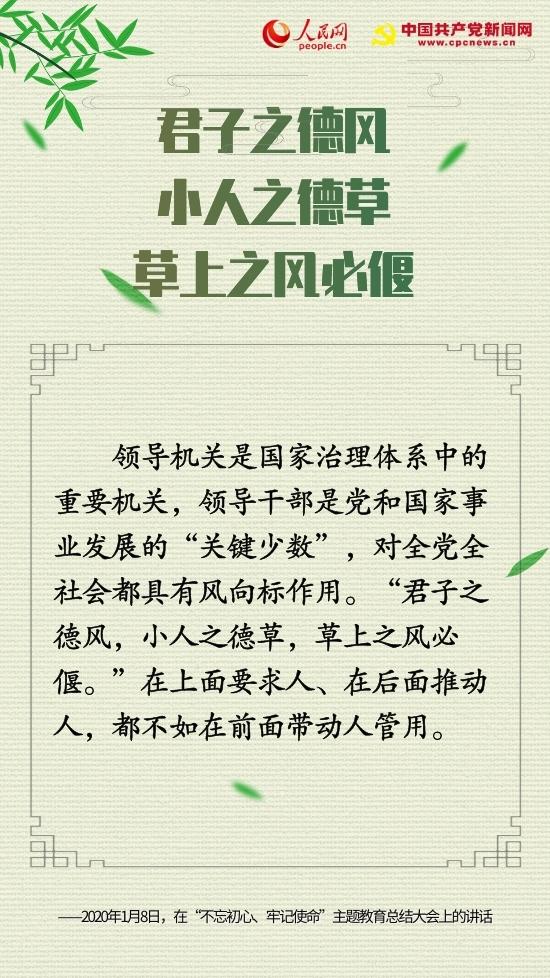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改变了人类的文明进程。著名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曾将文字的使用作为文明的标志,但是早期文字的使用只限于很少一部分上层人物,如埃及的书吏和中国商代的贞人。而且,早期文字表现和记录方式的困难,使得知识很难传播,制约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因此,蔡伦造纸对于知识传播和文明进程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蔡伦,东汉宦官,永元九年(97年)成为监制御用器物的尚书令。他以树皮、破渔网、麻头、破布为原料,发明了一套完整的技术工艺,故称“蔡侯纸”
遗憾的是,蔡伦造纸这件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史实,却因许多所谓的考古新发现而受到怀疑,蔡伦发明家的地位降格为造纸术的改良者。一些学者热衷于用考古发现来推进历史进程,却并不在意深入了解这些材料出土的埋藏背景以及社会因素,导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这种挖宝心态过分膨胀,就会变成冤假错案。比如,英国人道森刻意伪造皮尔唐人头骨,以证明大英帝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而日本藤村新一则以伪造考古现场来不断推进日本历史的源头。虽然“西汉纸”并非故意造假,但是考古发现过程的草率和鉴定的不科学是显而易见的瑕疵,值得我们重视。考古发现对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功不可没,但是对于许多新发现需要做严谨的科学鉴定,而不应该轻易根据单薄的证据就下轻率的结论,甚至贸然改写历史。
早年判断“西汉纸”的主要瑕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鉴定不科学,简单草率。早期的发现都是根据田野工作者的肉眼目测和直觉判断,而且提出西汉有纸断言的科技史专家并无考古学和造纸方面的专业资质。二是没有对“西汉纸”的出土背景做埋藏学或遗址形成过程分析。三是没有考虑“西汉纸”的功能背景和造纸术产生的社会动力。“西汉纸”的发现大抵还处于我国考古学经验主义盛行的时代,还没有科技考古的介入,以及当代考古学对考古材料产生背景进行探索的要求。因此,今天从21世纪的考古学标准来反思“西汉纸”的问题,需要重新评价这些发现的科学性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考古的发展势头强劲,成果斐然,并成为我国考古研究的常态操作。反观过去,像“灞桥纸”这样的发现,在没有经过造纸专家鉴定,考古人员直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自己目测判断的推测是很不规范的做法。所以,考古学鉴定对科技方法的要求,也需要我们对这个武断的结论再做审视和反思。
本文想从现在对西汉纸的专业鉴定,结合考古学对出土材料埋藏学和社会功能背景分析的要求,再次审视“西汉纸”问题存在的瑕疵。
纸状物的专业鉴定
造纸术的基本步骤包括:植物纤维的切断、沤煮、漂洗、舂捣、帘抄、干燥等步骤。而判断手工纸的一个关键特点是所谓的“帚化”,即粗糙的纤维经过打浆处理后被粉碎,使纤维端梢压溃呈丝裂状,形如扫帚。帚化的作用是使纸浆纤维在抄造成纸时提高结合点和结合强度。传统手工方法用纸帘抄纸,纸浆中的纤维经过纸帘滤去水分,形成匀薄的湿纸页。

较为详细的造纸工艺流程:1.切麻,2.洗涤,3.浸灰水,4.蒸煮,5.舂捣,6.打浆,7.抄纸,8.晒纸,9.揭纸
考古出土的古代纸状物无论外表看上去如何像纸,没有这道工艺,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纸。埃及的纸莎草纸和中国古代有丝絮纸,都是纸状的薄片,能够书写,但不是真正的纸张。在2006年出版、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一书中,王菊华和李玉华两位资深造纸专家对主要的“西汉纸”介绍了她们的鉴定结果[1],在此对几件久负盛名的“西汉纸”鉴定结果摘要如下:
(1)“灞桥纸”:可以看到纤维束走向,质地松弛,表面粗糙,没有任何抄纸帘纹的结构。因此,似纸的薄片是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所谓改写历史的“灞桥纸”实际上是铜镜的麻絮衬垫物。

“灞桥纸”,同一方向的麻絮状纤维,出土于汉墓铜镜表面的残布下面,发现时被人为湿化、揭开、并夹入两块玻璃之间压平

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镜显示,“灞桥纸”的纤维很长,质地松弛,纤维间无序靠在一起,无帚化现象。表明是乱麻
(2)天水放马滩“纸地图”:最初根据直观目测被定为“麻纸”,但经专家显微镜观察,表面的纤维粗短僵直,给人以纤维渣的感觉,无明显分丝帚化的迹象。王菊华等造纸专家曾发表专论认为,这张“纸地图”残片边缘裸露有像蚕丝的纤维,应是丝织品。黑点是虫眼,线条墨迹疑是后人画上去的,因为这些墨线绘在残片已经断损的纤维之上[2]。

放马滩“纸地图”,经鉴定其主要成分是蚕丝,残片上看似山川的线条不是入土材料上原有的,而是后画的。黑色斑点不是地理图标,而是虫眼,其中有的虫眼含有墨迹
(3)甘肃居延“金关纸”:小片样为几件絮状片连在一起,结构松散,表面粗糙。内含麻筋、线头、碎布头等,纸面无任何抄纸帘痕迹。原料主要是大麻纤维,未经舂捣、抄造处理,不能看作是纸。

纤维分散不好,匀度不好,纤维束较多,略有起毛,无帘纹抄纸痕迹
(4)陕西扶风“中颜纸”:外观纤维白净,质地粗糙,表面麻段和麻束肉眼明显可见。显微镜观察为大麻类纤维,有许多泥土。纤维分散度差,无帘纹。麻质废料经过简单的切和捶打,晾干成薄片,并未抄纸,但可以被视为纸的雏形。

中颜纸显微镜观察,为大麻类纤维。纤维扁平、孔隙度大、分散度差,无帘纹
(5)甘肃敦煌“马圈湾纸”:专家观察了两件标本,肉眼直观纤维不见明显的碎断现象,纸片结构松驰,但是分散程度较好,不见明显抄纸帘纹,略显麻布纹。显微镜和电镜观察,纤维成分为麻,有中等程度的分丝和帚化现象。马圈湾纸显示了明显的纸结构现象,表面有加填和涂布的工艺。纸样出土在地表下30-50厘米的灰层里,腐朽程度不高,淀粉没有变质。虽然干燥环境能够较好保存有机材料,但是这些有机质能够保存2000年之久仍然有点令人疑惑。专家根据纸样具有一定强度、出现了加填和涂布等工艺,并据可以查到的史料,认为这应该是东汉晚期甚至更晚的产物。

马圈湾纸为麻,中等程度的分丝和帚化。从其他相关证据判断,应该是较晚的产物
(6)甘肃悬泉置纸:1992年发现有20多张所谓“西汉纸”,其中4张有文字。2000年简报提及460余件麻纸,有文字残片10件,其中汉纸9件,专家用放大镜观察了16件样品。该遗址是从西汉到魏晋时期的一处垃圾堆积,由于年代跨度大,环境风沙扰动剧烈,堆积物松散而无规则,很难根据朝代做细致的地层划分。所以出土的纸状物特征也各不相同,主要为麻纤维的成分,还有麦草和蒲草,见有帘纹和布纹。外表直观纤维束较多,纸质粗糙,厚薄不匀。而有字的纸根据书法字体和遣词用字被定为西晋。

悬泉置出土的有字的纸,最初认为是“西汉纸”,后来根据字体和用辞习惯定为西晋

有字悬泉纸的显微照片,原料为麻,纸面细平,白度高。纸浆帚化程度高,不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产品
埋藏学分析
对于我国考古工作者来说,层位学是分辨时代的习见方法。因为老地层在下,新地层在上是一种规律性的堆积过程。尽管有时存在新地层打破老地层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可以从土质差异的比较来判断。然而应当注意避免简单、机械地套用这一方法。总的来说,层位学分析较适用于原生堆积遗址的年代分析。原生堆积是指人类将垃圾直接废弃在活动或居住面上经过长时间的堆积而形成了文化层。
但是,人类活动也存在一种次生废弃活动,即将垃圾清理后丢弃在生活区以外的地点。这种次生堆积是否会形成明显的时代层位韵律就很难说。因为,同一时代的垃圾并不一定定点废弃在同一个位置上,更不用说不同时代垃圾的堆积了。所以这种次生废弃物的堆积往往不会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可言。
一件器物或有机物被掩埋到发现这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在解释某项发现时,决定该文物自埋藏以来是否被扰动或改造,并尽可能重建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对考古学家来说尤其重要。发现物被掩埋而进入考古记录的研究被称为“形成过程分析”。一般而言,地下文物被发现是该文物自然和文化改造过程的最后阶段,需要了解它丢弃、保存、或者在埋藏过程中被破坏、扰动和改造的经过。只有通过对发现物及其相关背景的仔细分析,我们才能了解该发现物品原来的制作和使用功能。
美国考古学家迈克尔·希弗是最早提出形成过程研究的学者,他认为所有考古材料的研究必须从分析它们的基质、出处和共生状况开始。了解这些出土材料的埋藏背境和遗址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变化,涉及到这些材料生产、使用、废弃的生命史。分析形成过程使得我们对过去现象的推断能有更好的逻辑与科学基础,是考古学家对材料进行分析和解释的第一步。

迈克尔·希弗,美国考古学家,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行为考古学的奠基人和杰出倡导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1976年出版的《行为考古学》和1987年出版的《考古记录的形成过程》,主要涉及考古学对人类行为的探索和考古遗址的形成过程研究
从上面提及的几项重要的西汉纸发现来看,当时都没有考虑这些纸状物的埋藏背景和遗址形成过程,甚至根本就不在意形成过程对纸状物保存的影响、以及作为纸张功能和用途的逻辑推理。比如,“灞桥纸”的发现经过完全是墓葬被推土机破坏后的现场清理,谈不上科学的发掘和整理。据报道它与铜镜共出,是在数片残布下面找到的。还有人指出,“灞桥纸”在整理过程中麻絮状物被人用水弄湿、揭开,用镊子夹入两块玻璃中压成纸状物,所以受到了明显的改动,不是原始状态。
放马滩5号汉墓出土的“纸地图”,在棺椁无存、尸骨全无的情况下,居然保存完好是难以置信的。根据埋藏学原理,不同有机物在相同环境里会有不同的分解速率。以动物骨架为例,由于各部分骨骼的质地、密度不同,其分解和朽烂的速率也不同,软骨和纤细骨头分解最快。从放马滩5号墓的保存情况判断,外界朽蚀的营力相当强。纸的质地纤细,其耐蚀性显然远不及硬木制成的棺椁和人体骨骼。如果纸张是与尸体同时被埋入墓穴,从分解朽蚀的速率判断,纸的分解肯定要比棺木和人骨快得多。所以,即使在墓室内发现有纸,也可基本排除它与尸体从开始就共存的可能性,而上面的墨迹甚至是更晚画上去的。
悬泉置遗址是一处垃圾废物堆积区,显然为一处次生废弃的垃圾堆积。这个遗址在沿用四百年里仅留下一二米左右的沉积,平均每年堆积大概只有3-6毫米。有篇研究报告居然能在1.45-2.4米的堆积物中划分出6条水平层位,并能与8个皇帝和朝代相对应,令人生疑。在风沙营力如此剧烈的次生堆积中能判断“按时代堆积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人为主观的臆断而已。像这种垃圾堆积一个时期的废弃物不一定就水平覆盖在前一时期废弃物之上。加上干燥的气候和风沙的剧烈扰动,很难使这种堆积发生固结成层作用。从这种次生堆积的埋藏环境来看,对于这种外界营力改造剧烈的次生堆积,用层位关系来判别时代早晚需极为谨慎,而且用共生关系来推断纸张的年代非常危险,也十分不可靠。

悬泉置遗址,这是一处风蚀严重的垃圾堆积,这种松散的人为堆积一般无水平层位可言,加上自然营力扰动严重,极有可能把不同时代的东西混在一起
功能与社会背景
研究纸史一定要给纸赋以一种功能的定义,即一些原始的类纸物,如果不是专门用于书写,则不应该从造纸术的发明来考虑。其他包装物和人工加工的纸状物,如果不是用于书写目的,也不能从书写载体的发明和创造来考虑。从世界上大部分发明创造来看,20世纪以前多为个人努力的成果。只是到了20世纪工业化的充分发展,才使政府和商业机构成为一些重大发明的主要支持者和赞助人。
对于纸张的发明,根据文献线索,它是因东汉统治者深感“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作为宦官的蔡伦为了迎合上层贵族的喜好而发明了造纸术。《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蔡伦本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行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因此,蔡伦尝试造纸的发明行为可以看作是政府支持下的一种创新工程。
发明与发现不同,后者常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而且往往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的复杂程度密切相关。最早公开宣布西汉有纸的科技史学者自己既非考古学家,也非造纸专家。他在根据灞桥汉墓的发掘简报,提出西汉有纸的观点时,将造纸术的发明归功于西汉的劳动人民,有意贬低蔡伦,其动机和目的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从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相互关系来看,对纸需求的主要阶层恐怕不是普通的下层百姓,而是政府部门和知识界,所以纸取代简帛的主要社会动力应当来自于上层建筑。对于这点,后世文献也有探讨,比如清代何绍基在《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九《纸赋》里提及:“岂云智者创而巧述之,无如上有好而下甚焉”。认为正是朝廷对书写材料有所好,才推动了蔡伦发明纸张以满足贵族阶层的需求。这和过去大力宣传造纸术是西汉劳动人民的发明有明显的抵牾:广大劳动人民可能连字都不识,哪会有发明纸张的动机和念头?
从史前期以及历史时期的重大科技发明来看,一种新发明从诞生到普及应用之间往往有一个漫长的滞留阶段,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关系密切。最明显的例子是火药,它在中国发明后的漫长岁月中主要被用来制造烟火,但是它在传到欧洲后却被用来生产枪炮。这是因为在传统和常规的生产基础上补充一种新技术与建立一种全新的工艺技术,在经济和生产结构上完全不同。它不但涉及到原料的开采和供应、劳力投资、设备、市场需求和贸易规模等社会机能的完善,而且还涉及到工匠的充分培训和能动性提高。所以,有些重大发明在我们现代人眼里看来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经济潜力,但是在原始条件下,它的采纳和普及可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从而常常窒息和延缓了它的采纳和普及。
造纸术与简帛生产属于完全不同的生产工艺,所以造纸术在发明初期所需投入的代价未必一定比生产简帛便宜。这一发明初期所显示出来的优点,可能主要体现在它质地上的潜力。对于造纸术这种需要相当资金和劳力投入的发明,一般来说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地位、经济实力和劳力调遣能力的上层人物才可能予以尝试。而且在没有任何成效可以预见的情况下,要使为糊口而操劳的普通百姓自发从事这种尝试,可能是一种相当不现实的推断。蔡伦身处统治阶层,对纸的作用和意义应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更何况发明造纸术在一定程度上是秉承了皇帝旨意所进行的一项创新工程。
当时,蔡伦的官职已经做到了尚方令,这是一个主管皇宫制造业的机构,主管监督制造宫中用的各种器物。他管辖当时的皇宫作坊,集中了天下的能工巧匠,代表那个时代制造业最高水准。这就为蔡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他的个性、爱好以及他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过人天资,使得造纸术成为他在这个岗位上的集中展现。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向汉和帝献纸,蔡伦将造纸的方法写成奏折,连同纸张呈献皇帝,得到皇帝的赞赏,便诏令天下朝廷内外使用并推广,朝廷各官署、全国各地都视作奇迹。九年后,蔡伦被封为“龙亭侯”,表明朝廷对蔡伦重大发明和杰出贡献的肯定和嘉奖。。
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造纸术的应用和普及问题。纸张这种用品的需求主要是政府机构和知识界,最初使用的应当是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人如当时的统治阶层。可以想象,在纸张发明的初期,它应是一种颇为珍稀之物。只有当造纸技术改进,使纸张能成批生产,并且成本大大下降之后,才有可能被普及到基层供一般老百姓使用。目前主要的所谓“西汉纸”多出土于边疆地区或下层人物的墓葬,这是一个颇令人怀疑的现象:为什么当时在朝廷或统治阶层尚未使用的东西会在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和下层百姓使用?如果在甘肃悬泉置这样的边陲,纸张在西汉已作为平时公文用品却不见于首都和朝廷,似乎不合情理。
小 结
像造纸术这种重大的发明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于西汉,史藉应不会不予以记载。蔡伦的造纸术受到当时皇帝和朝廷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蔡侯纸”,就是官方的正式肯定。如果西汉已经能够造纸,而且已被广泛使用,朝廷未必会对蔡伦有如此高的评价和嘉奖。
造纸术的发明是一桩划时代的变革,它的应用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从某种程度上说,纸的发明最大的得益者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统治阶层和知识界。所以,对于这样重要的事件,西汉的官方记载和知识分子在文字记载上不留一点笔墨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特别是当他们日常使用的简帛被纸张所取代时,不会不留下一些述评和感想。所以,像造纸术发明这样的问题,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历史记载要比一些可疑的考古现象更为可信。换言之,就目前对“西汉纸”所做的科技鉴定结果表明,这些发现不足以动摇史籍记载的可靠性。有些学者坚持这类颇为可疑的考古发现来修改历史,否定蔡伦的地位是不可取的。“需要是发明之母”,从需要来说,古代劳动人民可能识字的不多,基本生计的操劳使他们对书写物品的需求和关切也不会很大。即使有些平民有这样的想法和愿望,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很难使这样的愿望变成现实。造纸术的诞生应被视为当时政治、经济 和文化发展推动下的产物。社会的发展促使具有一定地位的上层人物意识到书写材料变革的意义,并正好允许蔡伦能运用他的智慧、地位和权力来从事这样的尝试,并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人力,经过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才获得成功。
在造纸术发明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纸仍是一种难以推广和普及的用品。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具体事实来看,简帛向纸张的过渡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地方文书到汉末乃至三国两晋仍为简牍,如《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记载“及董卓移都之际...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所允面西者,载七十余乘”,说明东汉皇室藏书主要以帛书为主。而长沙走马楼出土十万枚东吴账册简牍表明,三国时期的普通书写材料仍然是竹简。到蔡伦发明纸张后约三百年的东晋,书写载体的新旧交替才以官方禁令取缔方式而告终结。这就是北宋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卷六百五著录《桓玄伪事》提及的:“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由此可见,纸取代简帛的过程取决于造纸术的改进,只有当造纸工艺改善到一定阶段,使得纸张成本大为下降而可以成批生产之后,才能成为最普通的书写用品。从目前几处出土的所谓西汉纸遗址的整体背景判断,特别是从它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阶层来看,应当说尚不具备使用纸张书写的条件和资格。换言之,如果像灞桥汉墓、放马滩汉墓和悬泉置这样层次较低的人士和帝国边陲的哨所或驿站在西汉已能用纸作为日常的书写载体,那么纸在当时应早已成为朝野比较普及的用品了,然而这岂不与三国时期仍大量用简的事实相矛盾?
最后,从考古学发展的现状来说,科技考古已经成为当下具体实践的常规操作。非技术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对特定出土文物的质地分析,必须请相关科技专家作鉴定,以了解原料产地和生产工艺的信息。过去那种单凭田野工作者个人直觉和经验判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早年发现所作的草率判断和结论,今天仍然对社会产生着负面的影响,“西汉纸”就是其中的一例。造纸专家抱怨,有的博物馆甚至知道展品经鉴定后不是西汉纸的情况下,仍然执意按过去的不实说明展出。表明在某种利益驱动下,有关部门无视真相,不愿纠错的复杂心态。
在科技考古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能够深入分析各种出土文物的材质和工艺,而且也可以对过去所下的结论进行重新的检验,20世纪中叶,考古学者和科技史学者在下西汉有纸的结论时并未首先请专家鉴定,过于草率、很不严谨。造纸专家在《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一书中对西汉纸状物的各种标本提供了权威鉴定,应该对西汉有纸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以后任何讨论有关西汉有纸的问题,应该首先认真和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新的发现,也应该首先将出土材料供专家分析鉴定,在得到他们的分析结果之后才能对外正式发表和报道。
本文相关照片由造纸专家王菊华工程师提供,李玉华工程师在具体细节的说明上也给予了大量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1]王菊华、李玉华:考古发现西汉纸状物的分析研究。见:路甬祥主编《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2]王菊华、李玉华、齐晓东、王玉、王松: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定论不能动摇——对“放马滩纸地图”残片的再观察。载:《纸史和手工纸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造纸出版社,2019年。
信息转自:理寓物内 artifactsandide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