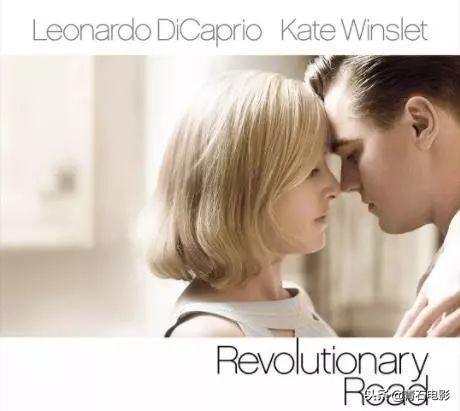新春伊始,万象更新,一转眼又到了出门赏花的季节。也许,论及踏青赏花的心情,古往今来都能给人以愉悦感。古有诗人陶渊明,对着桃花有感而发,写下传世名作《桃花源记》。然而,关于桃园的意象观念却在今天悄然发生改变。那么,从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到现代影视作品中的黑暗桃源,这些年桃花源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桃花源记》的故事流传久远,关于桃花的黑暗传说,常常以非正式的形态,出现于中国的影视作品中。说起桃花的黑化,就不得不提与桃花同为蔷薇科植物的樱花。它们同样花型娇小、耐旱、耐寒。这种转瞬即逝的美,让樱花在日本有着很高的地位。在绝大部分的日本文学作品中,樱花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然而,作为少数的负面代表,坂口安吾的小说《盛开的樱花林下》彻底颠覆了樱花的传统形象,把樱花林描绘为厉鬼索命之地。
小说虽然创作于1946年的战后,却是以作者在战时的真实经历作为蓝本。一天,坂口安吾走在日本上野的樱花林下,看见东京大空袭的死者正在被焚化。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回忆道:“恰好樱花盛开,杳无人烟的林中只有风刮个不停,充满了令人不禁想要落荒而逃的静寂。”于是,以此为契机创作了文学史上的名作《盛开的樱花林下》,提倡爱憎分明、直言不讳的人性化生活。以这个恐怖故事为出发点,坂口安吾否定了战前日本人的观念,提出“生存吧,堕落吧”。樱花也因此被赋予了堕落的含义。

巧合的是,这样了观点也同样出现在具有中国第一网剧之称的《毛骗》中。在坂口安吾的《堕落论》里写道:“人需要在正确的堕落之道上堕落到底,才能发现自我,救赎自我。”而在《毛骗》中主人公一群人也通过以骗治骗的形式,完成他们心中的理想。而他们的目标正是,铲除多年来由黑色桃花源带来的罪恶。一改往日的形象,《毛骗》把《桃花源记》理解为一个经过了粉饰的故事。电视剧对南阳刘子骥寻找桃花源未果,回来后因病身亡的情节做了新的演绎。认为,太守根据捕鱼人的情报找到了桃花源,看到桃花源的富足,太守痛下杀手血洗了桃花源。随后而来的刘子骥,看到饮血变色的黑色桃花惊惧而亡。之后,桃花源作为一个藏宝之地,通过金钱掌控人类。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贪婪的人来此杀戮,从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悲剧。
片中的另一个情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桃花源被黑化处理的原因。片中描述了一处愚公移山的旧址,然而,在主人公邵庄面前,愚公的后人所移之山,早已不是山了。古代人世代移山的壮举,在现代的采矿机下早已不值一提。在古人的伟业面前,现在的人只看到了采山造房的价值,而遗忘了推动发展的初心。
镜与花的意象

当然,《桃花源记》本就是一篇虚构文学,理解也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在文学中,还是绘画中《桃花源记》的虚构性都被塑造的十分明显。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充满了奇景的矛盾空间。比如,桃花开在三月,竹子生长在五月,桑树繁盛的季节却是七月。然而,误入桃源的捕鱼人却同时看到了“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里的人也甚是奇怪,他们虽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他们的衣着却“悉如外人”。因此,有人据此推断桃花源是一个捕鱼人误闯阴间的故事。
当然,这并不能就此说《桃花源记》是一个鬼故事。陶渊明没有选择他喜爱的菊花,也没有用代表高洁的梅、兰、竹,而特意选择了桃花其实别有深意。桃花一般开在清明节前后,因此有桃树辟邪的说法。作为阴阳两界的屏障,桃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代表了“儒与庄禅互补”的文人精神。它要求文人,一方面,要脚踏实地的完成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另一方面,也要依照庄禅思想修身。在理性受到现实打击时,做到独善其身、寄情山水。这也就是为什么,王羲之的岳父在选婿时,没有选择他礼数周全的哥哥们,而选择了在隔壁睡得正香的王羲之,来做他的“东床快婿”。

仇英《桃源图》节选
此外,桃花之阴,也常常代表女性。在中国的绘画中,有空间的内外之分。内意味着女性,是一种私密空间。外代表了男性,是一种公共空间。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桃源图》是一个镜面化的世界,画中一切伦理貌似如常。然而,男女的位置却发生了改变。本该是大门不出的女人却出现在了室外,而应该待在室外的男性反而被留在了室内。在中国古代的绘画中,空间代表了权力。仇英自然也不会挑战正统的礼仪,而是一种强调。仇英反转画面内外关系的做法,实则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于权力相对性的认知。
这种反转内外关系的手法也出现在小说《镜花缘》里。《镜花缘》借由女帝武则天的奇观,反转了整个世界的关系。前半部分,着重描写女权社会中男子的奇妙经历。描写了唐敖科举失意,与经商的妻弟林之洋等人游历各国的故事。作者通过反转的手法讽刺现实让故事看起来奇妙而有趣。而在后半部分,则直接挪用了现实社会男子的生活方式来描绘女子的生活。通过反转带来的反差,凸显了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地方。同南阳刘子骥一样,《镜花缘》里的唐敖也因误食了“仙草”,再也没有回家。在《桃花源记》里‘阡’字代表了通往坟墓的道路,进入桃园的入口也是前窄后宽,像极了 古代墓道的形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许无论现实如何,刘子骥和唐傲到死都没放弃他们的理想。
西方人“游”中国与儒家的“游”文化

如果说《桃花源记》是一篇记录了陶渊明游历虚幻世界的游记。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游”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他的纪录片《风的故事》(Une histoire de vent )里,记录了还是小男孩的他,乘着一架小飞机穿越云雾,来到了中国。他见到了月亮上的嫦娥、醉卧的李白,并与一群中国青年抱着兵马俑迎风奔跑。而后,他静下来凝望这片黄沙,发现自己终于实现了儿时游历中国的梦想,然而此时他已两鬓斑白,年过耄耋。
然而,就算是伊文思这样西方人,也会在结束中国的旅途后感到迷惘。他时常问自己:“我们走了之后,中国人会怎么评价我们?”不仅伊文思如此,事实上,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因为风俗差异而感到困惑。18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体会到了风俗的重要性,他们对中国的幻想也慢慢破灭了。孟德斯鸠认为,风俗操控着人的内在动机,在文化上具有决定意义。西方也就此开始了,对于风俗主导权的争夺。为了体现民族的主导性,孟德斯鸠把“封建”这个原本仅限于贵族的采邑制度,视为了一个地方领主限制人民自由的一种管辖。进而影响到了外交。造访中国的使者约翰·巴罗与孟德斯鸠的思想一脉相承,把中国理解为一个专制国家。对他来说,“中国是个孤单多疑、带着面具的社会,注定停滞与精神贫乏。”这种情况,在1842年后继续恶化,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人纷纷涌入中国。在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前,中国的道德体系也一同遭到了西方人的蔑视。1849年后,中国在政治上已经被遗忘了,移民来到美国西部寻求机会。伴随着1908年美国出台的《排华法案》,中国人彻底的沦为了西方人眼中的工具人。1982年,在詹姆斯·巴拉德的小说《太阳帝国》里中国人大多作为沉默的配角出现,他们往往不是尸体就是暴民。直到西方的殖民政策没落,西方人开始对自己的生存意识产生怀疑,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英国插画家 Tishk Barzanji 乌托邦,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回顾中国的历史,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不仅不专制,反而提倡民主。就算是皇帝的命令,也免不了有被宰相“留中不发”,甚至还会出现“面折廷诤”的局面。论语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待坐》一文中,孔子以启发的方式,让学生们谈谈自己的人生志向。急性子的子路最先回答,他要做一个英雄,通过三年的时间带领一个“千乘之国”站起来。接着冉有谦虚道,他只希望通过三年的时间能够帮助一个方圆六七十里的国家实现经济富足、人民知礼就可以了。轮到公西华时,他表示自己可以在从事国家大事的过程中学习,积累经验,慢慢的实现目标。最后,孔子问在一旁弹琴的曾皙,你怎么看?曾皙回答,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想着春天来了,农忙也过去了。把冬天的衣服一换,穿上舒适的衣服,跟大家一起游游泳,跳跳舞,尽情玩耍后唱着歌回家。谁料到孔子对此大为赞同。难道孔子的愿望真的如此朴素吗?当然不是,只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同样建功立业也是道阻艰难的,多少伟业免不了毁于一旦。而曾皙对描绘的游乐场景,象征着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却是与世长存的。在儒家思想中直线式的“游”作为精英身份的重要标志,能让人在游山玩水中得到自我升华。
“游”是古代小部分人才能享受的时空消费,这也是《西游记》这类小说流行的原因。在今天,人们不再为农忙所困,闲暇时间也可以去尽情的赏花。在自然的观念中,桃花代表了万物复苏,欣欣向荣。而在礼俗里,桃花坞、桃花运,也反映了桃花幸福、长寿的寓意。踏青时节,谁不想走出家门悠闲的去看一场桃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