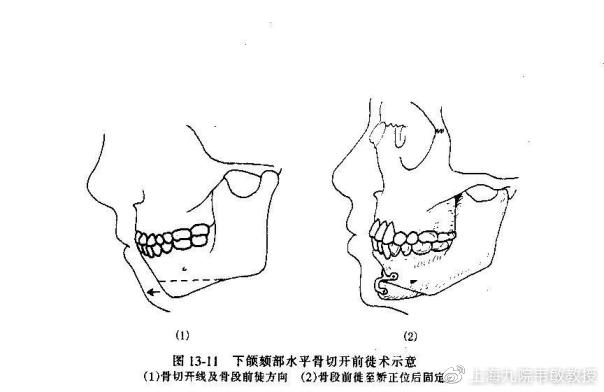撰文 | 文华
整理 | 榕小崧
每到夏天,去咨询整形美容手术的青少年就会变多,其中有很多刚高考完的女孩儿,她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得到成绩的奖励,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储存“漂亮”资本。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整形似乎是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的专属。虽然整形手术耗费不菲,但事实上各个阶层的女性都在整容,包括青少年、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和办公室白领、缺乏技能的下岗中年妇女以及流动打工女性等。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见证了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穷人可以变得富有,农村的可以变成城市的,传统的可以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可以成为中国的。不足为奇的是,有人也相信在“魔法刀”的帮助下,丑小鸭可以变成白天鹅。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促使人们努力抓住出现在眼前的每一个机会。认为美丽是一种资本、漂亮外表是获得机会的关键的想法,刺激了过去十年中国整形美容手术的发展。正如凯西·戴维斯认为,“在一个行动机会有限的环境中,整形美容手术可以成为个体女性通过改造身体来塑造自己人生的办法”。
激烈的竞争,基于性别、年龄、外表和身高的制度化的职业歧视,以及根深蒂固的始终推崇女性美貌的传统性别规范,导致很多女性对自己的外貌产生焦虑并因此整形美容。女性的身体焦虑,很大程度上是由转型时期的社会不确定性造成的。
对很多中国女性而言,选择整形美容与其说是因为虚荣,不如说是为了实用,因为她们相信,更迷人的外表能够帮助她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或配偶、保障婚姻、巩固社会地位或者从农村进入城市。今天的推送,讲述的就是她们的故事。
(以下内容选自《看上去很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报社授权发布。)
为找工作整容“漂亮就是资本”
2006-2007年,我偶尔会走访京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到了夏天,前来咨询或做整形美容手术的青少年和大学生人数会明显增加,其中多数是女孩。
2006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附近坐了一位看起来有点不安的中年女性童女士。她女儿小娟18岁,6月刚考完高考,成绩很好,可能会到北京一所著名大学就读会计专业。童女士遵守承诺,送了小娟价值2000元的双眼皮手术作为高考成绩优秀的奖赏。
以下是我与童女士的对话录音:
我:你为什么会支持女儿做整形美容手术呢?是她自己要求的还是你提出来的?
童:她要求的。我一直知道她不满意自己的长相,她抱怨说没遗传到我和她父亲的好基因……如果是20年前我们那一代,我会要求她保持原本天生的样子。但是现在的社会竞争这么强……她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孩,这几年学习这么用功。如果眼皮上多一道褶子能让她更开心、更有竞争力,为什么不同意呢?
我:你有朋友支持他们的女儿做整形美容手术吗?
童: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支持她女儿整形美容。她女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听说她老抱怨说女儿想找个好工作太难。肯定是这样的,对女孩子来说更残忍,因为她们的机会比男孩少。虽然我一直告诉我女儿,一个人最重要是要有好的性格和能力,但我知道外貌在现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别的父母已经为女儿的外貌投资了,我也得为我女儿做点什么。你知道,作为父母,我要为女儿的将来竭尽所能。为了我女儿的将来,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笔划算的长期投资。
“为了我女儿的将来,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笔划算的长期投资”,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一些中国家长支持女儿做整形美容手术时的态度。这次对话和我在田野调查中搜集的其他对话材料非常类似:父母为女儿支付手术费用,作为通过高考的奖赏或者对她们未来事业、婚姻的投资。
整容题材电影《丑女大翻身》剧照。
从全世界来说,青少年选择做整形美容手术当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在近年来的中国,这已经成了一种特别的潮流。总体来说,中国整容女性的年龄范围比西方女性要年轻得多。例如,根据美国整形美容外科研究院数据:2002年总共进行了约86万次整形美容手术,手术对象大多是女性……其中三分之一的整形美容手术对象年龄在35—50岁之间,另外有22%在26—34岁之间,18%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
陈静,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专业23岁的学生,和很多20岁出头的大学生一样,愤愤地描述了找工作的艰难程度:
说实话,从去年10月开始我几乎参加了所有我知道的就业推介会。……我觉得太可怕了!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为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经过一段艰难的时间后,她意识到外表可能和她的内在同样重要。
我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努力学习,就能找到好工作。所以当班里的漂亮女生和男生出去玩的时候,我却待在图书馆。但是快毕业的时候,漂亮的女生和男生们却比我更容易找到工作。这太不公平了!我特别沮丧!为了得到一个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首先我需要简历上有一张好看的照片。一张大学毕业证不能保证我找到工作,我需要一个优势来突出自己。
陈静下定决心要在北京找工作,她花光了所有兼职的积蓄:
我来自贵州一个偏远的村庄。我真的不想回去,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我家里没钱,在北京也没有“关系”,我不能指望父母帮我找到工作。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留在北京。这是一个讲美的时代!漂亮就是资本!
“漂亮就是资本”概括了这种正发生在中国年轻女孩中的现象,她们把通过整形美容获得美丽外表看作一种投资,认为能给她们带来就业市场上的优势。
虽然迷人外表和性对女性而言是有力资本,她们在使用这一资本时往往会产生罪恶感。为了抵制这种偏见,学者凯瑟琳·哈基姆把情色资本看作是女性在择偶和婚姻市场中的“王牌”,并总结说情色资本是“女性改变自身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倡导女性应该自觉地充分利用情色资本来确保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
在一个沉迷于身体美的文化中,美的确成为了一种资本。然而,关于女性如哈基姆所倡导的那样,有意利用这种身体资本或者情色资本所应该把握的度,仍存在争议。虽然这种资本在短期内对个人可能有用,但从长期来说,它会巩固造成对女性不公和歧视的审美体系,从而剥夺女性的权力。
为婚姻整容:“如荷花般清丽脱俗的女孩”
随着中国劳动力的大量富余,对理想工作的竞争毫无疑问是残酷的。对女性外貌的重视仍旧超过对她们能力和才干的重视,就像另一句著名的成语所说,“郎才女貌”。对女性美的过度关注不仅存在于职场,婚姻中也同样存在。
某天,一则轶事报道吸引了我的眼球:中国一位富豪花了21万元,在上海某家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占据整个版面的征婚广告,并购买了5000份报纸,在上海的大学里发放
(《东方晨报》,2005)
。在广告中,他列出了以下关于理想配偶的要求:
如荷花般清丽脱俗、温柔贤淑的女孩,拥有白皙的肌肤和苗条的体态,身高165cm以上,接受过正规大专以上良好教育,知书达理、秀外慧中,至今冰肌玉骨,身心纯洁,拥有传统的家庭观念,愿意做全职太太的26岁左右的女孩
(教师、医生最佳,在校学生亦可)
,你可愿成为我的灵魂伴侣?期待与你相见!(《新民晚报》,2005)
广告要求,有意向的候选人需随简历寄一张特写照片和两张正面照。这位富豪还允诺,不管谁帮他找到了未来的妻子,都会奖励一次海外旅行。
这则广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过去几年,中国其他大城市各种报纸上都出现过类似广告。虽然男主人不同,却是同一个故事:某中年富商
(通常已离异)
广告征婚。更准确一点,这位理想中的爱人要年轻、美丽、苗条、高挑、受过良好教育
(不过,据推测不能比该男性学历高)
,当然,要是处女。如上文广告中描述的那样,她应该“如荷花般清丽脱俗”。
这些富豪是真的指望通过这种滑稽的方式找到灵魂伴侣,抑或只是想炫耀自己的财富,还存在争议;但事实是,这种广告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到数百甚至数千份女性回复。能花几百万元打广告寻找妻子的富豪只是少数,但是,任何一份带有个人征婚广告的报纸都传达着同一条信息:评价女性是根据“美”和“德”,而评价男性则是根据“富”和“才”,“郎才女貌”的原则从来没有过时。
所以,获得就业优势不是女性寻求整形美容手术的唯一原因,也有人为婚姻而整形美容。
整容题材电影《丑女大翻身》剧照。
我的采访对象高琳就是一位为了婚姻选择整形美容的女性。高琳是位白领,在一家大型IT公司当经理。当时她33岁。当得知我在研究整形美容手术时,她变得兴奋起来,问我能不能给她介绍位好医生,因为她正在考虑做一些整形美容手术。我很吃惊,因为没想过她会考虑整形美容。我对她的印象是不算漂亮,但作为一位有大好前途的事业女性,她看起来很自信。“是,我在工作上有自信,我可能有好的事业前景,但那又如何?看看我,我已经33岁了,还是单身。”她说。过去八年间她爱上过两位男士,但这两段感情都以失败告终,在她心里留下了伤痕。
他们两个都和同一种类型的“小女人”结婚了,就是那种“很女人”的人,小脸蛋、大眼睛、白皮肤、长直发……我肯定不是那种会花一个小时化妆的小女人,我的前男友们总是抱怨我不管身体上还是感情上都没有“女人味”,太伤人了!
年轻的时候,被标记为有“个性”的女性是件很酷的事,现在我已经30多岁了,如果有人说我有个性,我知道那只是一种礼貌的说我不漂亮的方式……我的好朋友们说,如果想要感情有个好结局,我的穿着和举止应该更柔和、更女性化一些,也许她们是对的。老实说,我甚至不知道要怎样跟男人调情……
我的性格太强势,外表也是。脸部轮廓太僵硬,让我看起来更不女人……我可以让自己的气质更有女人味,但是对于长相,除了动刀子我没有别的办法……我的脸又短又宽,是方形的。听说可以做手术让脸变瘦,线条变流畅……我曾经相信一个女人的能力要比美貌更重要,但也许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反正“女为悦己者容”嘛。
高琳想变得更女性化的愿望,说明她即使事业成功,却依旧无法逃脱现存的性别规范。她的解释清楚地说明,对女性美的性别期望,在女性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认知和对整形美容手术的选择中,可能发挥着重大作用。“女为悦己者容”的通常说法,说明对待女性美的“男性凝视”在当今中国仍旧意外流行,尤其是在婚姻市场中。女性不管整形美容与否,都几乎不可能摆脱这种性别期望。
为保住工作整容:从“铁饭碗”到“青春饭”
过去20年,中国国企改制向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投放了数百万处于劣势的中年妇女。对一些中年女性而言,整形美容成为一种保持样貌年轻的手段,从而让她们在找工作时保有竞争力。
47岁的张女士在诊所做接待和杂务工作,比她的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年轻。我了解到,1984年她成为一家国有工厂的工人,但是在那里工作超过15年后,1999年初随着国企改革,她被解雇了。她告诉我:
这个打击太大了。我从来没想过会丢了工作,怎么可能呢?我当时完全崩溃了,丢掉一份那样的工作基本上意味着失去一切……我在下岗前两年离婚了,儿子在上小学。工厂什么都没给我,我只能每月从政府领到280块的失业救济金。1984年,我的第一份薪水是每个月48块,对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到了1999年,280块什么都算不上,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1993-2001年,4300万城镇职工下岗,大致相当于城镇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Dong,2003)
。下岗员工中,71%来自国有企业,19%来自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为了减轻大量人员失业造成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下岗”策略。从技术上讲,下岗和失业不同,下岗员工可以继续与企业保持两到三年的雇用关系,每个月从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200—300元的小额生活津贴。虽然下岗职工收入几近于无,但官方说法上认为他们不算失业。
因此,数千万曾经可以依靠国企终身雇用、端着“铁饭碗”的工人被投放到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就业市场。在各种社会福利都与工作挂钩的体制下,可以理解为什么张女士说“丢掉工作基本意味着失去一切。”
张女士讲述了她作为下岗女工重新找工作的艰难:
我40岁的时候下岗,再也没有“铁饭碗”了。那之后,我努力找其他工作。但对我这样的女性来说,找工作太难了。女性在被解雇时总是首当其冲,再就业时却被排在最后。他们总是聘一些年轻漂亮的脸蛋。我下岗后干过各种不同的工作,甚至当过清洁工,以前我会不好意思干这个。虽然又脏又累,但我不得不接受。在失去那么多之后,我需要抓住能找到的每一份工作。
“女性在被解雇时总是首当其冲,再就业时却被排在最后”,这句话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国企辞退的富余人员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下岗女性找工作比男性更困难。就业市场中因为性别、年龄和外貌,针对女性的职业性别隔离和歧视也让下岗女性处于不利位置。她们中大多数是中年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几乎没有适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在再就业市场中,因为教育和技术水平低下,大多数下岗女性进入了服务业,做家政、清洁、照顾老人的工作,也有些进入了美容服务业,包括理发或在美容院、健身中心、整形美容诊所和医院工作。而且,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下岗工人,年龄歧视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但对女性来说尤其严重,就像《纽约时报》一条引人注目的头条:“在中国,35岁以上女性=不能受雇者”
(Rosenthal,1998)
。
整容题材电影《狼狈》剧照。
我问张女士,如果她经济状况很差,怎么能够负担得起昂贵的手术费,又是怎么找到这份美容诊所的工作的。她说,2004年通过一个亲戚介绍,她开始在这家诊所当临时清洁工。
我不算丑,但是因为干过那些辛苦的工作,看起来肯定比实际年龄老。我想,如果能做免费手术让自己年轻些,可能有更多机会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我也想过我可能不会被选中做手术,但还是拼命想抓住机会。没想到,老板说我长得虽然不好看,但是五官端正,所以做脸部整形美容手术后有机会变得好看得多。几天后,老板同意给我提供免费手术,包括拉皮、隆鼻、去眼袋、垫下巴。作为报答,诊所可以自由使用所有我手术前后的对比照片,进行业务推广。
从工厂下岗后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困难和重返就业市场的希望,是促使张女士做免费手术的主要因素。她讲述了当时内心的恐惧:
我当然害怕做手术。我知道有可能出岔子,甚至还做了噩梦。但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手术是免费的!我怎么能拒绝呢?对我这样的中年妇女来说,找工作的竞争太残酷了。为了更年轻的长相,我当然愿意冒任何险……手术后的第一周,我的脸肿得像个怪物,我害怕极了!当他们终于给我拆绑带后,我松了一大口气。
痛苦而恐怖的手术最终有了回报。在一系列手术后,张女士得到了在诊所全职上班的机会,每个月有800元的稳定收入。可是张女士依然很慌张:
是,我现在有工作,但是看着周围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们,我真怕会再次失去工作。毕竟,在这一行,女人吃的是“青春饭”。
“在这一行,女人吃的是‘青春饭’”,这种说法生动描述了服务业中年女性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尤其是美容业,它的工作制度高度重视女性员工是否年轻、漂亮。张女士肯定不是唯一一个从国企下岗后,为了吃一口“青春饭”而做整形美容手术的人。
为城市生活的梦想整容
在美容院、瘦身中心、发型工作室和美甲店等非正式环境下,女性更愿意讨论有关身体美容的话题,包括整形美容。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赵颖,她是一位20岁的来自四川的美甲师,做过眼睑手术。和前文讨论的女性都不同,赵颖是一位来自农村地区的年轻流动打工女性,即“打工妹”。在大众媒体中,整形美容手术一般被描述成城市女性的特权。所以,我对赵颖的经历很感兴趣,因为它揭露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领域:农村流动女性对美和改造身体的渴望。
总体来说,在美甲店工作的赵颖是个长相普通的女孩,但我注意到她有一双大眼睛。当我赞美她的眼睛很漂亮时,她骄傲地说:“你不是唯一一个夸我眼睛好看的人,有人说过我眼睛像范冰冰,你不觉得吗?”
以“整容”为故事题材的电影《整容日记》海报 。
我问赵颖,她那么好看的眼睛形状,有没有通过整形美容手术提升。她没有直接承认,但在我去过几次美甲店,跟她熟悉起来后,她承认做过双眼皮手术,同时还做了内眦赘皮矫正术。亚洲人眼睑的特征之一是有内眦赘皮,即上眼睑最里面位置上的皱褶。手术去除内眦赘皮后,眼睛的总长度增加,使双眼显得更大。这种手术通常与双眼皮手术搭配着同时做。
赵颖14岁的时候开始外出打工,在2001年离开她的村庄到了四川省的万县。作为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外地人,她最初在外打工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一家小餐馆当洗碗工和服务员。
“那份工作又苛刻、工作量又超大、挣得又少……我一般早上五点起床,半夜十二点甚至更晚才睡。”她说。在忍受了老板一年的责骂后,她离开了那家餐馆,和她妹妹一起去了北京。赵颖说,她离开那个小县城去北京,是因为想“见见世面”。“我好奇城里人是怎么生活的。”她说。从那时起,她在各地当过女佣、服务员和售货员。2006年3月,经家乡一位朋友介绍,她开始在这家美甲店工作,为顾客提供手足美甲服务。虽然她做过的大多是临时性、工资低、不被人尊敬的工作,但修指甲,尤其是脚趾甲,似乎更不体面。但她说她喜欢,因为护理脚趾甲和手指甲是她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
在解释她做双眼皮手术的动机时,她一开始强调女人天性爱美。但是,随着我们谈话的深入,我意识到花1600元——这对赵颖而言是一大笔钱——买一对理想的眼睛形状,包含着比追求美本身更多的文化意义,它涉及到摆脱农村女性一成不变的“土包子”、“小气鬼”形象。
最开始在美甲店工作时,赵颖比其他女孩的顾客要少。一段时间后,老板不高兴地跟她谈了一次话。除了让赵颖练习美甲技术、学着更健谈些之外,老板特别强调说她的样子太“土气”不能吸引顾客,要求她换个新发型并给头发染色。赵颖回忆了她因为外貌和审美品味而被嘲笑是“土包子”的经历:
有一次,一个30多岁的女人来了店里。翻完目录书后,她没有找到喜欢的指甲样式。于是,她要求我自己创新,设计指甲样式帮她画。我在她指甲上试了几种样式,她没有一种满意的。最后,她变得不耐烦,抱怨我没有审美品味,甚至很粗鲁地换了另一个女孩给她画指甲。但是,真正让我恼火的是她大声跟另一个顾客说,我的设计跟我的样子一样俗气。当听到她嘲笑我眼影太重、像熊猫眼时,我尤其生气。
赵颖解释,她以前眼影画得重,是因为她眼睛小,想通过眼妆让眼睛看起来大一些。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空前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农村和城市之间边界的模糊,然而,这却并没有消除农民和城里人在审美品味和身体文化方面的文化边界。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方面,农村/城市的边界依然值得关注。赵颖的顾客批评她的审美和打扮“土气”、“俗气”,这两个词也是城市居民形容农村女性缺少时尚和美感时经常用到的。相反,通常用来形容城市女性的着装和样貌的词则是“时髦”、“现代”。在改革开放后的身体话语中,身体形象和打扮成了区分农村和城市女性的标志。
赵颖决定多花些时间和钱在穿着和化妆上,模仿那些来店里做美甲的城市女孩。但不管怎么化妆,她都不满意她的眼睛形状,在她看来太小了,她梦想有一双像电影明星范冰冰和赵薇那样的大眼睛。在美甲店,赵颖听到顾客谈论整形美容手术,最终决定通过手术改变眼睛形状。她说,从来北京开始,她一般每个月挣400-900元,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寄给她父母,春节期间要回家。但是2005年底,她没有给父母寄钱也没有回家,而是花了1600元在一家私人诊所做了眼睛整形美容手术。
跟其他诊所和医院的这一类手术相比,1600元是低价。但是对赵颖来说,1600元意味着她辛辛苦苦工作两年存的所有钱,为了理想的眼型花1600元对她而言绝对算得上奢侈。但是她买的不仅仅是漂亮的眼睛形状,而是试图摆脱农村女性“土气”、“俗气”、“小气”的成见。她的故事是一个例子,体现了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一个农村流动女孩如何试图通过身体实践来跨过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转变,实现自己变得“现代”的渴望,以及成为一个漂亮时髦的城市女孩、融入城市生活的梦想。
《看上去很美: 整形美容市场在中国》,文华 著,刘月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本文内容整理自《看上去很美》,由出版社授权发布。
作者 文华 整理 榕小崧
编辑 何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