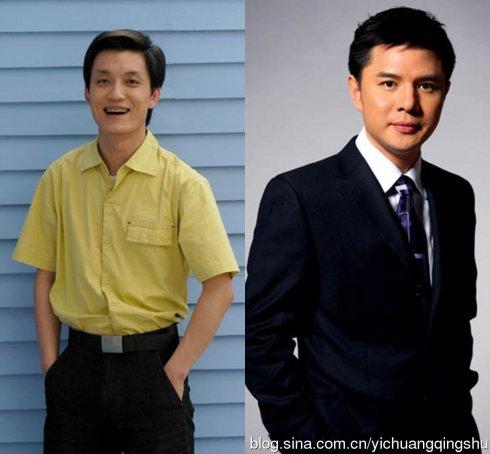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初小玲


北京日报1989年1月24日第001版,第13026期
20元一张票,可真够价!
“乔羽歌词作品演唱会”的票价就这么高。
我想采访乔羽。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轻轻捅了一下蹲在我身旁的娄乃明,她是这次演唱会的导演。“乔羽好接触吗?”我问。她笑着点点头。我又问:“能有的写吗?”她贴着我耳朵说:“‘乔老爷’是很有魅力的老头儿。”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采访“乔老爷”,竟是我来报社十多年来最尴尬的一次。
他说:“我不知道”
我一见到乔羽,就把酝酿已久的问题提了出来:“您的歌为什么让人久唱不衰?”
乔羽慢慢吐了一口烟,面部笑肌把原本不大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缝:“我不知道。”
我一下“卡壳”了,突然发现自己这个问题提得有多傻。
他也许发现了我的不自在,用力吸了口烟,自己说了起来:
“我写的歌词,经人谱曲流传出来的,按比例说,大概只有1%,那99%是不流行的。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那99%的词不一定写得不好,可就是不流行,我有什么办法?”
“您能否说点具体情况?”我需要的不是这些——我心里暗暗想。尽管他说得坦白、真诚,并非矜持,也无做作。
“就说《思念》吧,歌词是10年前写的,也有作家谱了曲,并且都发表了,可就是无人知道。去年经谷建芬谱曲,在春节联欢会上毛阿敏一唱,就流行了。有人说我赶得上时代,可《思念》是10年前写的,10年后它却流行了,真有点滑稽。更可笑的是,去年除夕,我与家人一起看电视,事先我一点不知道当晚毛阿敏要唱这首歌。待电视播完后,我还很纳闷儿,怎么大过节的唱这离别之苦的歌儿?过了一会儿,一个亲戚打来电话:‘听到您的歌了。这歌太好了,自从我们与台湾关系松动,许多人写歌,谁也没写好,怎么您一写就成了……’我拿着电话真是哭笑不得。没有办法,诗是无法解释的,人家怎样理解就是怎样,歌词也一样。”
“那么其它的歌儿呢?”我有点急了。
他仍是慢条斯理,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我写的歌词大多是‘遵命文学’,遵朋友之命。比如说《我的祖国》,那是我1956年写的。当时,我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特约编剧,正在江西写《红孩子》电影剧本。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接连不断地来电报催促我回长影,为《上甘岭》插曲作词。我曾看过剧本,除了坑道就是大炮,这能写出什么好歌词?沙蒙也很固执,电报不断。我索性放下手头的创作,八千里路云和月,赶到长春。看完样片,我被银幕上战士的爱国精神感染了。‘对歌词你有什么要求?’我问沙蒙。他说:‘只希望将来片子没人看了,歌仍在流传。’好家伙,他这一句话可把我憋住了。我把自己关在长影‘小白楼’的房间里,不停地抽烟,不住地喝酒。一天天过去了,沙蒙每天到这儿来看看,喝口酒就走,什么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他是在催我的词呀。10天过去了,我将憋出来的歌词递给沙蒙:‘好歹就是它了。’沙蒙默默看了几分钟,一拍大腿:‘就是它了。’没过几天,沙蒙又找我,让把歌词里‘一条大河波浪宽’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我说,这可不行。这首歌是写家乡、写祖国的。人们都会思念故乡的河,哪怕是家门前一条小水沟,在心目中也是一条大河。这样‘我家就在岸上住’,才使更多的人感到亲切。”
听着他的娓娓叙述,我发现这个“乔老爷”感情原本是挺细腻的。
他接着说,“这首歌词也把大作曲家刘炽憋坏了,四天之后他拿给我看,并唱给我听,嘿,绝对的好!你别以为歌唱家唱歌好听,所有的歌都是原作者唱得最好。你说怪不怪,郭兰英领唱的这首歌到电台录音后,第二天电台就广播了,很快就在大街小巷、乡镇村庄流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他顿了顿,似乎结论就是如此。
“《我的祖国》这首歌写得确实‘漂亮’,可那是作曲界骄子刘炽的‘漂亮’。这首歌传唱后,我们去北京大学,学生们兴奋得把刘炽扔了起来……”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刘炽。
“没人扔你吗?”我笑问道。
“没有。我是一辈子没变成天鹅的丑小鸭,我当时也崇拜刘炽,我都想挤上去扔他。”他倒是挺实诚。“不过我这个人很幸运,我与作曲家合作,几乎都是这些作曲家的创作高潮,黄金时期。刘炽也是如此。”
他说:“歪打正着”
“现在有人称您为剧作家,有人称您为词作家。在您四十多年创作中,究竟以什么为主呢?”
乔羽又眯起小眼睛笑了:“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我的主业是写剧本,我现在是剧协副主席。可现在许多人不知道我写了什么剧本。其实我写了不少,只是没有流行,不流行就算你没写一样。倒是应朋友之约时而写歌词,反倒流行了,这叫歪打正着。说来也有趣,当年我是看不起搞文学艺术的,认为那就是‘玩玩’,哲学、经济才是真正的学问。我很崇拜龚自珍,喜欢他的两句诗:‘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改变了看法,进了由范文澜任校长的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而且是在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剧本创作室与光未然、贺敬之、崔嵬等剧作家在一起。于是之参加革命后演的第一个剧本是我写的《胜利列车》。以后又写了不少话剧本子,都没‘成材’。我这辈子还写过两部电影剧本《红孩子》与《刘三姐》,除此,在剧作上就没有什么大成就。”
乔羽倒是老说大实话。看样子,他把这些都看成是偶然促成的,得失全在一瞬间。但是听了他的关于通俗歌曲与群众关系的一番议论后,我仿佛又有所悟。
那是两天后,我在和平宾馆《挑战——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学术研讨会上与乔羽偶然相见。会议正在发言,乔羽从外面“旁若无人”地走进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真不像话,这不是欺负咱老农吗?在饭店里转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你们在哪儿开会,问服务小姐谁都不知道,怪事……”大家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会议主持人请他发言,他倒不客气:“我先不说中国流行音乐什么时候走向世界,我说一个你们都很熟悉的‘群众关系’问题。流行音乐现在能这样受年轻人欢迎,我说是群众关系好,流行歌曲的歌词有一个特点就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唱,歌词像大白话,为群众喜闻乐见,那些歌星在台上也比较放松。而有些美声歌唱家,一上台,就拿出一副架势,似乎要拒人千里之外,人家不觉得你可亲,怎么能接受你的作品呢?我虽然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但我不回避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这关系到今后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不可轻视呀。”
“乔老爷”这番话真是语重心长!突然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问号:“乔羽没有流传的剧本和歌词,是不是群众关系不好呢?”接着,是另外一个问号:“乔羽得以流传的歌是不是就是因为群众关系好呢?”
他说:“让我想想”
对乔羽的第一轮采访结束了,整理出来一看,从他的嘴里依然得不出为什么“久唱不衰”的答案。不行!我咬咬牙,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又来到航空饭店。我按钟点到了,他还未到。闲坐着无聊,看见郭兰英在楼道闪过,“何不先去找她聊聊”,我追了过去。我正与郭兰英夫妇交谈,乔羽来了,我一时不能中断谈话,等结束后,他又要出去了。真是鬼使神差。我只好硬着头皮与他同去,在行进中的车上,我又开始了新的采访。
“您在不同时代作词的歌曲为什么能流传下来?”我还是固执地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想从他嘴里抠出个究竟。
见我“穷追不舍”,乔羽吸着烟,把头靠在车座背上,“让我想想。”沉思片刻,他这样对我说:“如果说,我的歌词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我注意在不同年代写人民群众心里的真实感情。还是说《我的祖国》这首歌,当时正是新中国诞生不久,这可是来之不易啊,每个中国人都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这种朴实的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那是1948年底,北京即将和平解放,我们这些华北大学的学生,也还是20郎当岁的孩子,可当时谁也不觉得自己小,都顶天立地的。进北京那天,我作为文管会成员,带领长辛店3000工人参加入城仪式,从前门大街进来,别提多高兴了。从北京到涿县有20多个车站是我亲自接手解放的。那时心里对今后祖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那种向往之情真是无法言喻。上甘岭的战士也是怀着这种心情走上战场的,这种感情就是50年代人民大众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我把它融进歌里,再现出来,人民就接受它。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是:‘身在坑道,放眼世界’、‘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坚决消灭入侵之敌……’等等。但歌是艺术,不是口号,我不能那样写,这种创作思想一直贯穿到今天。”
乔羽的这段话使我不由地想起一九八四年,中央电视台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实况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情景:除旧迎新的钟声刚刚敲过,坐在电视机前的许多人此时心里有多少想说的话,对昨天?对今天?对明天?……此时电视机里传来赵忠祥深沉的朗诵:“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不论天涯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歌声响起,多少历经磨难的人热泪盈眶,这首由乔羽作词的歌,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表达了中华民族每个人的感情与祝愿。
我明白了,乔羽在不同年代写的歌之所以能流传,不仅由于他深蕴的创作实力,而且他寻到了艺术的真谛: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去表达这个时代人民大众心底最美好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使乔羽的歌久唱不衰。
昨天,这篇采访写完了,我拨通了乔羽的电话,请他审稿。话筒里传来他那幽默而又浓重的微山湖畔的乡音:“不用,只要不是我自己写我,不会不客观的,凭你的感觉写吧。”
我写得“客观”吗?只好等待“乔老爷”的评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