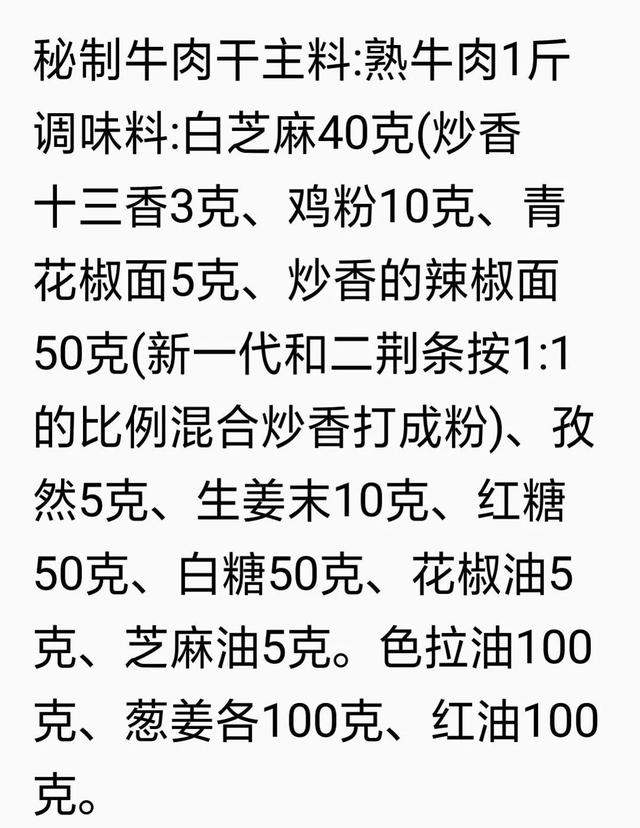芦蒿:红颜青睐的瘦人草
汪鹤年

早春二月,缠绵的春雨把江南的原野润染得如诗如画,一支支芦蒿和着春风的脚步,悄悄地从坚硬的土地里钻出,远远望去,在江堤边、河滩上开始浮动起一片片淡淡的绿烟。大约是其非常惹眼的缘故吧,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诗才会有如此生动传神的摹绘:“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那诗中的意境可说是美到了极致。
东坡先生诗中的蒌蒿,即人们习称的芦蒿。
古时常见的芦蒿两大品种
芦蒿又名水艾、香艾、小艾、水蒿、驴蒿、柳蒿、藜蒿等。据说,因其有减肥的功用,人们又送给它一个美丽的别称——“瘦人草”。湖北地区习称为泥蒿。若按叶型,可分为大叶蒿(又名柳叶蒿)、碎叶蒿(又名鸡爪篙)和嵌合型蒿等3种。如按嫩茎颜色分,人们又将淡绿色的称为白芦蒿,将青绿色的称为青芦蒿,至于紫红色的则称为红芦蒿。而在古代,人们经常食用的主要是青蒿和白蒿两种。
根系发达的芦蒿一般长在芦苇滩上,粗如笔管而有节的根状茎上,长着狭长的似艾的青白色小叶,初生时大约二寸来高。《清稗类钞》有过这样的描述:“蒌蒿为多年生草,生水边及泽中,茎高四五尺许,叶羽状深裂,似艾而阔,背密生灰白色毛。秋日开花,褐色,为头状花序。嫩茎香脃可啖。”
它们刚刚出土时就像是一片野茅针,远远望去,那地面像是铺上了一层紫红色的毛毯。但转眼间,这块硕大的毛毯就由紫红变成灰绿,紧接着铺开的就是一片翠绿。
芦蒿以鲜嫩茎秆供食用,既可凉拌、炒食,又可烧汤,还可腌渍了吃。由于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浓郁的菊香气息,入口外脆里糯,清甜无渣,故深得人们的喜爱。不过,其季节性较强,一旦过了其应市之时,它很快就成为无人理会的一堆废品。故民间素有“二月芦,三月蒿,四月五月当柴烧”的俗谚。
芦蒿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它含有谷氨酸、赖氨酸、多种维生素和钙、磷、铁、锌等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抗癌微量元素硒是公认抗癌植物芦荟的十倍。
中医认为,芦蒿性凉、味甘,有利膈镇咳、清热解毒、开胃行水等功效。《神农本草经》说它可治“疥瘙痂痒恶疮,杀虱,治留热在骨节间,明目”;《大明本草》称其“补中益气,轻身补劳,驻颜色,长毛发,令黑不老,兼去蒜发,杀风毒”;《唐本草》说其“生捣敷金疮,止血止疼良”;《本草纲目》引唐孟诜《食疗本草》还记载了几则验方:“捣汁服,去热黄及心痛;曝为末,米饮空心服一匙,治夏月暴水痢;烧灰淋汁煎,治淋沥疾。”
常用为祭品的野菜
至迟在春秋时期,芦蒿中常见的白蒿、青蒿等就已成为人们熟悉的野菜。
古时,一般称白蒿为“蘩”。对这种生于陂泽,其叶似艾叶,上有白毛,茎或赤或白,根茎可食的野菜,古人深为喜爱,并常用为祭品。《诗经·召南·采蘩》篇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诗·小雅·出车》亦曰:“春日迟迟, 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毛《传》释为:“蘩,皤蒿也。”孔疏:“孙炎曰:‘白蒿也。’”《尔雅·释草》也说:“蘩,皤蒿。”《说文解字》则说得更加肯定:“蘩,白蒿也。”
在一些地区,人们又将白蒿称之为“蒌”。《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三国吴陆玑《诗义疏》:“蒌,蒌蒿也,其叶似艾,白色,长数寸,高丈余,好生水边及泽中。正月根芽生,旁茎正白。”清人桂馥曰:“陆疏云‘其叶似艾,白色’,余目验其叶青色,背乃白色,疏当云‘背白色’,疑转写脱谬。”从陆玑的描写看,“蒌”指的明显是白蒿。

青蒿则被古人称之为“蒿”,或称“菣”,因其根叶青色,气味芳香,俗称青蒿、香蒿。《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孔疏云:“孙炎曰:‘荆楚之间谓蒿为菣。’郭璞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为菣。’”陆玑《诗义疏》也说:“蒿,青蒿也。香,中炙啖。荆豫之间,汝南、汝阴皆云菣也。”《尔雅·释草》中也有 “蒿,菣”的诠释,《说文解字》亦云:“菣,香蒿也。”
不仅在《诗经》中可频繁地读到与芦蒿相关的吟咏,在中国现存最早的星象物候历《夏小正》中也有“[二月]采蘩”的记载。
《左传·隐公三年》则借君子之口说:“[苹蘩蕰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也就是说,当时的“蘩”不仅成为王公贵族喜爱的菜蔬之一,还常被统治者用作荐祭鬼神的祭品。其为人们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战国时,人们已开始将水生白蒿制作成腌菜食用。战国晚期楚国作家景差《大招》中就有“吴酸蒿蒌,不沾薄只”之咏。王逸注:“言吴人善为羹,其菜若蒌,味无沾薄,言其调也。沾,多汁也。薄,无味也。言吴人工调咸酸,爚蒿蒌以为齑,其味不浓不薄,适甘美也。”对其制作要领,《本草纲目》也有过这样的诠释:“谓吴人善调酸,瀹蒌蒿为齑,不沾不薄而甘美,此正指水生者也。”意思是说,当时的吴人已掌握了用水生白蒿腌渍酸菜的方法。
三国陆玑《诗义疏》中还留下了人们蒸吃、生吃白蒿的记述:“[蒌蒿]生食之,香而脆美。其叶又可蒸为茹。”所谓生食之,可能是凉拌着吃。
到了晋代,江东百姓又将白蒿用作做鱼羹的配菜。晋郭璞在为《尔雅》“购,蔏蒌”作注时便说:“蔏蒌,蒌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东用羹鱼也。”
不仅江东如此,连地处西北的陕西及黄河以北地区都是芦蒿的产地。《证类本草》引晋张华《博物志》就说:“芸蒿叶似邪蒿,春秋有白蒻、青蒻,长四五寸,香美可食。长安及河内并有之。”
南北朝时期,芳香尤浓的青蒿更受人垂青,而且往往与香菜一起配用。南朝齐梁时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便有 “[草蒿]一名青蒿,一名方溃。生华阴川泽,处处有之,即今青蒿,人亦取杂香菜食之”一段记述。
当时,人们在制作女曲(糯米作的饼曲)时,还往往将青蒿作为上下两面掩覆曲饼的专用植物。《齐民要术》引《食次》曰:“女曲:秫稻米三斗,净淅,炊为饭——软炊。停令极冷,以曲范中用手饼之。以青蒿上下奄之,置床上,如作麦曲法。三七二十一日,开看,遍有黄衣则止。三七日无衣,乃停,要须衣遍乃止。出,日中曝之。燥则用。”
唐人还喜欢将白蒿用香醋腌渍着吃。唐孟诜《食疗本草》云:白蒿一名蒌蒿,“其叶生挼,醋淹之为菹,甚益人”。
五代时,青蒿亦成为人们腌制酱菜的原料,《本草纲目》引五代时后蜀药学家韩保升《蜀本草》云:“[青蒿]嫩时醋淹为菹,自然香。叶似茵陈蒿而背不白,高四尺许。四月、五月采,日干入药。《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即此蒿也。”
春盘、春饼中的主角
到了宋代,芦蒿已成为人们常食的野菜之一,其吃法也多种多样。
如青蒿,就是人们喜爱的春蔬,它既被人们与香菜一起配用,其干制品还被人们制作成茶饮。宋代医药学家寇宗奭《本草衍义》:“草蒿,今青蒿也,在处有之,得春最早,人剔以为蔬,根赤叶香。……土人谓之为香蒿。”北宋药物学家苏颂《本草图经》:“草蒿,即青蒿也。生华阴川泽,今处处有之。春生苗,叶极细,嫩时人亦取杂诸香菜食之,至夏高三、五尺;秋后开细淡黄花,花下便结子,如粟米大,八、九月间采子,阴干。根、茎、子、叶并入药用,干者炙作饮香,尤佳。”

老饕苏轼对青蒿也情有独钟,他便吃过用青蒿制作的饼,其《春菜》一诗中就有“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骨”的吟咏。而且,青蒿在他立春日所吃的春盘中,亦是常用生菜之一。其《送范德孺》诗就咏道:“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遥想庆州千嶂里,暮云衰草雪漫漫。”对老朋友的深情,也寄托在这小小的春盘之中了。
对青蒿的品种和特征,人们也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宋沈括《梦溪笔谈》:“蒿之类至多。如青蒿一类,自有两种,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谓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桧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独青,气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为胜。”
至于白蒿,也成为人们制作腌菜的原料,有时,人们还将其蒸着吃,《本草纲目》引宋掌禹锡等编著的《嘉祐本草》:“蓬蒿可以为菹。故《诗笺》云:‘以豆荐蘩菹也。’陆玑《诗疏》云:‘凡艾白色为皤蒿。’今白蒿先诸草发生,香美可食,生蒸皆宜。”
黄庭坚还吃过用白蒿下的面条。其《过土山寨》诗就咏道:“南风日日纵篙撑,时喜北风将我行。汤饼一杯银线乱,蒌蒿数箸玉簪横。”
林洪《山家清供》记载的“蒿蒌菜”更有特色:“旧客江西林山房书院,春时多食此菜。采嫩茎去叶,汤灼,用油盐苦酒沃之为茹。或加以肉燥,香脆,良可爱。后归京师,春辄思之。”据说,江西人还常用其制作鱼羹,名之为“蒿鱼羹”。

从苏东坡“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的诗句看,白蒿因有解河豚之毒的作用,还往往成为与河豚配食的野蔬。
或许,是因苏诗的缘故,此后的诗人并未将白蒿与青蒿明确地区分开来,而每以“蒌”或“蒌蒿”作为芦蒿的通称。黄庭坚在《次韵子瞻青菜》云:“莼丝色紫菰首白,蒌蒿芽甜蔊头辣。”陆游《戏咏山家食品》说:“旧知石芥真尤物,晚得蒌蒿又一家。”范成大《满江红》更声称:“任炎天冰海,一杯相属。荻笋蒌芽新入馔,鹍弦凤吹能翻曲。”
明人对芦蒿的不同品种及其主要特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如陈嘉谟《本草蒙筌》对茵陈与草蒿(青蒿)的关系所作的辨析就很有见地:“谚云:‘三月茵陈四月蒿。’人每诵之,只疑两药一种,因分老嫩而异名也。殊不知叶虽近似,种却不同。草蒿叶背面俱青,且结花实;茵陈叶面青背白,花实全无。况遇寒冬,尤大差异。茵陈茎干不凋,至春复旧干上发叶,因干陈老,故名茵陈;草蒿茎干俱凋,至春再从根下起苗,如草重出,乃名草蒿。发旧干者三月可采,产新苗者,四月才成,是指采从先后为云,非以苗分老嫩为说也。”
《本草纲目》对于青蒿与白蒿的记述亦体现出作者独到的观察力,其对青蒿就是这样记述的:“青蒿,二月生苗,茎粗如指而肥软,茎叶色并深青。其叶微似茵陈,而面背俱青,其根白硬。七八月开细黄花,颇香。结实大如麻子,中有细子。”同时,《本草纲目》在指出白蒿有水生和陆生两种的同时,还认为水生白蒿的品质更优:“蒌蒿(这里指水生白蒿)生陂泽中,二月发苗,叶似嫩艾而歧细,面青背白。其茎或赤或白,其根白脆。采其根茎,生熟菹曝皆可食,盖嘉蔬也。”
在充分发挥芦蒿的各种功用上,明人也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如《齐民要术》所记的青蒿罨曲法,在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就被改进为取汁作饼法,其“神曲条”云:“凡造神曲所以入药,乃医家别于酒母者。法起唐时,其曲不通酿用也。造者专用白面,每百斤入青蒿自然汁、马蓼、苍耳自然汁,相和作饼,麻叶或楮叶包罨,如造酱黄法。待生黄衣,即晒收之。”

明人在蒿类野菜的食用上,亦比前人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朱橚《救荒本草》在记叙白蒿的食用方法时就有“采嫩苗叶炸熟,换水浸淘净,油盐调食”的记载。滑浩《野菜谱》还收录了四种野蒿的采集时间及食用方法:“斜蒿,三四月生,小者一科俱可用。大者摘嫩头,于汤中略过,晒干。临时再用汤泡,油盐拌食,白食亦可”;“青蒿儿,即茵陈蒿。春月采之,炊食。时俗二月二日和粉作饼者是也”;“抱娘蒿,丛生,故名。二、三月采,可熟食”;“蒌蒿,春采苗叶,熟食。夏秋茎可作齑,心可入茶。”
高濂《野蔬品》中对蒌蒿、斜蒿和茵陈蒿即有大致类似的记载。
吴承恩《西游记》八十六回中在叙述老妪办素斋酬谢唐僧师徒之事时,对上面提到的蒿类野菜就有过诗意化的描绘:“果然不多时,展抹桌凳,摆将上来,果是几盘野菜。……斜蒿青蒿抱娘蒿,灯娥儿飞上板荞荞。羊耳秃,枸杞头,加上乌蓝不用油。几般野菜一餐饭,樵子虔心为谢酬。”
王世懋《学圃杂疏》还记述了今江西九江等地芦蒿大量外运的史事:“藜蒿多生江岸。九江诸处采卖以数百石船装之远货。吾地亦自不乏。”
在清代的京都,芦蒿已成为市面上常见的野蔬。清郝懿行《尔雅疏》即云:“今京师人以二三月卖之,即名蒌蒿,香脆可啖。唯叶不中食。”
对芦蒿,清代的一些文人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清人马曰管《咏春蔬组诗·蒌蒿》:“厥蒿二月生,细白美盈寸。登柈点吴酸,携筐采下馔。河豚愁腊毒,得此可不论。珍重下箸时,佐我桃花飰。”清诗人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之十五:“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听说河豚新入市,蒌蒿荻笋急须拈。”
在芦蒿的吃法上,清人也有其独创性。如蒌蒿炒面筋,就成为清人曹雪芹笔下贾府中人的一种吃法。《红楼梦》中的小丫头曾说:“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

清童岳荐《调鼎集》所记萎蒿的菜品,则有拌萎蒿、萎蒿炒豆腐、萎蒿炒肉等。至于腌渍类的水腌萎蒿、干腌萎蒿等菜品,也为时人所重。如“干腌萎蒿”就是这样制作的:“取肥大者,不论青红,因其晒干同归于黑。重盐腌二日,取起晒干,入坛贮用。”
如今,芦蒿除了野生的外,还有专在大棚里人工种植的。不过,其香味当然还是野生的更胜一筹。
大约是芦蒿的香味特别浓郁,因而不管你是烹是爆,或汆或烫,都能烹调出独特的口感与不同的风味。喜欢吃荤者,可用芦蒿炒肉丝、炒猪肝、炒牛肉、炒腰花、炒香肠、炒鱼片、炒虾仁,只要烹调得法,自可炒出绝然不同的味道来。至于芦蒿鲜河蚌、蒿干烧鳗鱼、鲜蒿生鳝丝、蒿干爆炒虾、蒿干土鸡汤更是芦蒿菜谱中的荤菜妙品。你要是不想吃荤的,那么可来点素炒,如炒红椒丝、炒香菇、炒香干、炒面筋、炒茭白,等等,也自有其别样的魅力。至于芙蓉鲜蒿羹、芦蒿水饺、芦蒿米糕、蒿香煎饼等,则无疑是芦蒿素食系列中各具个性的精品。
不过,惯于美食者,首推的芦蒿素品还要算是芦蒿炒臭干,此菜经旺火热油一番爆炒,芦蒿的翠绿、清香与臭豆干的乌黑、郁臭便浑然交融成清香爽脆,韵味无穷的素菜绝品,使人吃过一次便久久难忘。至于荤炒芦蒿中的精品,则又非腊肉炒芦蒿莫属,腊肉的暗红与芦蒿的翠绿交织在一起,特别地勾人眼球,那大荤配大素而炒出来的清香,更称得上是顶风香十里的极品。
参考文献(略)
《先民菜篮子里的秘密》(连载)
版权作品:鄂作登字-2017-A-00016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