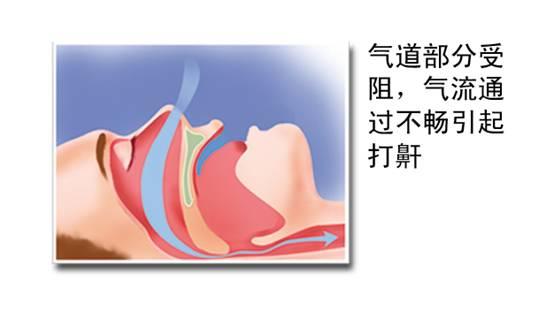锐公司(ID:shangjiezz)报道
作者/ 周慧娴
霓虹灯绚丽的光影将深夜的城市点亮,然而在光明的背后,黑暗依旧将隐秘的角落浸透。
一名小女孩紧咬着双唇,脸颊上还印着通红的手掌印,来不及哭泣,就连忙小跑到了一对青年情侣面前,死死拖住男人的腿:“哥哥,给姐姐买一束花吧。”
黑夜里,总有一群这样“死缠烂打”的卖花女孩,她们成群结队地行走在城市夜生活最繁华的街道,幽灵般地出现在路人面前,强势央求他们购买比市场价高出好几倍价格的玫瑰花。
她们贩卖着同情心,成为路上扯不掉的“狗皮膏药”。然而路人们不知道的是,女孩们有可能前一秒刚被恶狠狠地扇过几耳光,只因没有卖出手上的玫瑰花。
娇俏美丽的花束,在夜灯与月光的映射下,愈显浓郁,仿佛电影里刚刚完成畅饮动作的吸血鬼残留在嘴角的那一抹猩红。
意外的是,女该们坚强、早熟的表情下,似乎对这一切习以为常。她们不寻求任何帮助,只是一如既往的卖花而已,路人们也习以为常,或买或拒绝而已,夜夜如此运转着、流逝着......
本应被父母精心呵护的童真,却被丑陋的交易肆意撕咬,这难道是一种正常?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01
被父母“绑架”的卖花女
“天亮了,太阳升起,人们穿着新衣来到街上,看到小女孩微笑着冻死在墙角”。
这是《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结尾,在微弱的火柴光线下,小女孩看到了爱她的奶奶,微笑地奔赴死亡。
这些顶着烈日、迎着寒风的卖花女孩何尝不是这个时代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有热心市民也曾怀疑这些孩子是被人贩子拐卖而来的,但现实往往更加残酷,有民警顺藤摸瓜调查后发现,很多女孩父母竟然是“幕后黑手”中的一员。
河南省商丘和周口交界的几个县,坐落着不少杂技学校,入学前,家长们就与学校约定好,只要孩子们学成后卖艺,就可以不收取学费。不少学生3、4岁就开始进入学校学习杂技,1年后学成毕业就开始全国巡演,卖艺赚钱。
入读的学生大都是家境贫困,因而有不少家庭将把孩子送往杂技学校当作减轻负担的途径,自然不会在意其学业成绩如何,更不会在意学校如何“分配”孩子们的未来。在家长眼中,孩子们的最终归宿无疑是回归故土,面朝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土地辛苦耕耘,既然结果如出一辙,那么就没有必要纠结之前的人生历程了。
从进入这些杂技学校开始,这些孩子的人生轨迹便已然偏离正常轨道。这些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难免被心怀鬼胎之人盯上。
当地有专门的中介负责与杂技学校联系,从在校生中挑选合适的孩子,被选中的孩子们将会被带到各大城市卖艺、卖花。然而对于这些,家长并非不知情,对于学校的安排他们并不排斥,只要孩子被“出租”到大城市,那么整个家庭还能从中分摊报酬。
河南省贫困地区的杂技学校只是卖花黑产上游链条中最简单的一环。学校并不是这些卖花女孩的唯一来源,在中国各地贫瘠的土地上,还活跃着这样的工作者——有村民专门从事组织孩子外出卖花的营生,相比打工,这是一份更具诱惑力的职业。
02
野火烧不尽
几年前,阿强(化名)在见识到这份职业的“魅力”之后,花了2.8万元买了一辆旧货车,请人将其改装成能容纳多人的“房车”。就着这辆破车,阿强拖着“租来”的孩子们,肩负着孩子父母们的憧憬,奔赴上了他梦想中的财富之路。
为了确保收益最大化,阿强会在孩子们正式“上岗”之前,进行“技能培训”,传授卖花技巧和话术。当然,干这一行不需要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过硬的职业素养,让孩子们尽可能地死缠烂打,卖花事业便已经成功了一半。
上午孩子们睡觉,妻子就会去花店购买便宜鲜花。大伙儿吃完午饭后,下午就得在阿强的监视下“出工”。
阿强是名负责的“老板”,孩子们卖花,他就在不远处监视着“公司”的日常运营,方便进行员工考核。他还自己总结出来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奖惩制度——销量最高的孩子会得到一粒糖或是一小包饼干,但如若有孩子销量垫底,或隐瞒“收入”被查出,则会受到斥责、打骂,甚至不给饭吃。
就这样,阿强麾下的“卖花”新势力就成为了南方某城市繁华街道的地头蛇。
阿强只是卖花大军中的一员,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阿强。
十几年前,卖花黑产便如细菌一样,滋生到全国各地阴暗的角落。各地警察也并非没有关注到这群超越年龄的“狡黠”的女孩。她们就好像烧不尽的野草一般,生生不息。
有警察透露,组织女孩卖花的幕后推手,一般都是同村或邻村的邻居。这些乡邻之间一般存在亲戚关系,就算被警察抓到,由于双方的亲属关系,并且不存在拐卖等不合法行为,因而被发现了也很少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被警察解救返乡的卖花女,会被另一批、甚至同一名组织者重复之前的历程。
就像这样,组织女孩卖花的“暴利”就好似烧不尽的野草,每当春风吹过,便会得到新生。每年,这种低成本的暴利“行业”就好似塞壬的歌声,诱惑着成百上千的村民亲手撕毁亲戚家女儿的未来。
痛心的是,有父母在看到组织女孩卖花的暴利后,甚至会将魔爪伸向自家女儿,拖家带口地卖花。原来,并非所有孩子都在父母的庇佑下,听着童话,“少不经事”地长大。贫穷就像是一面放大镜,无限放大了人性的丑陋。
卖花产业链也给犯罪分子撕开了一大道口子。在利益的诱导下,极有可能出现拐带幼童“卖花”的人贩子;就算女孩们跟着亲戚卖花,女孩们的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曾出现过卖花儿童因“暴利”兜售行为,被路人殴打致死的案例,此外,这些女孩的童贞也很难被守护。
03
被盯上的留守儿童
电影《何以为家》中,主角小男孩的父母打算将年仅11岁的女儿嫁给商贩,为的只是换取价值全家几个月用度的礼金。父母们不知道的是,儿童不应该是自己赚钱的工具。
在我国,留守儿童“出租”的产业链日渐庞大,有不法分子从家长手中“购买”到孩子们的使用权,组织着原本应该在学校用功读书的孩子四处卖花、卖艺、甚至是乞讨、行窃。
此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鲍毓明性侵养女案”就被扒出背后的送养黑产链,一名无辜的孩童被拐卖到网络送养平台,平台管理者假装是孩童的父母,打着“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明天”的借口,将孩子贩卖给恋童癖。
不仅偏远山区的父母将孩子当做赚钱的工具,在城市中长大的父母也不例外。
有父母将自己的女儿租借给 “医托”。有了孩子,“医托”就方便将自己伪装成带孩子看病的患者,这样才能与其他患者搭讪套近乎。还有家长将孩子租借给婚庆礼仪公司充当花童。
甚至有年仅3岁的孩童靠“吃播”赚钱,被父母喂到70斤;5岁的淘宝模特因为“不好好工作”,被父母拳打脚踢;还有8岁童模化着过分浓重的妆容,出现在公众视野……
正如一名母亲所说:“孩子小,更容易引流量,用孩子博同情,来钱快。”但这名母亲忽略的是,这般赚快钱是以牺牲孩子未来作为代价,如此交易实在不划算。
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占未成年人犯罪70%,并呈上升趋势。出租产业链毒害的不仅是儿童的身心,还有我们民族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