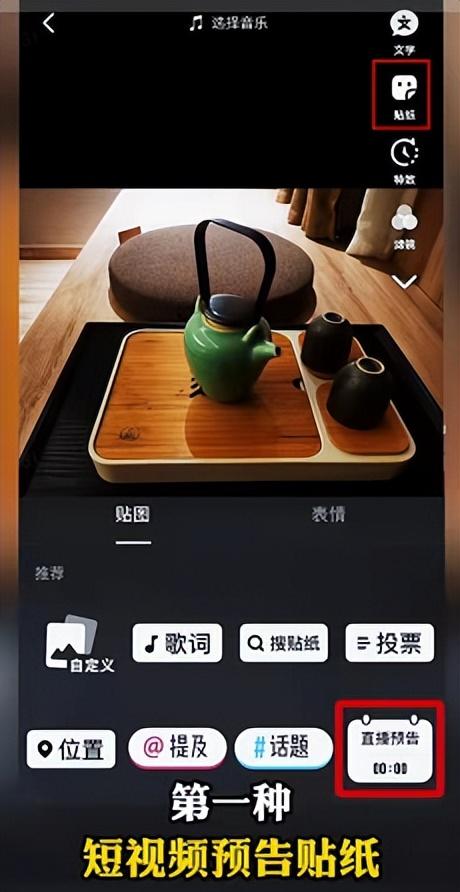大巴车
清晨的微风还有些凉,天空和街道似乎都加了深蓝色的滤镜,两边的椰子树还没有从黑色的剪影中立体起来,远处清洁工的大扫帚哗哗地撩拨着一脸铁青的柏油路面,树上掉落的黄褐色枯叶和大朵的红色木棉花洋洋洒洒在路边的草坪上,石径上。

一个中年女人坐在还没开门的商场前石墩上,面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发呆,手里拿着一叠楼盘广告页。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早就出来。
我和老高眼睛盯着马路的尽头,每出现一个大巴车都会紧张一下,使劲分辨前面的车牌号。刚才身边几个参加一日游的已经准时被接走,而我们的车已经晚了快10分钟了,更可疑的是始终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等候,会不会出了什么差子。手里的广告页已经被我折成飞机,又拆开折成垃圾盒,精美的图片上恢宏的楼盘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车终于来了,比预定时间晚了有二十多分钟。满满一车厢的人,我们如同走红毯一般在全车人的注目下隆重地从车头走到车尾,在最后一排的两个空位上落座。后排的好处是上半身活动相对比较自由,视野也比较独特,全车人的后脑勺一览无余。缺点是靠背不能调整,总得坐得笔直尽量后靠才能让较高的头枕部分垫起颈椎,而不是顶住头向前倾。

同一排的左边坐着另一对中年夫妻,看样子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左前方两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靠边的这位长的珠圆玉润,虽然浓妆,但一张娃娃脸冲淡许多脂粉气,长长的假睫毛下那双藏不住心事的大眼睛在我们从身边经过时呼扇呼扇盯了个仔细。右前方是个慈祥的老奶奶,灰白的头发,一副银边眼镜,干净利索。
导游好像是从港台片里走出来的一个黑社会老大身边的马仔,费力但不讨好的那种,黑西装不系扣,里面是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衫,喋喋不休地用海南普通话(其中普通话占的比重很少)说着一些注意事项,表情和手势都非常夸张,像演一出舞台剧,把每个字的发音都拖到很长,但又控制不住音调和乱窜的舌头,我试图认真听讲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你们是哪里人?”我把目光从导游身上收回转向旁边邻座。我们两个女人坐在中间,两个男人各自一边靠车窗,于是我自觉负担起基本社交任务。在海南旅行团问“哪里人”,如同中学英语课本问“How are you?”,北京人问“吃了吗?”,都是套路。
“山西的。你们呢?”
“啊?我们也是山西的!“
在海南一个月了,感觉所见外地人里90%是来自东北,剩下10%集中了四川,河南,内蒙,北京(很少听说有河北的,都说是来自北京,虽然口音不一)等地,其中山西并不多见。
有一次看田间一个老农种水稻,老农带着套袖和草帽,扬起晒的黧黑的脸大声问我们:“你们是哪里来的?”
“山西!”
“噢!我知道我知道!太原!”
“对对对!”我激动地喊,太原如今这么知名了吗?它可一直是很没有存在感的省会城市啊!
“你们是住在窑洞里吧?”
“呃。。。”

邻座夫妻来自山西侯马,女人的社交能力和我不相上下,交换过所在城市,目前所在小区和海南逗留时间后,所会的套路已所剩无几,老乡见老乡的激动像南方冬天家里的空调,好像是有些暖意的,但又不知怎么才能深切感受和维持。
旁边两个男人听见是老乡感觉是来了兴致,都侧过半个身子,向遥远的另一极打招呼。
大巴车刚上高速,就开始响起了“嘀嘀”的报警声,于是在第一个服务区,全体人员下车休息。
再上车时,我“无意”地走在老高前面坐在了靠窗的位置,回头看到老乡夫妻也换了位置,女人正静静看着窗外。两个男人兴奋地坐在一起。
“侯马我去过。你们那个***厂…, ***企业…”
“是,是,我家就是那儿的…”
我开始昏昏欲睡,断断续续听着两个男人间的对话。
“房价现在多少?”
“现在机场建设,路桥建设啊,对经济带动…”
“俄罗斯…, 乌克兰…”
……
迷迷糊糊中感觉老高一个劲拿胳膊肘碰我:“看外面,看外面。“
“什么?”
我扶扶眼镜向窗外看,向后奔驰的路面,飞快闪过的电线杆和高低错落的椰林和灌木,远处一片波光粼粼。
“万泉河!“老高说。
“万旋活碎~~,亲又亲~~”导游深情献唱。
“嘀嘀嘀……”大巴车又开始报警。
“那个,因为呢,这个,”导游说话时的语气助词相当多,”呃,我们滴车的话呢,是有些问题的了。所以呢,我们决定呢,赠送大家一个景点的啦!当然呢,赠送的话呢,当然是很好的啦,呃,巴厘村!”
“巴黎?村?”

(下集预告:海花岛两日游——巴厘村,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