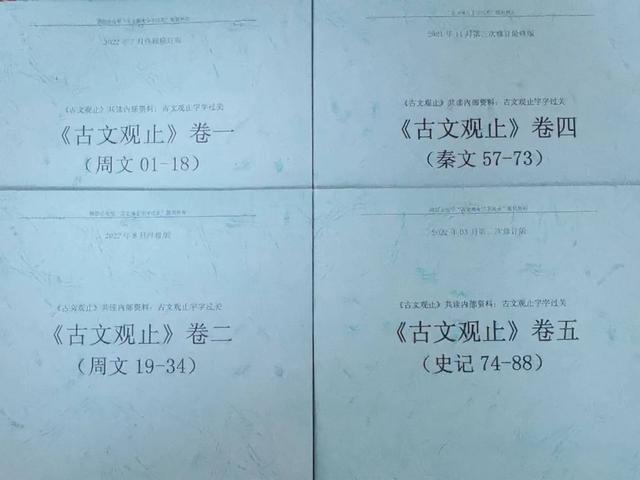每当我认为已经掌握了某个字的用法时,就总是会遇到一些特例,突如其来出现在眼前,动摇自己满满的信心。“而”字就是这样的例子,也可以说,所有最常见的虚词都是如此。
今天读“范雎说秦王”,其中有一句是:范雎谢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若是者,交疏也。”
“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中的“而”字,就令人费解。一般的虚词词典,“而”字可作连词、代词、助词、词缀等等,但这些义项置于此处,都不太合适。
比如,似乎可以作转折连词用,可译为“自己作为一个渔翁却在渭水北岸水边钓鱼而已。”不妥。
比如,似乎可以作递进连词用,可译为“自己作为一个渔翁而且在渭水北岸水边钓鱼而已。”还是不妥。
其他“而”作连词,表并列,表顺承,表因果,表假设,表偏正,统统与文义不符。此处“而”作代词、助词或词缀,就更为不妥。
而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全注全译版本,均置“而”字而不顾,以意译大法规避之。
有的译为“只是一个在渭水北岸垂钓的渔翁罢了”。
有的译为“是个渔父,在渭水边钓鱼。”
有的译为“只是垂钓于渭水北岸的一个老渔翁而已。”
还有的译为“身份只是个渔父,在渭水北岸垂钓罢了。”
除少部分必须意译之外,大多数的意译都是取巧,或偷懒。如果本着学知识、学本领的目的,则意译就更为不妥,因为那样学不到东西。
目前学校也是如此,老师在讲文言文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含糊过去。含糊过去肯定没问题,教育部门规定大纲要求就可以。但是,你含糊过去的地方不要考呀。但事实恰恰相反,某些倡导大语文高居庙堂者,只说读熟就可以。难道读熟之后,这个“而”字的用法就能因为熟而知之?
我很怀疑。我总认为,语文,或者说文言文,本质上不像数学那样吃智商,它只吃积累。而积累,总要有人告诉孩子们吧?孩子们都不知道有这种用法,难道要等孩子们自己去研究不成?难道研究的工作不是像王力、杨伯峻这样的专业工作者的事?他们研究过了,认为这个“而”字,具有某种用法,小朋友们记住有这种用法,今后遇到类似的句子,拿来用就可以了。
可叹社会上皆认为,文言文,只要背就可以了。幸好没人说数学只要背就好了,也没人说,阿拉伯语只要背就好了。
书归正传。我从有限的工具书中查到了一些端倪。
《虚词诂林》P260载杨树达《词铨》,解“而”为陪从连词,与“之”字用同。举例为: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耻其言之过其性;
“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君子耻其言之不见从,耻其行之不见随;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之传命;
杨伯峻《论语译注》P155,注“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中的“而”字时,说“而”字用法同“之”。
杨树达和杨伯峻,都是文言大家,其言可信。
回到本句“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则“而”的用法也等于“之”。那“之”字在这一句中起什么作用呢?
“身”是主语,“为”是谓语,“渔父”是宾语,而“之”是标志定语后置,即“身为钓于渭阳之滨(之)渔父耳”。
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中的“之”,则是取消“言过其行”作为句子的独立性,使“言过其行”像一个名词性结构一样,成为“耻”的宾语。
综上所述,杨树达先生既然认为“而”字与“之”字用同,那此处的“而”更应该是结构助词,而不应该连词。说“而”字是结构助词,更易于孩子们掌握。
原文:范雎谢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若是者,交疏也。”
试译为:范雎道歉说:“(我)是不敢认为这样是对的。我听说,当初吕尚遇到周文王时,(吕尚)自己(不过)是一个在渭水北岸水边垂钓的渔翁而已。像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交往生疏。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