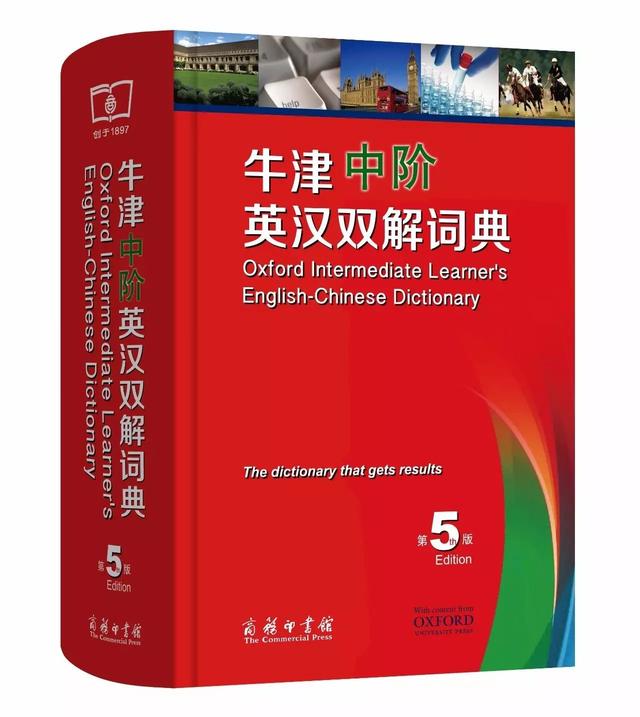有人说:故乡当是你想起来就会热泪盈眶的地方,憎恶故乡的人是无根之人。
我喜欢这句话,“故乡”和“热泪盈眶”对于游子来说是一对近义词。

我的故乡——温泉镇
在游子未成为游子,还是小孩的时候,最向往的是远方,远方有梦中的一切:王子、公主、繁华的街道、精彩纷呈的故事,就连童话中的坏巫婆都肯定住在远方。于是想办法逃离。
我的故乡温泉镇离县城40分钟的车程,小时候去到最多的地方是县城的幺爸幺婶家,幺爸家的女儿,我的堂妹,有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里面有一张真正的书桌,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种课外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儿童版、小学生作文、课堂内外...... 于是这里成了我寒暑假最期待去的地方。
高中去到位于县城另一个方向的小镇就读,县城里排名第二的学校,寄读。当时觉得可真新鲜,真神奇:原来县城的另一端还有小镇呢,在这里还可以向远处延长,冒出一些我从未听过的地名。原来四面八方都有人类聚集地,我们天各一方,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也能各自安然地生活着。
我妈带我新生报名、买好寝具等用品之后就搭车回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生活在新奇的远方小镇,独立的、没有家人在身边。我很快结交了朋友,来自本县各个乡镇的同学、室友,以为我肯定不会怀念那个因我那坏脾气的、嗓门大的妈而减分的故乡。
事实证明,我低估了故乡的分量。每个月末被允许回一次家的月假,会提前几天影响我们的学习情绪和睡眠质量;临放假的周五下午,去挤开往县城的大巴车,是一场校级性的狂欢,连晕车都不再重要了。只能在家度过短暂的周末,周天返校的大巴车上,拥挤的空气里弥漫着沐浴后的芳香,鼻在、身在,心不在。坐在星期天晚自习的教室里,满满一教室人总是静不下来的声音,嗡嗡的,连老师都听不清楚到底是哪儿发出的声音,又远又近。像从深山里往外走,到达最后一个山垭口,刚能眺望城镇,城镇里的密集空气、热浪、嘈杂声一下全涌过来,惶惶然,不知身处何方。
爸爸很有条理,不喜欢我的包裹一袋一袋地散着。为了多和他们待一会儿,我每次都会往回多走一段路,在爸爸的药铺门市上去候车。通常背着一个背包,拎着N个手提袋。爸爸说这样容易随手就漏掉袋子。他便把东西倒一些出来,重新布局,尽量把大布包和背包里的空间利用到极致,减少手提袋的数量。“ 看,这不就装下了。”
有时候碰上他给人输液,或是拿西药、或是抓中药。我就等着他,也不想早走,赖着他说些不重要的闲杂话。待到实在要去门口候车了,?爸爸在药铺里的办公桌后半撑着桌子,腿不方便,也不出门来,时不时看你一下,想起了又交代几句话。“零花钱够吗?再拿两百吧?” “周末放假了,去学校外面吃点好的。”
每次离开,都有奶奶的目送。奶奶半佝偻着身子,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在阳光里虚着眼,留意着路的尽头,那里会出现一辆公交车,载着我离开。上公交车了,奶奶还在那里冲我挥手,说:“路上好生点儿哈,到了记得打电话”
这对母子,一老年,一中年,是我最不舍的人;这幅离别的画面,勾勒着我心底最初、最深的思念。

我的奶奶
家这个词,在离开之后才显得珍贵。
大学去到另一个离家40分钟高速 40分钟大巴车程的城市读书。走得不算远,算是最近的学校了。即便如此,独自坐在离家的大巴车里,看着右边车窗外,流淌在两山之间的河流,也不知是河在追随着车,还是车跟随河,比赛似的并肩去往远方,我还是会头顶着车窗玻璃,不住地想,离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忍不住羡慕起那些永远不离开家的人,甚至嫉妒扎根于此的土地、树木。
再长大一些,又去了更远的远方:深圳、成都。
漂泊,除了让我不再晕车,一定也有其他意义的。城市是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更多机会,更大的上升空间促使人们用脚投票,迈向了那里。
但无论什么时候,心都系在故乡的一小方土地上。它不声不响地提供着能量。
“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从此有了漂泊,有了远方;
异乡安置不了灵魂,从此有了归乡,有了故乡。”
有人选择远方去安置肉身,有人在故乡也能安置灵魂。
我大伯、三婶、爸爸,就是后者,将灵魂安放在故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