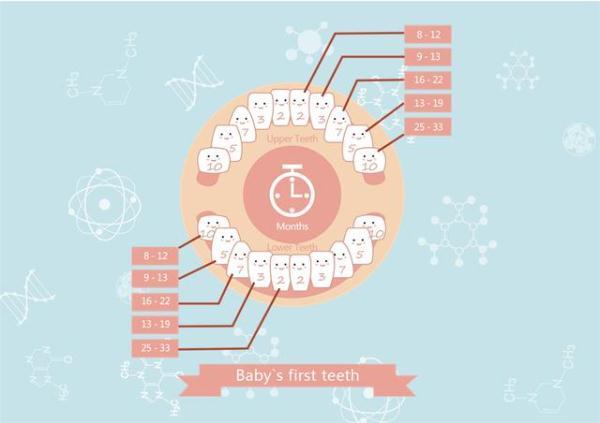《红楼梦》的主旨
鲁迅先生《〈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写道一一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偏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既然能被人看见种种,则种种状况均存在,则《红楼梦》为杂拌儿无疑,因其剪裁有致,可比之为百衲衣。总之,其体裁特别,具独创性,正如托尔斯泰谈及《战争与和平》时说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也非观点鲜明的历史,而是独创性的一部书一样。
至于鲁迅先生所谓,宝玉终于出家,以及认为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的判断,是一家之言。
《红楼梦》的立意,不在小器上,人物的兴衰际遇,是作者“演大荒"的材料而已,所谓更向荒唐演大荒(为什么要向荒唐演大荒,而不向繁荣演大荒,也有得一扯!),什么是大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聊可意喻。其主旨,象《好了歌》与赋所昭示,不是悲,亦不是喜,然其中又有悲有喜,不是小悲情与小欢喜,而是大慈悲与大欢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生生不息的人间戏剧。
贾宝玉的出家,最多是居士,而且是僧是道,颇费踌躇,书中僧道相随,自有深意,一一况曹雪芹最喜谐音喻意,假语村言弄出个贾雨村,甄士隐意谓隐去真事只留实情,连王熙凤小两口打趣时说出个大萝卜还要屎浇(教)的俏皮话儿一一自然而然,一僧一道,暗指亦僧亦道,非僧非道。林语堂谈及中国人的信仰,或者更准确一点叫意识形态(信仰太过执着)时大约说,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年青时多半是法家,中年则是儒家,老了老了,便是佛教,最后是道家。此一观察很有几分神似。贾宝玉的出家,不过是世俗精神的出轨,大半并不在于非得青灯黄卷不可。
《红楼梦》立意主旨如此,又一例证是刘姥姥家的中兴小康与王熙凤的末路的相形相照,此起彼伏,正是生生不息之写照。
这场大戏的最终格局,曹雪芹还没有完成总体的架构,只是正在显露端倪,不意中途撒手,留下许多猜想。
人云:心胸多大,舞台便有多大。正因为立意在演大荒,所以能包容那么多的人和事,所以任何场景都历历如真。巴尔扎克用人间喜剧搭建自己的平台,可谓异曲同工。
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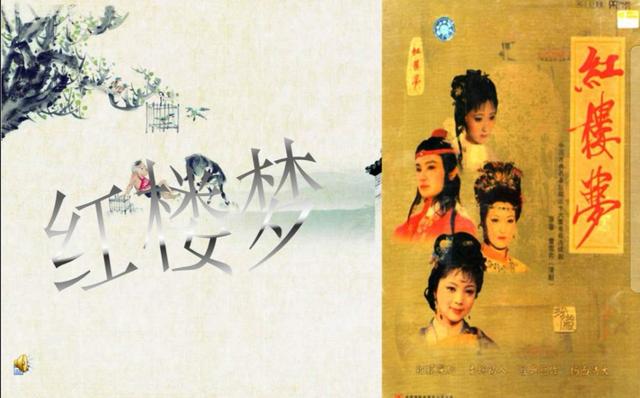
解构《红楼梦》,还原曹雪芹的写作过程。
任何可能都是存在,都可以联系起来。
《红楼梦》研究,不宜注重所谓草灰蛇线,什么伏线千里。任何存在都是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任何事情之间,如果推究,总会有其必然的理由。
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态度以及态度的变化符合她的身份、心态,或者说,作者准确而微妙地描绘,恰如其份地表现出王熙凤的作派,真实,可信。
一一一一一

《红楼梦》索隐派三大分支及其谬误
《红楼梦》研究中有一重要的派系为索隐派。
索隐派的始祖当属康熙大帝,据传他略读过《红楼梦》的部份文字后,说,此明珠家事耳。
索隐派发展到后来,渐渐形成多个分支,其主要者有三,分别为: 明珠与纳兰性德,清世祖与董鄂妃,以及康熙朝政治。
索隐派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其一为蔡元培,此公办学之包容并蓄,为世所称道。又其大力倡导艺术,以为可作宗教之替代,涵养国人心性,为上佳途径。然其研究《红楼梦》而误入索隐之歧途,实未参透艺术之原理。
另有一人,为改革开放之初因短篇小说《班主任》闻名全国的刘心武,他历数年功夫,凭猜想而附会《红楼梦》之文本,名之曰考证,并依其盛名,登央视讲坛,传播其谬误,尚不肯罢休,冒然着笔续写红楼,终于成就一册不伦不类,硬伤处处的《续红楼梦》。
艺术作品,是作者借物传情,表达自己对世事人情的观察,体味,犹如传说中借尸还魂一般。
《红楼梦》所要展现的,依笔者之见,当是《好了歌》及赋所昭示的,好便是了,世间生生不息、变易不居的易的境界,是亦僧亦道(书中一僧一道常常相携而至非为闲笔)的参透领悟,所借助的是闺阁闲情,但所传者,决非闺阁闲情。作者既有参透好便是了的境界,何在意于一家一朝一代的恩怨情仇,在他,那不过是世事纷纷而已。
普希金面对大海,极目远眺,黯然神伤。我们用不着考证他神伤者为何,仍然为诗人的诗所感动。
可是《红楼梦》的索隐者们不干了,他们非得要牵强附会,对号入座,弄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可。
一一一一

《关于<<紅樓夢>>的提纲》
1.<<紅樓夢>>研究不等於其本身,但<<紅樓夢>>值得研究
因此,有许多人,以不同的角度研究它。
2.沒有<<紅樓夢>>也可以。
《红楼梦》,不能当饭吃,有它没它,相信人们照样过日子。有那么多人,一生不读《红楼梦》照样生活。
《红楼梦》本是从无处而来,它没有陈陈相因,而是从无处生发,有论者认为其化自《金瓶梅》,但并不确实。《金瓶梅》与《西厢记》等等,都是他观照的对象。它用一种古怪的结构,包罗万象,有他所熟悉的闺阁闲情,也有他的诗作,也有他的学识,也有他读书听戏时的顿悟。本从无处来的,何妨原本便无,所以有没有它,并不影响世人的生活。有了他,中国人便会高出一头来?没那么严重。
3.沒有<<紅樓夢>>的中國是另一種樣子,有多少人研究紅樓夢?紅樓夢的價值
对于看重《红楼梦》的人而言,对于关心关注中国文学的人而言,《红楼梦》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建筑群,某种意义上,它极象园明园,只是园明园是被毁,而《红楼梦》却是未完。这未完的建筑群还有巨量的工作要做。极有可能曹雪芹到死,还不能预见到它的最终规模与格局。它边回忆边读书边写边改,虽说貌似给自己定下了结局,那不过是一个大致的方向,最终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
《红楼梦》是一部没有范本没有框框的活书,曹雪芹把他的一切,一股脑儿全揉在一部书中。他给自己搭了一个大大的平台,即他所谓的大观园。大观园的建构颇具中国建筑特色,依山傍水,因势而为,不象西方建筑那么讲究对称,追求人工。我们在赞叹西方那些宏伟的建筑的同时,不得不欣赏依山傍水因势而为的园林的自然美。《红楼梦》对金陵十二钗也好,对贾府的兴衰的不同阶段也好,其篇幅的安排,从量上讲,没有进行表面上的结构性的均衡分配,而是顺其自然。何其芳曾经划分过几个主要线索的段落,从中可见一斑。
4.石頭的特征
石頭的寓意,書名在石頭記與紅樓夢之間難以取舍:
石頭的特征與夢的特征兼有,
说它大,它是女娲补天多下的一块石头,它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小说写法上别开生面。
说它小,不过是手中的玩物,是曹雪芹排解时日的寄托而已。百科全书,只不过是曹雪芹个人经历生活片断,看书学习所感所悟的大杂烩,是一件百彩斑衣。
<<紅樓夢>>不是<<康熙起居注>>,它是用線穿成的石頭珠子,是百衲衣,是藝術品
石頭的寓意:可大可小,近看則大,遠觀則小,任何事物都有這一特性,相對於三千大千世界,相對於宇宙,任何東西都是小的,時間也變了.還有一層,這書的本身.痛苦,甚至一個家族與一全王朝的毀滅,也是可大可小的事,廢墟上照樣有芳草起舞
5.夢的境界
夢的機理,用夢的特性使人物分類變得生動,有趣,不是作者生硬的旁白.紅樓夢的人物絕不是自然人的摹寫,是作者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考究後,增刪而成的人物.夢可以壓縮時空.使荒唐成爲可信.
夢具有精神病患者的特徵,也具有藝術思維的特征.
夢者過後要復原丰富生動怪誕的夢境之不易,與寫作的人,要表達其直覺到的藝術境界,有同樣的困難與無可奈何
6.何謂荒唐言
7.偏執的特性,是作者观察的角度;
8.<<紅樓夢>>不可續
9.妙玉的結局

妙玉眼中的寶玉:他無需承擔俗務,故無俗氣,他是唯一可以心神想往的對象.至於後來,她是否屈從於生活,與另一個男人生活一輩子,那必須要經歷一塲苦痛的舍棄,那怕是正常的還俗出嫁,對妙玉而言,都是一劫,那是一種更深刻,更悲壯的苦難.甚好比被劫更为痛苦,而且是不足为外人道,不被人理解与认同的劫,所以如果寫成平常的生活之中的一劫,可能更爲深刻.
寫成高鹗续书那樣,完全是偶然事件,牠完全有可能不會發生,不是眞正意義上的人生之劫.生活的眞正悲劇在於於無聲處的惊雷,在於歲月的銷磨,在於世俗對於年青的心靈的無情打擊.也許這種打擊是不可避免的人生課程,是人生的的成人禮,是對人心的歷練,讓牠長出堅硬的外殼以適應世間的風刀與霜劍,即便如此,這種心路的歷程,也是值得傷悼的.人生也就有了太多的無奈了.因而那些眞正的幸福,才顯得那麽珍貴,那些經歷人生苦難依然保持樂觀向上的人生才那麽值得禮贊.
有些女子生活,表面上看似平靜,其實內心多少波瀾.也許經歷過隱忍的愛情的破滅,那種苦難,不亞於妙玉的被強盜劫持更常見,更不被人重視,甚至有人不以爲然.這才是眞正的人生苦難.
10. 被许多人视为总纲的第五回,其实不足以作为全书的证据
生活作为一种实在,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生活永远无法重复,无论是从体量上还是从时间的丰满性上说,都是如此。任何文学作品,永远只是作品,只是生活的断片,只是某一种角度的观察,它决不是人们伤悼的过去的本身。只要作者愿意,它可以让事情这样也可以那样,这完全决定于作者的心境、审美情趣、取舍判断。没有办法预知未来。文艺作品的这一特征,正与生活本身相似。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总有那么一些不确定性。我们的想往与信念是一回事,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形,又是一回事。
第五回,可以看作集中为一些女子算过一回命。算命是怎么一回事?能作为一个人真实生活的依据吗?
何况,以梦的形式出现,更加不靠谱。梦的解析,正的反的主观的都有。怎可以此为据?
曹雪芹费尽心思,写出个第五回,自然是根据自己对人物的直觉,将人物分了个类。可这最多只能从人物的性格性情气质上去理解。至于实际的生活轨迹,无法以此为据。命运无常。
客观上,第五回加快了全书的节奏倒是不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娜塔莎的命名日以及罗斯托夫返乡之时娜塔莎的兴奋与活泼劲中,我们无法预见她的未来。可是,贾宝玉的一场梦,我们便对人物的命运有了个大致的印象。宝黛初见,不但宝玉心中讶异,读者也觉得两人一定得有点什么,他们是前世有缘!这种先入为主的勾当,从艺术上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1.“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
曹雪芹是天生的情種,他的筆下,沒一個偉男人,要麽象寶玉,要麽象薛蟠,要麽象賈芹等,沒一個能正經成事的.可是女子則不一樣,連老太太如劉姥姥都顯得有主見爲家里辦了一件大事她死時可以無愧地說她爲家庭擺脫貧困立下了汗馬功勞.XXX的老婆兒,生性淫蕩,可就是這樣一個女子與男人相形之下也讓男人顯得那麽齷齪沒出息 “那女子有奇趣一經男人上身便…”
爲什麽只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因爲不未及長大成人,躋身職業男人群中,便家道中落,衹能在寒窗下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了,也把自己的理想,學識,文才全都傾注其中.
<<紅樓夢>>主要的特征: 貌似自傳式,但非自傳,只選取若干塲景加以推演;以因空見色之空包容生活的深廣度;以描寫女性爲中心;用時間與事件來串聯不相干的主題;
12.神瑛侍者給了絳珠仙草什麽水?-----一解:与性有关;二解:作者自况,以心血浇灌而成书,《红楼梦》是边写边改而成,象一粒种子慢慢吸收养份长大。
13.刘姥姥的重要性----《红楼梦》的散点透视
刘姥姥是贾母的清客,贾母的夸耀有了对象;同时,刘姥姥使得大观园的寻常物事,有了不寻常的色彩,距离产生美!贾府的饮食,贾府的摆设,贾府的排场,这些寻常的东西,都引得刘姥姥不停的赞叹,给作者的描述提供了机会,显得自然。
14.非自传、更非政治小说,只是艺术作品,或者说是玩意儿。
15.说好听者是百科全书,说白了是杂拌儿、百纳衣。
16. 摊子铺得太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在日常生活场景及对人物命运的分类式总结,以及社会生活的变故之间,很难取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远远不够。如曹雪芹活得更久,瞻前顾后的修改与增减,不知会有多少。
一一一一
为什么喜欢拿《红楼梦》说事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红楼梦》知道的人较为普遍,雅俗共赏。围绕它来说事论理,不用作铺垫。
与“言必称希腊”相类,用普遍都知道的来阐明观点,比较方便。
一一一一
闲笔不闲
《红楼梦》第六回,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进门前问道时的情形------
“……到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刘姥姥不敢过去,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
看似不经意的笔墨,却是在渲染刘姥姥眼中荣国府的富贵与气象: 先是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好比现在的停车场,满满地泊着各色豪车。就连角门前的看门的人与轿夫,都不寻常,一个个挺胸叠肚,必是活不累,伙食好!还未进门即看出不同寻常,想必被“震”住,急忙掸掸衣服,又教板儿几句话。廖廖几笔,不经意间为后来刘姥姥大观园里“开洋荤”作了铺垫。
《红楼梦》里大事件
黛玉入住
元春省亲
刘姥姥进大观园,刘姥姥促成的集会,胜过诗社。规格高,参与的届别广,活动范围广,把贾府上下抖了个遍,真个是一个大“排场“。
诗社
贾母与林黛玉与刘姥姥
漫说红楼第五回
量子纠缠,同一系统里的响应,黛玉与晴雯,
训诂与红楼梦研究
训诂是拉近,有些红楼梦研究却是误导
梦是什么?梦的“文”“化”特征。
梦是情绪情结统驭下的碎片化场景组合与再现。

《红楼梦》里的人名之谐言会意,个人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偏好,给众多人物起名,总要有一定的方式。至于真事隐,其实与“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的申明相似。任何一个作者,写一个人,只不过是作者从他的角度写他对这个人的观察、看法与判断,比如说,曹雪芹写晴雯“心比天高”,就是一种判断,也许别人不这么看,也许睛雯自己不过是率性,不过是行为举止不掩藏而已。但为什么可信呢?因为世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之人,的确有。《红楼梦》所写的任何一个人物,其性格特征,都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应证,这正是《红楼梦》的“真实”所在。但他所借用的所谓写实,其实是他的观察,有如画家为一幅画作所作的“缩写”,是人物环境给作者呈现的表象。本来就不是对象的本身。这是认识论上的问题,人们对现实对象的认知,来自于现实,又不是现实,只能是对现实的认知。既然认知不等于绝对的现实,曹雪芹所谓的真事隐,实际上是一桩自然而然的事情,说与不说,都是。
个人认为,《红楼梦》的所谓“密码”,不宜过度解读。以人名为例,有人统计,共写了975个人物,有名姓的732个,给这么多人物起名,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他要真事隐去,说白了,是借生活速写为素材,演绎《红楼梦》,自然不用真名,于是用谐音,如贾雨村,甄士隐;于是用“原应叹息”为四个春起名;于是有依职业特点起名的如赖大家的,等等,这些更主要的是写作“技术“上的解决方式。至于张友士问诊之类的情节,当细细品味描写的本真趣味,过度解度得来的结论,不过是想多了。 《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的研究,过多地执泥于考据,与作品的原型与地域,而对其审美与文本本身的美学价值则相对较弱。我们吃蛋一定非得知道是哪只鸡生的吗?
但我觉得意义不大,张三写的与李四写的,还不是一样?我觉得。《红楼梦》只是个艺术作品,是个玩意儿,可以说它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可以说它是个杂拌儿,可以说它是无缘补天的石头记,也可以说它是供人把玩的扇坠。它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已经有了它的生命,再怎么考证,它的审美意义是无法变更的。
我是固执的对考据意义的否定派。这种工作把文学引到故纸堆里去。这种工作,至多只有艺术沙龙意义。
如果说《金瓶梅》好比世态的素描,写真,《红楼梦》则是赋有义理旨趣的文人画
《红楼梦》以闺阁闲情为素材,铺陈故事。
女儿应是水做的,柔,随和,随物赋形,兰天下海水是兰,滴一滴墨立即变黑。
是什么把水变污?是什么让美玉蒙尘?
人生本是零碎事,镇日琐碎自消磨
豪情欲寄凭大风,
1,红楼一曲惊风雨,有字通灵遇慧心。茅椽蓬牖骚经续,吟成奇书作汗青。
2. 无情如何能动人,宝钗行事太精明,随和只为获人赞,低眉顺目博好名
3 红楼莫只看情痴,也须平常看世事,
4,一僧一道一痴人,亦真亦幻如梦境。顽石无缘补天去,历世遭劫演世情。
*红楼考据亦可怜,营营苟苟仔细刊。
吃蛋何须明鸡食,穿衣一定去种棉?
5,艺坛高手曹雪芹,只从闺阁演世情。
6.人生岂能全预料,世事变化无穷尽。红楼判词终是幻,幻梦散尽才是真。
7.满纸荒唐演大荒,世事原本多荒唐。漫言宝玉腻脂粉,雨村审案为大事,营营苟苟荒唐甚。
8.叹宝钗
无情怎么能动人
好花原来为风开
三从四德随人意
痴情公子怨气来。
8,十二钗归纳性与情,未尽,副册与又副册补之
9人生百事都荒唐,且就荒唐演大荒
闺中笑谑情为线,日常琐碎演剧忙
富贵原是人生望,得来却是梦一场
10
人物的命运是飘忽的,就象人生是飘忽的一样,连人生这样对个人那么重要的东西,都飘忽不能完全把握,我们怎么能要求,怎么能确定曹雪芹笔下人物的命运行踪是预先确定好的,是作家埋好了伏笔伏线的?所以,对《红楼梦》的考据是徒劳无益的。
11叹宝玉访晴雯
12.未经离乱与幻灭与变故,则有《闲情偶记》《浮生六记》等等
13依着石头说红楼
心比天高为其大,身为下贱是其微。石头亦是人生之喻
14无年代可考
不猎奇,无大事,中国人的心理,生存状态,
15 妙玉的结局
妙玉的判词-----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的确,依佛门净地的标准,妙玉打开始就未“曾洁”过。明眼一看,她心中有宝玉,无论是品茶栊翠庵,还是琉璃世界雪里寻梅,把少女的情怀表现得那么充分(曹雪芹不惜笔墨!)。
妙玉的眼中,宝玉是唯一可以倾心的对象:除一般年青男子所有的令少女倾心的特质外,无俗气,恐怕是妙玉倾心的重要原因。大观园中,最不用考虑俗务的要算宝玉了,且他又心思细腻,对女子关怀备致,是个多情种,正是妙玉这种不能公开爱人者内心倾慕的对象。也不知他们何时因何缘相见,可以肯定,从那个时候起,妙玉的心中,再也装不进其他的人物了。
但妙玉与宝玉是不可能到一起的,哪怕妙玉在无数的长夜之中作了千万种假设,演出了千万种爱情的传奇。所以,妙玉面对现实时,只有心灰意冷。阳光下的白昼,是那样的寂寞与无聊。
至于后来,妙玉是否继续过青灯黄卷的日子,还是还俗与另一个男人成家过日子,无从考证。可以想见,无论哪一种生活,对她而言,必然有一次内心痛苦的舍弃:舍弃少女心中“不洁”的幻想。
高鹗续书所写妙玉后来被劫,貌似暗合第五回的判词,其实不然。“淖泥”不等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生活本身,是平淡无奇,司空见惯的生活本身,我以为,这才是它的本来面目。生活的真正的悲情在于于无声处的惊雷,在于岁月对人的理想与意志的销磨,在于岁月对于年青的心灵的无情打击。也许,这种打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课程,是人生的成人礼,是对人生的锤炼让它长出坚硬的外壳以适应世间的风刀与霜剑。即便如此,这种历练也过于悲情了些,令人叹息。因此,人生也就有太多的不完整不圆满,也就有了太多的无奈。许许多多的人生就象被山间石头压迫下生长出来的灌木,未免歪歪扭扭。从病理学的角度而言都有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心理缺失。
这就是生活,曹雪芹所谓“淖泥”,妙玉那般人物所面对的“淖泥”。它不是偶然事件可以寓意得了的。因为偶然事件可以发生,可以不发生。偶然事件不足以说明世俗生活何以是“淖泥”。
有些女子的生活,表面上看似平静,其实内心多少波澜!爱情理想的破灭,比比皆是。中国人将较为典型的情形,归纳进民间传说之中,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型的,有白蛇许仙型的,有牛郎织女型的,等等。那种苦痛,对于身受的人,不亚于妙玉的被劫。因为生而被劫,相对偶然性更大,它可能不会发生,发生了还可以被解救。而心灵的理想被日常看不见的风刀与霜剑所侵蚀,才是最残酷的。那是一种更深刻,更悲壮,更令人束手无策的苦难。这种种苦难,比高鹗所谓的妙玉的被劫更常见,更不为忙忙碌碌的自以为是被生活打磨得心里长起老茧的人所重视,甚至还要不以为然。这才是真正的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痛苦,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假使,曹雪芹写完他的作品,妙玉的结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

画“蔷”的深意
《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写宝玉见一女孩子在地上画“蔷”,痴痴地在雨中傻看。也许,他怎么也想不到,也不愿想这女孩儿画“蔷”的深意是恋爱上贾宝玉之外的男子 。
待到第三十六回,写及“识分定情悟梨香院”,才了解画“蔷”的女孩儿的深意。这一刻,宝玉灵机发动,有了很大的很重要的心灵触动。画蔷一节,对局中之椿龄,是深爱的流露,对宝玉而言,是人生的顿悟,这顿悟帮助他走出迷幻的童年的痴愚,渐渐看清自己。 这是宝玉走出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识的重要一步,原来,天下并不是他自家的,并非所有的人都向着他,识定分,这是他正视社会的开始。
其实,任何人,都有这一步,只不过程度不同。任何人,都有从倍受保护与溺爱的环境中走脱出来,面向社会与人生的过程。曹雪芹深切地了解这一过程,这是心的失落,更是人生的开始。
更大的“定分”其实不是,或不仅仅是认识到女孩儿各有各的归宿,而是后来知道大观园跳不出轮回的规律,新陈代谢,势所必然,才有所谓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之类的说道。《红楼梦》正是以轮回作为大背景,展示一个人所见识的一群人的幸与不幸,展示变故中人们的生态。
大观园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经营,大限来时,经营是没有用的。大限就是制度上的轮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变故。
识定分,是人生自觉的开始,也是人的理性的归宿。所谓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岂不也是识定分么! 另一面,知人识人,也是识定分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也算得识得了定分。每个人,各有各的定分。
凡此种种, 如果深究下去,画“蔷”情节中的深意之外,还有更深更广的意味。

红楼片语
谈《红楼梦》者甚众。单是评说《红楼梦》的所谓名家,可以列出一大串:胡适、鲁迅、王国维、俞平伯、蔡元培、何其芳、周汝昌、王蒙,等等。但是他们说过之后,我辈仍有要说的,相信众多的后人也有要说的。《红楼梦》说不完,此话有两层含意,一是指评说《红楼梦》的人永远没有完结,另一个意思是说,《红楼梦》给人的启示是说不完的。《红楼梦》好比文学领域的胜迹,前赴后继不断有人登临凭吊,话转致此,终于可以借用孟夫子的诗: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说《红楼梦》是伟大的小说,自然是不会错的,正如说有钱人富足无虞,说穷人日子艰辛一样的不会出错。所以,如果不是真有所悟,难免人云亦云。但话说回来,《红楼梦》的价值也正在于世世代代不断有人读、有人说。这样一想,似乎谈谈《红楼梦》,也算不上无聊。
得说一下我与《红楼梦》的缘份,我最早看见《红楼梦》大约在初中时期,那时还不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那时我们的课本里并没有提《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当时村里有位在外当干部的人回乡,经常带些学习资料回来,比如介绍美国的农业,日本的科技的资料,也带回供批判用书如《水浒》及《红楼梦》。
他家主场院是个热闹处所,人们喜欢聚在那里聊天,听他讲外面的见闻。一次上他家院子里玩,偶然见到《红楼梦》,便拿来翻了翻,不认识的字很多,同时书上的话怪怪的,看不懂。村里赤脚医生见我翻看,很严重地说,这书小孩子绝对看不得。那时村里固然有很多奇怪的禁忌,专门针对孩子的也不少,比如,小孩子吃泥鳅黄鳝写字手颤,女孩吃猪血将来做女红会不干净,吃鱼籽将不认不得称杆上的星星点点。但赤脚医生说到《红楼梦》时的郑重其事的表情,到现在还记得。因而《红楼梦》这书还真的钩起了我的好奇。只是,一时得不到。
大学里,才正经读过《红楼梦》,虽未能解悟,已品出点味道,盖因那时读过相当作家的书,有了些直觉的鉴赏力,只觉得有的书读一遍足矣,可有的书,读的次数越多越有味道,《红楼梦》即属此类,且还题过一诗云:红楼一曲惊风雨,有字通灵遇慧心。茅椽蓬牖骚经续,吟成奇书作汗青。诗虽题,但《红楼梦》的好处,并未真的细细品味出来。
《红楼梦》这等诗化的“史”,比观念化的“史”更为真实直观,它呈现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生存模式,这种模式中暗藏着历史的必然。
面对《红楼梦》,自以为与作者心心相印,自作解人者甚多。但其实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红楼梦》。
世间大事已让人做尽,诚如歌德所说,凡是值得占据的地方,早已有人占据着(大意)。所以我等凡人,每日上班重复着每天压根儿也谈不上创造性、与崇高伟大无缘的工作,挣够家用之余,无事可干,于是读些闲书。自然也读《红楼梦》,读后也偶有所悟,自得非常,忍不住记下。过后反观,所思所想,未免牵强,因题曰“红楼”附会。
《红楼梦》的语言基因独特,富有多义性,见出作者的超脱、大视野与精到的观察与感悟。观察二字,其实有两层念义,观为看,视而不见、观而不察者世间该有多少,故屈原有诗:荃不察兮余之衷情。但曹雪芹能察善观,悟得深悟得高远,故有如此这般《红楼梦》。文如其人,则其语言随处可见其特质。我名之为语言基因。今摘取文中字眼加以穿凿附会,试图照出《红楼梦》基因图谱片断。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此种究诘,追根溯源。情因何而生,为何而生?即此一问,便超脱日常藩篱,这才有大视野。
*“朝代年纪,失落无考”
诗与情感,穿越时空,本无从考,无需考,如果非得处当时之景才能领会,则无艺术之可言。令普希金暗然神伤的隐秘愿望,到底是什么?谁知道,他对大海的倾诉,源于何时何地,是一时之兴,还是久久不能释怀的情愫?无从考,无需考。
* “几世几劫”
实为今世一劫,一劫则足以看清世人的面目。“劫”往往是对于那些锦衣玉食的人而言的,生于贫民窟里的人,已安然于社会底层,无所谓“劫”与不“劫”。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可见出世人的真面目。 “劫”或许是文学家的财富,因此,文学是沉重的,艺术之花是需要人生的苦难来滋养。鲁迅叮嘱后人莫做空头文学家,大概有这层含意吧。一个生活无虞的人,其再有才华,至多只能写些所谓富有“旨趣”的文字,臂如冰心的文字,虽然它们别有一番意义。
*“风月宝鉴”
人生的两面,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个快乐的奥布朗斯基,有一段名言,“如果能够摆脱尘世的欲望,那当然无比高尚;如果不能忍受寂寞,毕竟也享尽人间欢乐”,同样是写人的两面。风月毕竟是诱人的,世间大多数人都难以抵御。也正因为难以抵御,人类才会有发展,如果全人类都是不食烟火的仙道,恐怕人类早已自灭了。
*点化
一僧一道点化甄士隐。点化,更重要的是内心的顿悟,外因只不过的诱发、触发而已。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托尔斯泰看见一道花边,顿悟到《安娜*卡列尼娜》的概貌;罗曼*罗兰在山坡上张望黄昏的地平线,预见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能被点化,缘于慧根。
* 空空道人
道人原本空空。或,真有道者廖廖,多数乃披着道衣之空皮囊,以空空无为为之道者而欺世。
* 一僧一道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此后,一僧一道,常捉对而来。
何以至此?原来,一僧一道,即亦僧亦道。“俄见”乃“我之见”也。曹雪芹喜用谐音会意的笔法,书中比比皆是。此说当有所据。
亦僧亦道,反之,非僧非道。反映与我们中国人的信道信佛之状况,大多数人的信佛信道,没有那么认死地虔诚,而且也似乎不大清楚自己到底是信佛还是崇尚黄老之道,所谓信,远不能称为宗教信仰,佛与道,与儒家学说,与天命观等等,是中国人意识构成的一部份。
佛与道,让人很轻易地从世俗中超脱出来,但并无大碍,就象宝玉的参禅,因为很快,他又会从佛与道中超脱,回到现实中去。佛与道,不过是稍有阅历的中国人的心智的一部份,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不知道这种态度是好是坏,反正很大一部份中国人,就是如此。
*万事皆空
万事都是一个空,则世间无大事,万事因“空”而平等。则闺阁闲情与所谓仕途经济的正事,都平等了,而且仕途经济的大事,更有无趣之病。貌似以“空”来否定尘世,实则,因空见色,肯定世间缤纷的色彩。
*灌愁水
用眼泪与忧愁来书写。
*离恨天
离散之日,际遇不堪,则天天为离恨天。
*石头记之石头
石头大小是个物件,派什么用场,可不完全由它的特质决定。
*情僧录之情僧
泛情之僧,非限定于男女之情,对失去的乐园伤悼之情:闺阁闲情、日常生活起居、平常琐碎细枝末节,身处其中,或不以为意,一旦失去,伤悼之时,则细枝末节均是伤心处,自然男女情、童伴谊,更不用说。更兼闺阁中滋养出的多情种,其情更是不堪。虽灵性十足仍无力回天,故只有在空灵中去伤悼而已。
*因空见色之“色”
色非专指女色,目之所见之世象,是为色。
*荒唐言
其意不在于“言”本体是否荒唐,而在于所有列于纸上之“言”,以及立言的举动,均属无可奈何之举、无力补天之憾,因而是荒唐的。满纸空言天下事,徒然失意怅西风。立言者,尤其是失意的立言者,往往有这般惶惑。比不得商场官场得意之辈,所写均可列为教科书励志文。于是自嘲者有之,自傲者有之,也有默默地,如张爱玲所说称,将自己放低,低到尘埃里,从中开出花来。当然,也有说大话者,如“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古今”。即使是说大话的李白,也有诗云:吟咏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
*写实
鲁迅说,《红楼梦》因写实转成新鲜。写实部份只是材料,其中还有用非写实的东西(象征、幻象等)作经纬,也有书中幻化而来,更不用说其中的诗词歌赋,有不少篇什就象写字时描红一般脱胎于前人之作,如此等等,串联成一部奇书。
*为何以“考较女子”为主旨
《红楼梦》开卷即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因而设问,何必非得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考较去?其实所有之人,无论男女老幼高低贵贱,细细考较去,都有故事,都是一片天地。且按照所谓人人生而平等之时髦民主观,则人人都值得关注、值得细细考较。故曹氏值得推崇的不在于他考较的是女子,不在于他借贾宝玉之口说出的女儿是水做的等等惊人之语,而在于他的考较的真实与自然。艺术家们的精力有限,生活有局限,兴趣有差别,故而曹氏有他的主旨与角度,因为他自幼生长在温柔之乡,他从闺阁之中看世事最为自然方便。
*真事隐(甄士隐)
其实所有写就的作品,都不是真事,只不过是事件呈现给作者的表象,或者说作者用自己的观念所领会的事物,但它们并非事物的本真。就连日记之类、甚至《康熙起居注》都是片面的。作品只能是生活的影象、表象。“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者都不是花鸟的本原。凡事过境迁,真事不存,何用刻意隐去?故曹氏此语,已属多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凡人之所写所绘,永不可能是人事的本真,只不过传达其中之情之意而已。
*槛外人
体制外之人,俗世外之人,旁观之人。槛外人,也有动心的时候,但对于局中之事,未免隔膜。“世外仙姝寂寞林”。
*好了歌
激愤者的嘲解,或仅是市井之言,不足看得过重。无论如何,人类生存的欲望,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 如果《好了歌》能让世间人不再追名逐利,世人世事也太单纯了,也太无趣了。好比说,人固有一死,宇宙终有一天会毁灭。说了等于没说。
*焦大的骂与探春的耳光
焦大的骂有点道听途说,其实他并不知贾府的要害。探春的耳光才的重重地打在痛处,她理过贾府的事,深知其中的就里,所以,她打在受者的脸上,其实,自己的痛远比受者要大得多。
*风刀霜剑
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风刀霜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心理障碍者,别人无意,可是其心已伤,而且伤得隐秘,不得不隐忍,伤在潜意识之中。世间有各种各样性格,各种各样人格障碍。每颗心都会其成长过程中结下硬硬的壳,这壳是原本没有的,原来,它是一颗赤子之心。这是一种病态,可是,只有经过病后长成的硬壳,心灵才能有免疫力,才不致受到伤害。有些心灵,其赤子之心不改,于是,始终对于外在的世界高度敏感,时时有所感,总觉得风刀与霜剑无时不在。如林黛玉是也。

也说宝黛初次见面
宝玉与黛玉初见,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情形被人们注意到,且弄得很玄妙。
书中写道: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好象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
宝玉则更直接:
........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奇怪吗?其实不用怪异,只能当做平常事去看,用不着想着太虚幻境中的那些暗示,那些只不过是作者的故弄玄虚,或者说是作者用来编织他的作品的经纬,用来包容生活多面性的大器。宝黛初次相见时貌似怪异的行止,其实并不怪异。
其一:宝黛既表亲,则虽未见本人,未必没有见过与之相似之面孔。
其二:我们常有一种经验,生活中往往会发现此地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总有几个人,与原先所见过的人相似;------虽说人生不同如其面,但是,相似的人事,却常会碰到,常会因此地某人,而想到过去经历的人与事。
故宝黛的初识,只是平常事,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因果关系,多的是偶然事件。
《红楼梦》的第五回,全然可以把它当做算命先生的推论,生活,不可能按这种提纲走下去。
曹雪芹倘活到足够大的年纪,能把书写完,结果一定不会是当初想象的样子,说不定他会因此,倒过来修订第五回。
由此联想到,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开头部份,当安娜在火车站上偶然遇见一桩车祸时,安娜的心中“咯噔”了一下-------这一细节的生活基础是:安娜对自己的生活,在潜意识中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了。所以她疯狂地,不顾一切地与伏沦斯基私奔,其实,生活,与卡列宁的婚姻,令她的整个生活,已经死亡了。
生活中的许多事,其意义是由观者的内在决定的,而它们本身,并无必然的联系,把它们联系起来,甚至赋予宿命含义的,是观者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