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
编者按:本文为2020年11月7日刘铮于思南文学之家举办的《既有集》新书分享活动上的发言,经作者授权发表。

《既有集》,刘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288页,48.00元
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心爱的批评家”,这个题目公布出来之后,有一位我的朋友在网上转发,她说:如果是作家来谈啊,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的批评家”,在“我们”之后空了两个字,但我们依常理推断,这空白的两个字也许可以填上“不屑”“厌恶”,也就是“我们不屑的批评家”“我们厌恶的批评家”,如果空白的是四个字,那也可能是“深恶痛绝”。
我们今天来讲“心爱的批评家”,真的就不如先从这被人“深恶痛绝”的批评家形象说起,因为批评家的这一倒霉形象也由来已久了。
去年我读了一本美国人文主义者、保守派批评家莫尔(More)的评论集,其中有一篇是谈批评的,莫尔引用了达拉斯(E.S.Dallas)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归纳、总结历代文人对批评家的嘲讽的,其中把批评家比作锅匠、比作屠夫、比作蠢驴、比作毛虫、比作剪径大盗。为什么比作锅匠?大概是想说批评家所做的事无非是修修补补;屠夫,自然意指野蛮、血腥、大开杀戒;蠢驴,人所共喻;毛虫呢,大概是说批评家,“不咬人膈应人”;剪径大盗,也许是说批评家攘夺别人的财富,取之“无道”。
十九世纪法国有位崇尚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叫尚弗勒里(Champfleury),他说大多数的批评家扮演的是三种角色:cataloguers(编目师)、embalmers(尸体防腐者)、taxidermists(标本剥制师),再无其他。我的理解,那就是原本已经死透了的却要费心加以保存,而原本活蹦乱跳的却要给它弄死,然后心肝内脏统统挖掉,最后剩下一张皮。
那么批评家对自己就只有恭维吗?不是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批评家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书信中就对批评家这一身份大放厥词:他说“阉人是第一位现代批评家”,他说“如果我来写一部自传,我会管它叫‘皮条客的自白’”,他说“在我看来有学问的批评家是个畜生”,当然他自己就是特别有学问的一位批评家。批评家是阉人,用中国话说,不就是“太监”吗?皮条客,就是拉皮条的,是不是对着普通读者宣布哪本书很好,就像拉皮条一样呢?无论如何,不管是被评论的对象——作家、诗人们,还是批评家自己,对批评家都有很多负面评价的。
对批评家还有一个常见的指责,就是在批评的职业化、产业化之后,作家们说批评家是个寄生性的身份。海明威就很爱这样说,我们作家写出作品来,养活了批评家这个行当。批评家是依附于作家的作品来生存的,是寄生性的。
对批评家有如此多的责难,有如此多的“差评”,在此我不可能也无须一一加以反击。我就只说这最后一条吧,也就是“寄生性”这个问题。确实,围绕着大作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群体,围绕海明威也的确可能有一个小型的批评产业。不过,说起来,类似这种衍生性的批评或研究,恐怕不是批评的主流,也不是批评最高的体现。我们都知道,作家里面也有很多不入流的、糟糕的人,拿他们来代表作家,可能作家的群体也会觉得不公平。事实上,海明威的作品我已经十几年没有重读过了,当然他也写过很好的东西,比如说早期以尼克·亚当斯为主角的短篇小说,甚至第一个长篇《太阳照常升起》,我都觉得写得不错,但是对我来说,这十几年来没有感到重读的迫切需要,而且这些年也没有改变对他的认识。但好的批评家的作品我是每天都在读的。一个作家自信自己的作品能比批评家的作品更垂诸久远,其实是虚荣心的反映,且未必符合事实。是不是没有作家写出新作品,批评家就没事做了呢?也许有人会这样问。但这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这就好像是在问:要是没有农民种植蔬菜,没有养殖场养猪养鸭,是不是厨师就没事做了呢?当然如果真的发生那种情况,厨师就无用武之地了。然而,那样一种假设,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假设的情况不可能发生,总会有人种田、总会有人养鸡养鸭,也总会有人写出新作品。
那么如何理解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是否可以认为他们分处产业的上下游?的确,先有作品,后有批评,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先有水泥、钢材,建筑行业就寄生、依附于水泥厂、钢铁厂了。大家其实在各干各的事。通常来说,批评家做的事,不是为诗人、作家服务的——老实说,诗人、作家是个数量非常小的群体,批评家是为读者服务的。读者这一群体至为广大,心胸开阔的诗人、作家自己也属于读者这一群体。
说批评家为读者服务,那他是怎么服务的呢?他做的事又是怎么体现价值的呢?我自己有一个“一道光”的提法。“一道光”是说批评家将一道光投射到古往今来的作品上,让读者注意到那个地方,让读者学会观察进而理解那个地方。所谓“洞烛幽隐”,批评家是把被人忽视的、隐藏在幽黯之中的美和好指给人看。一道光束打上去,你的视线随之转移到那个地方,把它清清楚楚地看明白了,这就是批评。当你越来越多地领受这些光线,你自己的心房也变得越来越明亮,你自己也越来越多地向外投射光线,你变得越来越会领会文学、品鉴作品,你也成为“照射者”之一了。
在我的心目中,好的批评家就是投射光线的人。一个时代越是昏暗、越是朦胧,越是难以看清看透,我们对光线的渴求也就越强烈。
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很不幸,如果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许相当于东罗马帝国时期,相当于拜占庭帝国时期,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一个漫长的半死不活的状态,这不是针对中国来说的,而是就整个世界而言的。在我看来,如果选择一个标志的话,那么2001年的“9·11”事件可以作为地球文明进入衰败期的一个标志。事实上,自从2004年德里达去世以后,整个世界也就再没有出现过什么“全球性”的思潮了。当然,这种衰败是可以而且应当上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只是我们为了方便、好记起见,把它定在2001年。近二十年来,我们的文化、文明停滞了,甚至衰退了,乱哄哄的,平庸化了。地球文明进入昏暗朦胧、不清不楚、不尴不尬的时期了,像张爱玲说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着惘惘的威胁”。今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也许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不管我的认识或预期对还是不对,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它都必将影响到一个人的行动——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写评论、喜欢评论的人,我既然抱有如前所云的想法,那我必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有意识地沉入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文学评论中去,我读了大量今天已被人遗忘了的评论家的著作。一方面,这是“尚友古人”,与古人交朋友,另一方面,我也是试着探寻对抗我们这个时代昏沉症的良方。
我想回到一个热烈的、充满个性的、充满真知灼见的批评氛围中去,我想回避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在我看来经常是虚假的、无关痛痒的命题,我想借古人的一股“真气”。
在我的阅读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忆念的时刻:当时我在顺德出差,半夜十二点,我手边只有一本书,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国批评家沃尔特·雷利写的一本小册子The English Novel,一部写到司各特为止的英国小说史。那个晚上,我为他对文学的体会之深刻、判断之透彻所触动,感慨很深。比如在谈到英国十八世纪的女作家拉德克利夫(Radcliffe)时,雷利说过这么一句话:Romantic Movement may be described, in an aspect, as an invasion of the realm of prose by the matter of poetry.(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运动是诗的题材闯入了散文的领土)这样一种判断,在我看来,真有石破天惊的效果:它不止把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讲明白了,也把雨果、夏多布里昂讲明白了,同时也把“德国浪漫派”讲明白了。而这种深刻透彻就埋藏在一本1894年出版的旧书里。在那个晚上,我就在想,在中国,我们把时间放长点儿,比如说十年,在十年时间里有没有另一个中国人读了沃尔特·雷利的书,得到深深的触动和共鸣呢?也许都没有。那么这些深刻的话语是不是就躺在黑暗深处,也在等着“一道光”来把自己照亮呢?
我们回头来想雷利的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浪漫主义运动是诗的题材闯入了散文的领土”这样一种判断有个什么特点?这种判断是没法用事实推导出来的,你知道很多关于文学流派的知识,你读了很多作品,你也说不出这句话;这种判断,也不能用事实来证明或者否定。这种判断来自深透的审美体验,来自灵机一动的心理感悟,它只能以“一语道破”的形态存在,它是不可能靠事实性的学问积累来获得的。比如说我的书里,其实我是不做这种判断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所以我还是按事实的方式去论述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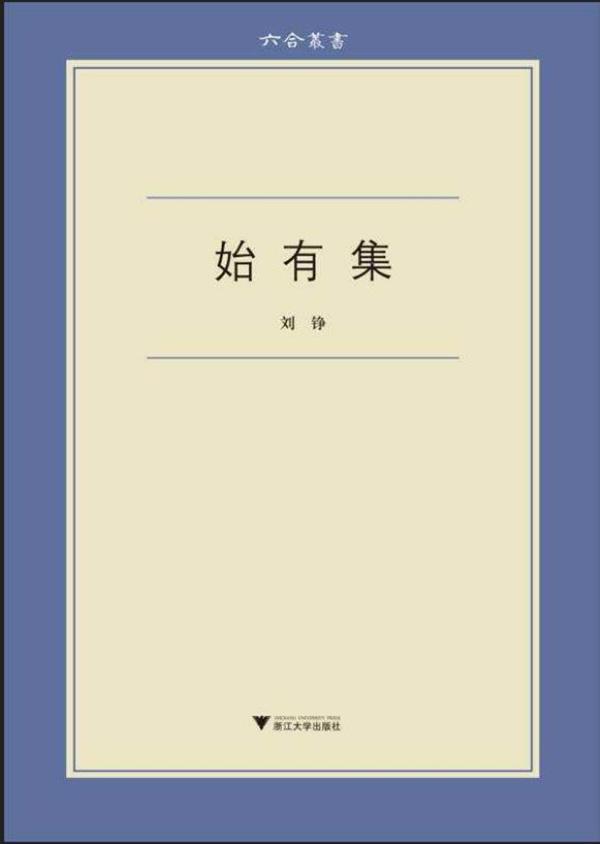
《始有集》,刘铮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242页,32.00元
我们今天谈“心爱的批评家”,我想说我心爱的,正是能做出这种判断的批评家,他超越了学问,是只有内行人才会为之击节叹赏的。波德莱尔也说过,实际上最好的批评不是那种貌似合情合理、四平八稳的批评,而是相反,充满激情的、丝毫不加掩饰地表露个人好恶的批评。勒南(Ernest Renan)也说过,“批评即不敬”,批评不承认“尊敬”这回事,批评就是撕去面纱,就是不顾权势,打破神秘,本质上是不敬,是背叛。它是唯一的权威,是只凭自己的权威。勒南说这是一种圣保罗式的精神存在:它判断一切,却不为任何他人所判断。当然,勒南的表达过于激烈了,但我想说,如果有好的批评家,那他一定是一个能做出超越事实层面、超越单纯学问的判断的、充满激情的、在某些时刻能表现为“大不敬”的批评家。
在与这些被遗忘的批评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有时候会有一种脱离了当下、脱离了这个俗世的体验:好像这些人就像幻影一般飘荡在我的周围,我的耳朵里似乎听到伊波利特·丹纳怎么说,欧内斯特·勒南怎么说,阿纳托尔·法朗士怎么说,圣伯夫怎么说,布吕纳介怎么说……就这样,我摆脱了我认为已经相当疲沓、相当乏味、相当无所适从的当代。
当然我得承认,当我在这些故纸堆中沉溺、吟味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我要寻找什么的。甚至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所获得的东西能够怎样被加以利用。在此之前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我在做这样的阅读,我也没有寻章摘句的企图,打算把它们引用到我今后的文章里,我也没有任何计划,想要把这些阅读变成一种有具体目标的研究……没有,完全没有。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像在荒野中一个人信步走走地读着书。对我来说,可能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就是我选择的,与这个世界对抗、对立的方式。也是像人家说的,在一个人身上,反抗这个时代。
我想感谢那些死去的、已经被人遗忘的了不起的批评家,他们的“潜德幽光”仍然向我投来光线,让我看清文学、看清文明,也看清自己的卑微的存在。这一切是如此之好,于是我决定,今天来谈“我们心爱的批评家”。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