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亚麻(原创)
作者:董涛(甘肃武威)
童年时代,我生活在凉州海藏寺西面一个叫李家磨的村子里,在我的印象中,麻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作物,每年春种时,队里除了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外,还要种植一定数量的麻。
故乡的麻,质地优良,色泽洁白,纤维度高,是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每年公社都下达一定数量的收购任务。故乡种麻一方面是完成收购任多,增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种麻是为了土地倒茬,今年种过麻的地,明年种植粮食作物,定会取得好的收成。
每到春天,和煦的春风吹过,休养生息了一个冬天的土地,从沉睡中醒来,像一块熟透了的处女地,早已地肥土软,等待耕种。同样闲了一个冬天的农人们,也养足了精神开始干活了。在队长的带领下,社员们拿上农具、牵出牲口,套上犁铧,开始了一年一度繁忙的春种。春耕时节, 春天广阔的田野顿时人欢马叫,呈现出一幅春耕的热闹景象。女社员和一些男劳力在田间撒农家肥、平整土地、拌种,一些壮劳力及有技术的老农负责犁地、播种,先是种上小麦后,再播种麻。麻生命力强,不择土壤,不论地块肥瘦,它都能够茁状生长。春耕过后,下过几场春雨,用不了多长时间,田里就开始出苗了。这时,天气更加暖和了,天空中燕子在呢喃欢歌,湖边垂柳舒散着绿色的枝条,放眼望去,田野里一片碧绿,像铺了一条绿色的大毯子,好看极了。在播种的作物里,小麦性子急,总是最先出土,麦苗的颜色是深绿色的。但相差不到一星期,麻地也开始出苗了,刚出的麻苗有二片淡绿色的小叶,看似嬴弱,羞羞藏藏的,让人看着心生怜爱。但不到半月时间,麻生长的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小麦。
转眼到了学生放暑假的时候,地上的小麦已一片金黄,到了开镰收割时节,麻地里的麻己长得一人多高,像张艺谋执导的《红高梁》中成片的高梁地,风吹过起起伏伏,很是壮观。在整个假期里,大麻地就是孩子们眼里的青纱帐,在麻地里玩“捉迷藏”永远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而在成年人眼里,大麻地也是一个绝妙的去处,一些热恋中大龄青年,也常到麻地深处缠绵,个別偷情男女,不分昼夜,大麻地始终是他们的消魂之处。曾有一次,年轻力壮的队长,正领着队里一个年轻媳妇在麻地里销魂,被媳妇的男人抓个正着,队长挨了打,这个男人还扬言要杀了队长,吓得队长躲在外面,有两个多月不敢回家,后来由派出所出面才平息了此事,多年以后麻地里的这个故事仍是乡亲们的笑料。
等到秋天,麻已长老,麻头上的麻籽稞粒饱满,麻地里整天就有成群成群的麻雀飞落到麻头上吃麻籽,人经过时,能惊飞一片。学生们在上学路过麻地时,也会拽倒麻,折取麻头,揉下饱满晶亮的麻籽,装在衣袋和书包里,当做像葵花籽一样的零食,那时节磕麻籽成了大人小孩的一种时尚。麻籽是油料作物,含有丰富的饱和脂肪酸,吃起来很香。这些麻籽,除生产队派一些女社员,选择一些籽粒饱满的麻头,剪下来留做次年的麻种外,其余的任人摘取。村里一些勤快的女人们,在劳动之余,她们就会摘来麻头,收获麻籽,用麻籽炒新下场的小麦粒,村里人叫“麻籽炒麦子”,这两种禾物是最佳搭档,吃在嘴里嚼起来又脆又香。还有心灵手巧的媳妇们,就把收获的麻籽收藏着,等到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尊贵客人,把麻籽破碎,放在锅里煮出麻腐,捞取麻籽壳,倒了汤,乡亲们把这叫“点麻腐”,点出的麻腐闻着就让人垂涎欲滴,点了麻腐的汤,喝起来很香,但性凉,喝多了闹肚子,小时,母亲点过麻腐的汤,我和馋嘴的弟妹们都爱喝,但母亲不让多喝,怕我们喝多了闹肚子影响上学。点好了麻腐,把土豆煮熟,捣成土豆泥,放上一些切碎了的葱末,拌在一起,就是上好的馅,用这馅包的饺子,就是“麻腐饺子”,不用放肉,吃在嘴里,那种绝妙的香味难以言传。小时侯,我母亲常做“麻腐水饺”给我们解馋。"麻腐水饺”是家乡的一道著名小吃。
“秋风”过后,地上长着的大麻就到了拔的时候,队里的男女社员们就戴上手套,到麻地里拔麻,把拔下的麻稍微晾晒,然后捆成捆,等待下坑沤麻。只有沤熟了麻,才能除去麻杆的青涩,便于从麻杆上剥下纤维。 沤麻也是个技术活,先是在麻地挖出一个长10米、宽3米、深3一4米的长方形麻坑,然后把梱好的麻,一层层地排列整齐,放满麻坑后,在上面压上石头,灌满水。经过太阳照晒,十几天过去后,麻坑里的水就起了变化,变成了绿色,远远都能闻到沤麻的味道,这时候麻就沤熟了。队里的男劳力就抽干麻坑里的水,取了压麻的石头,把麻一梱梱地从麻坑里捞上来,解开梱,散在麻地里晾晒。经沤过的麻,沒有了绿色,变得白亮。经过几天的风吹日晒,晾干的麻,重新梱成梱,生产队就按人口,把麻分配到每家每户。
分完麻,天气已到深秋,地上的秋禾已收获完毕,队里的男劳力开始犁地,给土地保墒,等待下一年春种;各家的女人们,则选择自家院里或院外巷道里一个向阳的地方,坐上板凳,和邻居们一边拉家长,一边剥麻。剥麻不能性急,这个活一般都是妇女们的事,这时你若进入每家的院落,都能看到婆婆、媳妇都在一边说着话,一边剥着麻,一些闲着的男人们偶尔也会帮着剥麻,但男人沒有耐心,剥一会就坐不住了,随即就会找个理由出去抽烟、耍牌。
我奶奶去世的早,父亲在信用社上班,剥麻的活,全由母亲一人承担,我和弟妹们都小,也帮不了母亲的忙。记忆中,每年的冬日,白天母亲除了剥麻,还要承担我们的一日三餐、打扫卫生、喂猪、喂鸡等家务。在漫长的冬夜里,有时我从梦中醒来,都看到母亲在屋里昏暗的煤油灯下,坐着板凳在剥麻。静静的冬夜里,母亲“嘶嘶”的有节奏的剥麻声,伴着我入眠,也声声敲打着我幼小的心灵。一个冬天的剥麻,母亲的双手溃裂,手上布满了老茧,开满了裂口,双手目不忍睹,使儿女们看着眼中流泪,心头流血,恨不能承担母亲的劳苦。直到今日,母亲去世二十多年后,我仍能清晰地忆起冬夜里母亲在油灯下剥麻的坚强身影。
整个冬天的剥麻要持续到次年春天来临才结束,这时生产队就开始向各家各户收麻了,称了斤数按麻的等级标准,折算着记上应得的工分,做为冬天剥麻的报酬。 缴完麻后,各家都有剩余,留足自家用的麻后,还能把剩余的麻,拿到城里的市场上卖了,买回家里用的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
麻浑身是宝,剥了麻后洁白的麻杆,是村民们生火引火的最佳材料,各家各户都把麻杆捆了,码放在院子的一个角落,留做全年生火引火的材料。村里有些小媳妇回娘家时,还会拿上几梱麻杆、几斤麻当做礼物,送给没种麻的母亲使用。家里留下的麻,家庭主妇们会把它纺成像棉线似的麻绳,这些麻绳是纳鞋底的上好材料,用麻绳纳成的鞋底做的“千层底”布鞋,鞋穿破了,鞋底还不坏。我小时侯穿的布鞋,就是母亲用自纺的麻绳,一针针纳成的,那坚实的“千层底”布鞋,我穿着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千层底’的布鞋,凝聚着母亲对孩子们浓浓的爱。
几十年过去了,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年,我的故乡早已随着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被扩建为湿地公园,村里的乡亲们也成了城市小区的居民,住上了楼房,过上了幸福的日子,那故乡的麻地和亚麻,永远成了我心中尘封的一段美好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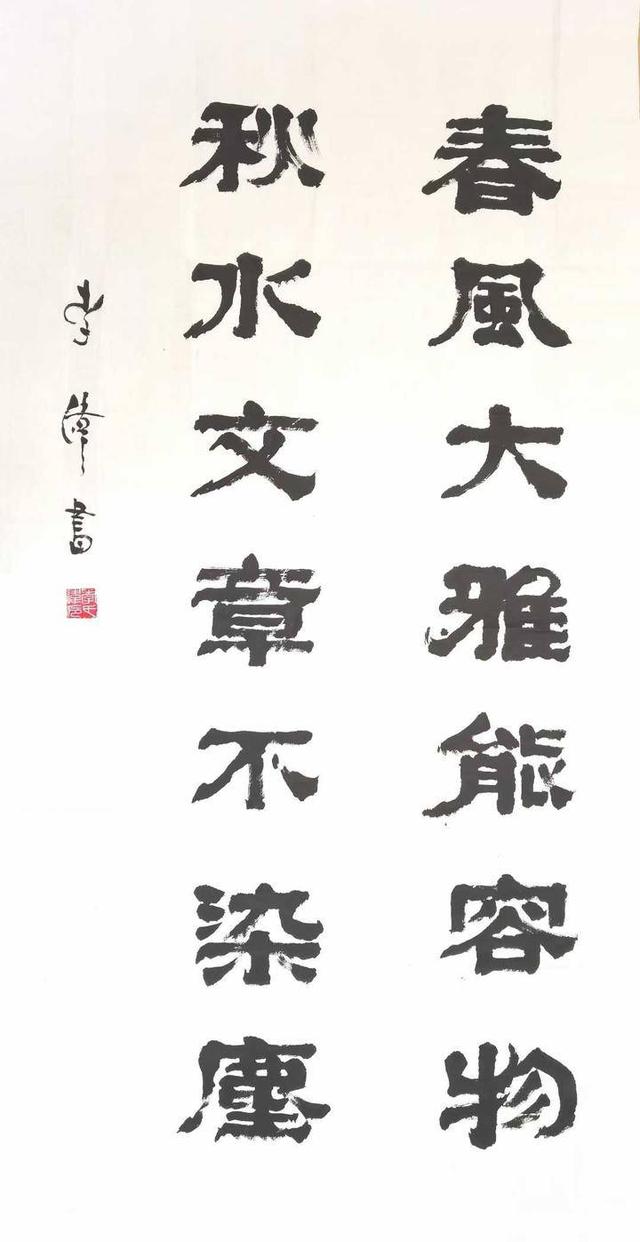

壹点号 望月文学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