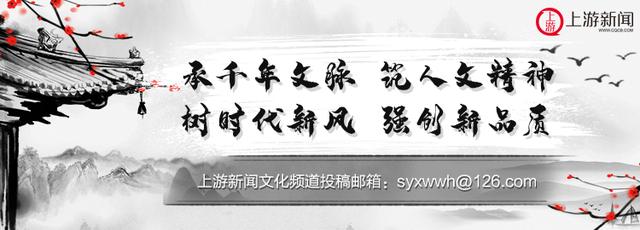一片树叶包裹的爱
高兴兰
农村有一道舌尖上的美食,只用一片树叶包裹。吃到口里软绵绵的,一股浓浓的清香沁入心脾。那就是母亲用桐子叶包裹的味道,是我不肯忘怀的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到立夏过后,一个火热的劳动场面铺展开来。生产队长安排一部分社员收割小麦。那时没有收割机,全凭镰刀,把橙黄色的小麦割来放在身后。然后用几根麦秆捆成一小捆,再由第二梯队人用三匹长篾片,分上中下三段,捆成大捆。劳动力强的就当运输人员,按头等劳动力计工分。
我记得,那时运小麦的工具是背夹。现在不易见,只有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偶尔还能看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背夹逐渐消失,但背夹留下的记忆,承载着农村的一段历史。
母亲干的是头等劳动力的活,用背夹上的绳索套住一捆小麦,蹲地而起。走平路还好点,要是遇上坡和下坡时就艰难,额头的汗水直往外涌,衣襟全湿了,遇上合适的坎才停下来松口气,从头顶上拿下毛巾擦一把汗又继续走。就这样从早走到晚,从地头走到打麦场,一季小麦收割完,没有听到叫苦声和怨声。
白天母亲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到晚上一家人吃饭后才去磨麦面。那时还没安装电灯,在月光的照射下,凭着感觉用石磨磨面粉。刚开始,借着朦胧的月光,母亲感觉有些不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磨绳上绕来绕去的。母亲停下石磨,叫我把煤油灯端去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是一条蛇爬在磨绳上。只见母亲手疾眼快,拿来一根竹棍果断的把蛇干掉。
面粉磨完后,见母亲拿来一个大团盖和两个小筛。其中一个为格筛,一个为面筛。格筛的作用是先去掉麦麸,为面筛作前战;面筛就是最后一道工序,或者说是细加工。母亲用一勺面粉加水,调成羹状,装在盆里,捂上盖子,叫发酵。这种发酵是不加什么酵母、苏打、碱的,完全是土法上马。只需上一次用剩下的面粉水作为发酵水,加点面粉发酵就行。第二天早上,母亲在发酵的盆里加面粉搅拌均匀,揉成面团。进行第二次发酵后,到房屋周边摘回一把桐子叶,叫我把叶片洗干净。
我把桐子叶拿到水井边上洗,观察到桐子叶比巴掌大。叶片心形,上面深绿色,前端尖,有光泽,基部有一根红绿色的长柄。基心处有两个小圆点,像红宝石。页面正中有一根叶脉延伸到叶尖,沿叶面对称的还有长短不一的叶脉线,下面有紧贴密生的细毛,味苦涩。听母亲说,桐子叶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母亲把第二次发酵好的麦面放在桐子叶面上,然后双手将桐子叶轻轻一合,放到蒸格上蒸15至20分钟,停火。约5分钟后,打开蒸盖,哇!一个个躺在蒸格上,有头有尾的,还真像猪儿睡觉一样。于是,桐子叶粑就有了另外一个头衔——“猪儿粑”。叶片露出的麦粑成赭色,有深浅不一的裂口。尤其是贴在锅边的面有锅巴,橙黄橙黄的,纯绿色食品。我提着猪儿粑,从头撕开桐子叶,里面有大小不一的蜂窝孔。吃在口里,软绵绵的,很有嚼劲。略有酸味,酸中有甜,清香可口,吃了就忘不了。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母亲把两边有锅巴的猪儿粑放到我书包里作午餐。我拿出猪儿粑正准备撕开桐子叶,一位同学手里拿着一本连环画,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我走来。四目相对,各有所思。她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猪儿粑,一边在手上不停地翻弄连环画。那本连环画我确实没看过,又特别想看,心知肚明她的意思。我将猪儿粑作为交换条件,她获得了猪儿粑的美食,我收获了连环画传递的知识。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猪儿粑由雪白雪白的馒头取而代之,农村没有人再蒸猪儿粑了。人们想吃粑的时候就上街买馒头,吃着白胖胖的馒头,总觉得差点味,没有猪儿粑的清香和嚼劲。我便怀念起猪儿粑的味道,满街、满市、满城到处找“猪儿粑”。
奇迹出现了,“买——猪儿——粑!热烙烙的猪儿粑!”我寻着街上的吆喝声走去,正是我要的那种猪儿粑。我伸手探了探,还带着余温,一下我就买了几个。回到家一吃,食之无味,嚼劲不足。不知是麦子的品种出了问题,还是厨艺不过关?我百思不得其解。
2019年,我回去陪伴母亲一段时间。在闲谈中,我说还想吃母亲蒸的猪儿粑。母亲说:“从哪年就没种小麦了,街上都没小麦卖。”在一旁的表弟说:“场上有时碰得到小麦卖。”说好了,你明年给我买点小麦,我回来让母亲给我蒸猪儿粑吃。可我没等到那一天,因2020年突发疫情,我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回家。这年末,母亲突然离我而去,我只有在心里深藏着母亲那片桐子叶包裹的爱。
母亲的桐子叶粑已成悄无声息的过往,演绎成深流的静水,潜伏在我人生的最深处。流逝的光阴,承载一片树叶包裹的爱,难以忘怀的情。
(作者单位:石柱县林业局)

版面欣赏

编辑:罗雨欣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