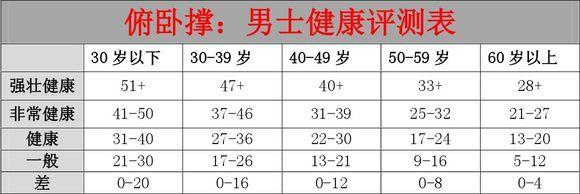在印度电影中,身体并不止于奇观化或者力量化的视觉展现,也不仅限于对两性关系的探讨,有时镜头还会对准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物,着力表现他们有缺陷的、无力的身体。

当中既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也隐藏着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而本质上对于“无力身体”的刻画也是印度电影在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包装策略。
对边缘身体的人文关怀印度影片中不乏对无力的身体展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缺乏力量的弱者,但对这一群体的观照则彰显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也体现出对生命的人道主义尊重。

在影片《地球上的星星》中,8岁的伊夏经常迟到、逃学,在课堂上由于想象力过于丰富,注意力总是难以集中,这直接导致了他的成绩落后并与成绩优异的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他总是遭到父母的嫌弃,之后父母把伊夏送到了严苛的寄宿学校,从此伊夏的生活便失去了颜色,也因此丧失了自信。
而美术老师尼克却敏锐地觉察到了伊夏在绘画上异于常人的天赋,他发现伊夏的学习问题其实是因为他患有先天性的阅读障碍,尼克不断鼓励他,并以别出心裁的方式辅导伊夏,这不仅使伊夏在美术上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也使伊夏找回了自信,重拾了学习的动力。

影片批判了唯成绩论的教育观念,强调了因材施教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也表达了尊重差异的价值观念,充分肯定了个体的潜在能力。
另外,这种独特性的彰显也体现在性别的取向问题上。而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如火如荼,同性恋群体也逐渐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

当代印度新浪潮电影导演阿那班·奥尼尔2005年的作品《我的兄弟尼基尔》就关注了同性恋群体的生活状态。片中刻画了同性恋群体所受到的压抑,描述了他们无法言说的情感。
片中尼基尔的性别取向一开始就注定了身体被社会边缘化的状况,但影片中表现得更为极致,片中尼基尔不幸患上了艾滋病,在此之后更是遭到了亲生父母的遗弃,这种边缘的状态再加上患病的身体,将同性恋者的无力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同时影片也表现了尼基尔从绝望无奈到努力争取自己尊严的过程。

另外,影片还插入了许多的人物访谈,展现了不同人眼中尼基尔的形象,侧面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视点。
影片对于这一边缘群体不再是模糊的展现,而开始直接将镜头聚焦到同性恋群体在遭受主流话语压迫之下的身份困境,表现出他们对于摆脱“妖魔化”标签的渴望。

可以说对同性恋群体的影像构建从暧昧模糊到被妖魔化,再到以一种正视的姿态进行展现,当中体现出一种对社会边缘群体观照。
而在2005年《黑色的风采》中则讲述了两个身体有残缺的人互相帮扶,在黑暗中寻找希望的故事,体现出导演的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关怀。

2010年《雨中的请求》则通过讲述伊森渴望安乐死的故事,表现出对生命尊严的渴望,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弱者叙事的内核与遮蔽虽然影片中展现了边缘群体/弱者在身体上的无力感和匮乏感,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一味地蜷缩在角落等待关注。

相反,无力的身体机能有时还可以强化他们的执念与行动力,使他们能够拥有比常人更加沉稳的心境,更加认真的态度与更加执着的精神。
相比之下,他们身上的这些缺陷往往不值一提,反而还有可能成为性格优势,非但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甚至还能承担起民族大义和国家话语的建构功能。

影片《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可以被看作两个弱者化解民族冲突的故事,小女孩沙希达作为“失语者”在异国走失,显然是需要帮助的角色。
而帕万虽然身体健壮,但20岁才考上高中,智力不高,但正是这两个力量都并不强大的人,却凭借着最真诚的情感化解了民族隔阂,突破了国家、宗教的双重阻隔,表达了对和平的希冀。

影片《我的名字叫可汗》则从家庭切入,讲述了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主人公可汗在美国四处奔走为穆斯林正名的故事。
影片旨在破除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的恐惧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排斥,旨在破除长期以来对亚裔、非裔的刻板印象、种族歧视以及“白人优越论”的观念,片中展现了善良质朴的非裔美国人与可汗之间的友谊,并以可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的情节表现了跨越种族的友好团结,隐喻着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诉求。

而相比之下,片中的白人则被塑造为暴力的施加者,白人学生仅仅因为可汗继子萨米尔的姓氏就粗暴地将其判断为恐怖分子,并将萨米尔殴打致死,而片中美国总统布什也被刻画为胆小怯懦的形象。
如此看来影片虽然打破了对穆斯林及非裔群体的刻板印象,却对白人的形象也进行了丑化,反倒建构了另一面“种族歧视”的壁垒。

而“以这样的偏见去解决另一种偏见,遮盖上世俗主义中的宗教宽容的大旗,用虚无缥缈的‘爱’去铺平宗教、民族、国家间的差异,显然只能是个梦幻。”
其次,影片中的“弱者”并非真正的弱者,影片只是借助弱者的力量来激发人类最本真的情感以实现对真善美的回归。

而在这类影片中也往往传递着朴素的、普世性的价值观。例如《我的名字叫可汗》当中非黑即白的论述,即“世界上只有好坏两种人”。
而《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当中的帕万在与沙希达的相处过程中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将沙希达平安送回家乡,从而忽略了宗教、国家之间的重重界限,这些人物身上的简单纯真反衬了社会的阴暗,而他们看似“反智”的思维与钝感力量恰恰完成了对人性真善美的最终召唤。

其实帕万与可汗都是阿甘精神的典型代表。前者为了送孩子回家,不惜违背岳父,跨越边境身受毒打。
后者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儿子正名更是独自踏上寻找总统的旅途,甚至被FBI误会为KB分子关至监狱。

影片中的这些“弱者”秉承着朴素的信仰,忽略了来自社会其他力量的束缚,这与经典电影《雨人》当中雷蒙德的形象不谋而合,但其本质不过是基于弱者视角下的成人童话。
因为他们本身都并非弱者,可汗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虽然表达有些吃力,但并不妨碍他追求爱情,并且可汗还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以及猜字水平、熟练的维修技巧,甚至有能力帮助受灾的非裔美国人在灾后重建家园,也正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比普通人稍显迟钝的“弱者”代表穆斯林群体向美国总统道出了心声。

另一方面,美国自9.11事件后对穆斯林群体的情感非常复杂,甚至有不少媒体将其妖魔化,而这种以弱者姿态进行的正名,也更容易为海外观众所接受。此外,这类影片中也潜藏着主流的意识形态。
2018年的《嗝嗝老师》讲述了患有妥瑞氏症的奈娜战胜自己的身体缺陷并且带领全班同学走向逆袭的故事。

该片在中国获得近1.5亿元的票房,虽然称不上大热,但对一部小成本的影片而言,这样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
影片的创意其实并没有十分出色,因为早在2008年美国就推出了影片《叫我第一名》,片中的奈娜与布莱德患有一样的疾病,也都从事了教育工作,简直是印度女版的布莱德。

虽然奈娜因为疾病从小受到了诸多歧视,但必须承认她具有一般人难以匹敌的高等学历和出色的专业能力,实际也并非真正的弱者。
不论是《嗝嗝老师》当中的奈娜,还是《地球上的星星》当中的伊夏,他们的成功更多是基于原有天赋。

虽然影片给这些人物赋予了不少现实的弱点以作为英雄的掩饰,例如出身低微、患有某种身体机能的障碍,但事实却是这些“小人物”本身就是天才。
只不过影片在叙事机制的缝合下使观众更多地将目光放置在对他们处境的同情以及对他们追寻成功的认同之上。

这类故事大多遵循了好莱坞的经典叙事结构,而显然小人物三幕式的成长故事也更易被世界各国观众所接受。
因此弱者的叙事逻辑其实也是印度电影的传播策略之一,它在移情的作用机制下,表达了一种“只要乐观自信地面对生活,就终有一天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观。

综合来看,身体叙事虽然基于主体身份,但并未止步于个体欲望的言说,其中还凝聚着女性主义、国家意志等诸多文化意义。
从整体上看,21世纪以来印度电影大胆地展现了银幕上的身体,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并通过展现力量化的身体将个人与国家的意志紧密结合,且这种身体的力量也开始逐步过渡到女性身上,甚至成为女性进行反抗的行动表现。

虽然这种女性的力量仍然无法完全逃离父权的秩序框架,但却昭示着两性话语的变革,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寄托着女性对于未来生存环境的期许,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再次,印度电影中还通过弱者叙事的策略传递出一种易于为全球观众所接受的价值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