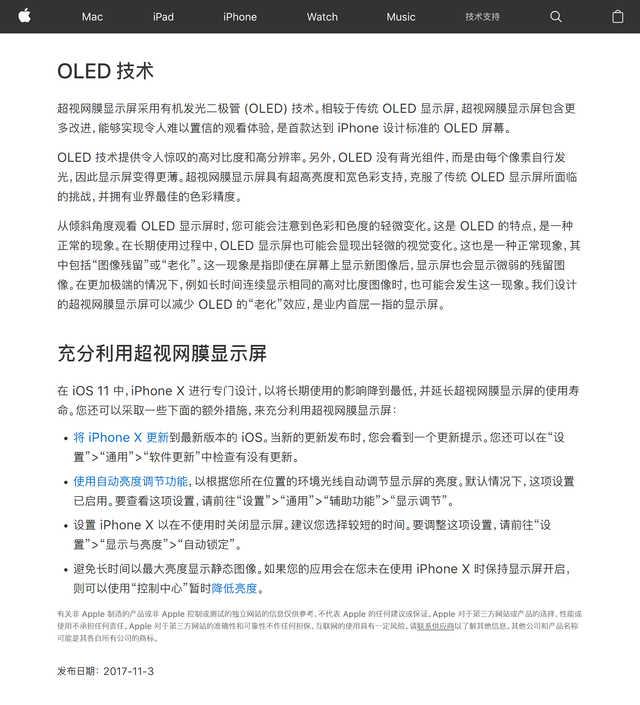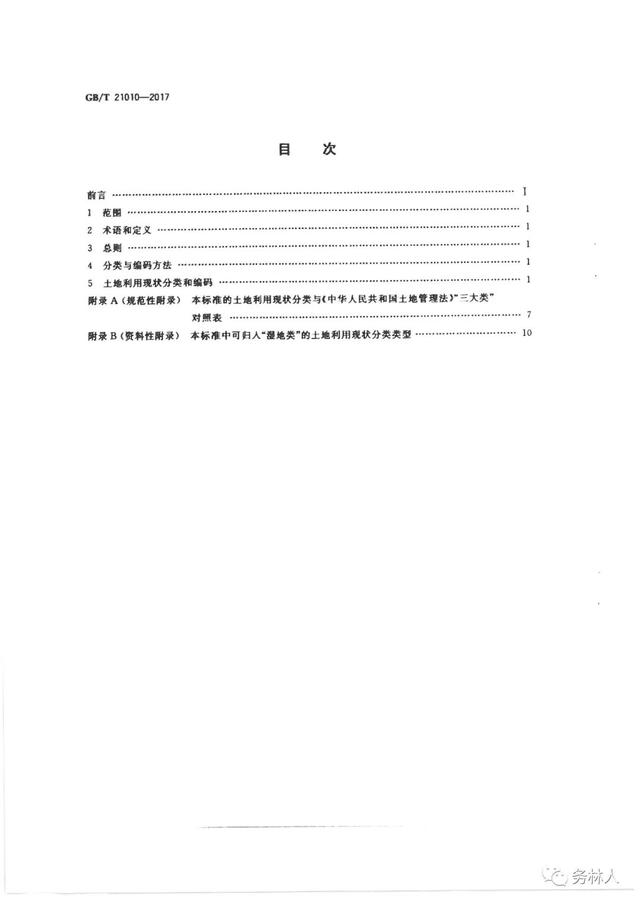《洗冤集录·验他物及手足伤死》说:“诸以身去就物谓之磕。虽着,无破处,其痕方圆;虽破,亦不至深。”
这段话的意思是,凡是人的身体、四肢、头部碰到硬质的物体,检验的定义叫作“磕”。一般说来,皮肤没磕破的,其痕迹呈圆形状;有破口的,其创口也不深。
为防止对损伤的描述有歧义,宋慈特地把所谓“磕伤”,讲得清清楚楚,以便日后检验时有依据,避免错案。宋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几百年后的清代作家曹雪芹著《红楼梦》时,就描写了有人故意把“砸”伤改作“磕”伤的案件,揭露了一起官场司法腐败案。
《红楼梦》里有个人物叫薛蟠,前后两次惹人命官司。第一次是在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打死了冯渊;第二次是在第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寄闲情淑女解琴书”,打死了酒店的酒保。这第二次闹出的人命案件,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详细描写了衙门里仵作修改检验报告的故事。

这次人命案件是薛蟠在得意楼酒店喝酒作乐。因为“当槽的”酒保张三前一天老是拿眼睛来偷瞟薛蟠带去的蒋玉函,心中甚是不快,就故意斗气找碴打架,拿碗砸酒保张三的头部。一下子砸下去,张三脑袋就开了花,当场咽了气。薛蟠被当地官府拿住,自认“斗杀”,招供在案。后来,薛姨妈、王夫人求了贾政托人与知县说情,凤姐又与贾琏花上几千银子,把知县、仵作和涉案证人等全都买通。
到了当地知县正式开审时,所有的证人都改了口,都说是没有看见薛蟠打人,而是“酒碗失手,碰在脑袋上的”。薛蟠供词也说:“小的确实没有打他,为他不肯换酒,故拿酒泼地。不想一时失手,酒碗误碰在他的脑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里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过一会就死了。前日尸场上,怕太老爷要打,所以说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爷开恩!”
知县叫仵作上报尸格,受了贿赂的仵作禀报说:“前日验得张三尸身无伤,惟头顶囟门有磁器伤,长一寸七分,深五分,皮开,囟门骨脆,裂破三分。实系磕碰伤。”于是,知县判决,薛蟠是“误伤”张三致死。
按照大清法律,“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是要比照“斗殴杀人”罪而“依律收赎”,就是拿钱财来抵销掉原来应该判处的刑罚,给予“被杀之家”营葬费用,折白银十二俩。那对于“丰年好大雪”的金陵大户薛家来说,完全只是九牛一毛。
《红楼梦》这一故事里,仵作将原来的“砸”改为“磕”,就是完全改变了致伤的性质。宋慈《洗冤集录》所定义的磕伤,一般是没有创口的,留有痕迹,即使是形成了创口,“虽破亦不至深”,应该是个浅伤口。而张三的脑袋上的伤口“长一寸七分,深五分,皮开,囟门骨脆,裂破三分”,居然是自己硬把自己的脑袋“磕碰”到位于头顶的囟门骨开裂三分脑浆涂地的程度,所以只好说张三的囟门骨实在是“太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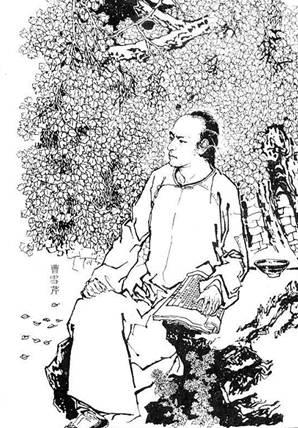
曹雪芹笔下所描写的“砸”改为“磕”,实际上是抨击鉴定人受贿后“自行修改鉴定”,指出修改鉴定行为的背后有权钱交易。与修改鉴定同样情形的是“自行撤销鉴定”,其背后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觉得不错,请点赞↓↓↓
,